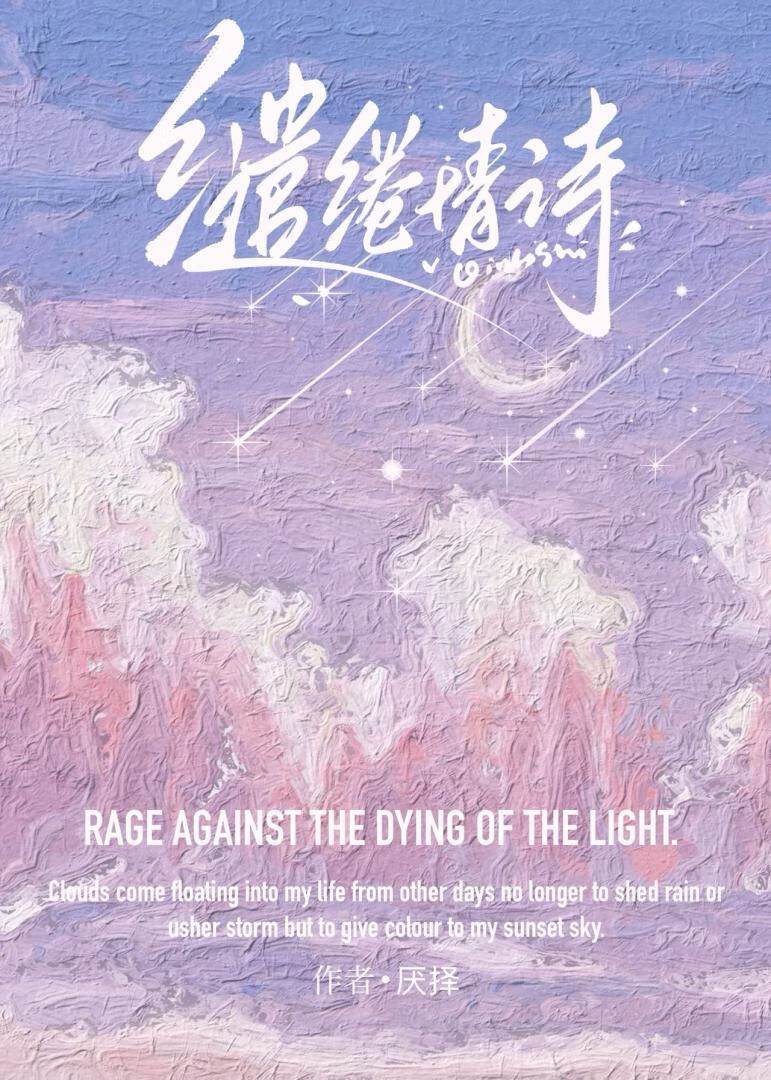《浸入玫瑰池》 第1卷 第126章 吻到
楚絨心頭一,下意識就要往鶴鈺離開的方向追去。
可還沒邁出一步,手腕就被沈厲尋牢牢扣住。
“昭昭,生日快樂也不跟二哥說一聲嗎?”
他嗓音低啞,幽深的眸子鎖著,帶著幾分醉意,幾分執拗。
楚絨掙了掙,卻被他握得更。
氣得瞪眼,又拿他沒辦法,最終還是不不愿地開口,
“二哥……生日快樂。”
說完,以為他會松開,卻沒想到沈厲尋突然用力一扯,直接將拽進懷里。
楚絨渾僵住,鼻尖瞬間盈滿他上淡淡的木質香氣,混合著微醺的酒氣,沖擊得頭腦發懵。
“沈厲尋!”
氣得跺腳,聲音都帶了。
然而還沒等徹底掙,一蠻力驟然襲來,沈厲尋被猛地拉開,接著,的手腕被另一只悉的手扣住,力道大得似要將的骨頭碎。
冷冽的雪松香沉沉過來,楚絨抬頭,正對上鶴鈺在昏暗線下的半張側臉。
男人廓如刀削般鋒利,眼底翻涌著冷戾的暗,下頜線繃得極,像是抑著某種即將發的緒。
“鶴鈺……”
心口一跳,下意識喊他。
男人沒有看,甚至沒有回頭,只是松開了的手腕,而后,抬手,揮拳。
“嘭——”
一聲悶響,沈厲尋踉蹌著后退幾步,后背重重撞上銅柱臺子才堪堪停住。
他抬手,指腹蹭過角溢出的跡,腥甜在舌尖蔓延,醉意終于散了幾分。
夜沉寂,庭院里只剩下急促的呼吸聲。
鶴鈺站在原地,指節泛紅,眼神卻比方才更冷。
他盯著沈厲尋,嗓音低沉,一字一頓,
“別。”
沈厲尋沒有看鶴鈺,也沒有回擊。
他半倚在臺邊,幾縷黑發垂落在眉骨前,襯得那雙冷眸愈發深邃,一雙幽深的黑眸越過面前的男人,直直向楚絨。
Advertisement
夜風拂過,他的呼吸似乎停滯了幾秒,結艱難地滾了一下,
“昭昭。”
楚絨站在原地,眼神復雜地與他對視了一瞬,隨后垂下睫,默不作聲地往鶴鈺后躲了躲,直到整個人都藏起來。
這一細微的作像一把鋒利的刀,狠狠刺進沈厲尋的心口。
他的瞳孔驟然,角扯出一抹苦的弧度,像是自嘲,又像是認命。
“對不起。”
這三個字像是從嚨深出來的,干得幾乎聽不清。
說完,他轉就走,腳步踉蹌了一瞬,卻又很快穩住,最終消失在長廊盡頭的黑暗里。
楚絨目送著人走遠,輕輕拽了拽面前男人西裝一角。
鶴鈺只是轉看了一眼,眸深沉如墨,什麼也沒說,提步往前走。
連忙小跑著跟上去,指尖飛快地在手機屏幕上敲打,舉到他眼前,
「你怎麼回來了?」
鶴鈺垂眸掃了一眼,薄勾起一抹極淡的弧度,依舊沉默。
不回來?難道要任由沈厲尋抱著?
這個念頭在心底翻涌,暗的緒如水般蔓延,可他面上卻毫不顯,只是神淡淡地繼續往前走。
楚絨不肯放棄,又低頭敲了幾個字,再次遞過去,
「你生氣了嗎?」
鶴鈺的目緩緩從手機屏幕移到臉上。
走廊下,小燈亮,仰著小臉,睫纖長卷翹,神間帶著幾分忐忑,瓣因為張而輕輕抿著,顯得格外。
這張臉漂亮到讓人對著,連脾氣都發不出來。
可他依舊沒說話。
楚絨咬了咬,三連步跑過去拽住他的胳膊,整個人幾乎掛在他上,賴著不走。
當然阻止不了他的腳步,但卻功拖慢了他的速度。
一步,兩步,他的步伐果然漸漸緩了下來,最后干脆停住,轉看。
Advertisement
一雙黑眸醞釀著濃稠的緒,深沉得讓看不懂。
“鶴……”
剛想開口,男人卻突然彎腰,一把將打橫抱了起來。
楚絨下意識掙扎,頭頂卻傳來他低沉喑啞的嗓音,帶著幾分危險的意味,
“鬧什麼。”
頓了頓,他又淡淡補了一句,
“不是走不嗎。”
回到家,鶴鈺將輕輕放在沙發上,轉便進了浴室。
不一會兒,嘩啦啦的水聲響起,接著的手機屏幕亮起。
「叮咚——」
他發來信息,屏幕上是擺放泡泡球的小框:
「喜歡哪個。」
楚絨心不在焉地掃了一眼,隨手點了個的。
水聲停了片刻,浴室門被推開。
鶴鈺走出來時,上只穿著一件白襯衫,袖口挽到手肘,出線條分明的小臂。
水汽氤氳間,襯衫微微著意,約勾勒出肩頸線條的廓,領口松了兩顆扣子,鎖骨若若現。
他徑直走到面前,彎腰將抱起。
楚絨下意識吞了吞口水,清晰地到他上那低沉的氣。
鶴鈺不高興的時候就是這樣,沉默得近乎抑,所有的緒都化作行,一句多余的話都沒有。
浴室里香薰蠟燭靜靜燃燒,浴缸中鋪滿了泡泡和玫瑰花瓣,溫熱的水汽裹著淡淡的香氣撲面而來。
的心跳突然加快,下意識開口,
“我自己可以。”
話說出口才想起來他聽不見。
愣神間,鶴鈺已經將放在浴缸邊緣,手指不不慢地搭上的扣。
楚絨本拒絕不了。
男人給洗澡的作很認真,也很仔細,可那張臉卻始終冷著,面清冷,眉目清寒,眸底深暗如墨。
有一肚子話想說,可看著他這副模樣,又全都哽在嚨里。
反正說什麼他都聽不見。
手想去拿手機,卻被他一把扣住手腕,力道大得不容掙。
Advertisement
男人的指腹帶著薄繭,蹭過細的,好幾都被他得微微泛紅。
楚絨也是有脾氣的。
終于忍不住自顧自地發泄起來,
“干嘛那麼兇嘛!”
“我也不想的呀!我剛剛明明是要去追你的,誰知道沈厲尋他……你別蹭了,疼!”
氣得抓起水面上漂浮的花瓣就往他臉上扔,上也不肯罷休,
花瓣輕飄飄地落在他肩頭、發上,甚至有一片沾在他邊。
鶴鈺神未變,只是抬手撥開,繼續手上的作。
氣紅了臉,啞著聲罵他,
“鶴鈺你就是個王八蛋。”
濺出來的水珠順著男人高的鼻梁下,滴落在襯衫領口,暈開一片深的痕跡。
鶴鈺半跪在浴缸外,襯衫早已被水汽浸得半,在上,勾勒出悍的腰線。
他盯著張張合合的,忽然淡淡開腔,
“我不是。”
楚絨一愣,猛地抬起眸子看他,眼底滿是欣喜,
“你能聽見了?”
“聽不見。”
“啊”了一聲,滿眼失落,
“那你……”
鶴鈺勾了勾,語氣平淡,
“猜得到你在說什麼。”
頓時氣結,又抓了一把泡泡往他臉上糊。鶴鈺也不躲,任由鬧,只是在想站起來的時候,一把扣住的腰,重新按回水里。
楚絨想反抗,他倏地俯,狠狠咬住的,力道重得幾乎讓吃痛。
下一秒,他直接進浴缸,水嘩啦一聲漫溢出來,打了地面。
的泡沫和破碎的玫瑰花瓣被沖散,隨著水流漂到更遠的地方,像是一場無聲的潰敗。
楚絨被他抵在浴缸邊緣,后背著冰涼的瓷壁,前卻是他滾燙的溫。
水汽蒸騰間,他的襯衫徹底,半明的布料在理分明的膛上,發梢的水珠滴落在鎖骨,燙得輕輕一。
“鶴鈺……”
剛想開口,卻被他再次封住舌。
這個吻帶著抑已久的怒意和占有,近乎兇狠地碾過的呼吸,他的手掌扣住的后頸,指腹挲著敏的,得仰起頭承。
浴缸里的水還在不斷晃,波紋一圈圈撞在邊緣,發出細微的聲響。
鶴鈺的呼吸重,眼底翻涌著濃稠的暗,像是終于撕開了冷靜的表象,出里近乎偏執的占有。
楚絨被他吻得缺氧,手指無意識地揪住他的領,指尖陷繃的理。
直到快要不過氣,他才稍稍退開,鼻尖抵著的,呼吸錯。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91 章
閻王愛上女天師
白梓奚只是隨師父的一個任務,所以去了一個大學。奈何大學太恐怖,宿舍的情殺案,遊泳池裡的毛發,圖書館的黑影……白梓奚表示,這些都不怕。就是覺得身邊的這個學長最可怕。 開始,白梓奚負責捉鬼,學長負責看戲,偶爾幫幫忙;然後,白梓奚還是負責捉鬼,學長開始掐桃花;最後,白梓奚依舊捉鬼,然而某人怒摔板凳,大吼:哪裡來的那麼多爛桃花,連鬼也要來?白梓奚扶腰大笑:誰讓你看戲,不幫忙?
33.8萬字5 34513 -
完結1074 章

我渣了死對頭的哥哥
司西和明七是花城最有名的兩個名媛。兩人是死對頭。司西搶了明七三個男朋友。明七也不甘示弱,趁著酒意,嗶——了司西的哥哥,司南。妹妹欠下的情債,當然應該由哥哥來還。後來,司南忽悠明七:“嫁給我,我妹妹就是你小姑子,作為嫂嫂,你管教小姑子,天經地義。讓她叫你嫂子,她不聽話,你打她罵她,名正言順。”明七:“……”好像有道理。司西:“……”她懷疑,自己可能不是哥哥的親妹妹。
90.2萬字8 35281 -
完結462 章

傅爺的王牌傲妻
寧洲城慕家丟失十五年的小女兒找回來了,小千金被接回來的時灰頭土臉,聽說長得還挺醜。 溫黎剛被帶回慕家,就接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警告。 慕夫人:記住你的身份,永遠不要想和你姐姐爭什麼,你也爭不過。 慕大少爺:我就只有暖希這麼一個妹妹。 慕家小少爺:土包子,出去說你是我姐都覺得丟人極了。 城內所有的雜誌報紙都在嘲諷,慕家孩子個個優秀,這找回來的女兒可是真是難以形容。 溫黎收拾行李搬出慕家兩個月之後,世界科技大賽在寧洲城舉辦,凌晨四點鐘,她住的街道上滿滿噹噹皆是前來求見的豪車車主。 曾經諷刺的人一片嘩然,誰TM的說這姑娘是在窮鄉僻壤長大的,哪個窮鄉僻壤能供出這麼一座大佛來。 兩個月的時間,新聞爆出一張照片,南家養子和慕家找回來的女兒半摟半抱,舉止親暱。 眾人譏諷,這找回來的野丫頭想要飛上枝頭變鳳凰,卻勾搭錯了人。 誰不知道那南家養子可是個沒什麼本事的拖油瓶。 南家晚宴,不計其數的鎂光燈下,南家家主親自上前打開車門,車上下來的人側臉精緻,唇色瀲灩,舉手投足間迷了所有女人的眼。 身著華服的姑娘被他半擁下車,伸出的指尖細白。 “走吧拖油瓶……” 【女主身份複雜,男主隱藏極深,既然是棋逢對手的相遇,怎能不碰出山河破碎的動靜】
176萬字8.46 260012 -
連載120 章

限時閃婚:傅少追妻不要臉
閃婚一個月后的某一晚,他將她封鎖在懷里。她哭:“你這個混蛋!騙子!說好婚后不同房的……”他笑:“我反悔了,你來咬我啊?”從此,他食髓知味,夜夜笙歌……傅言梟,你有錢有權又有顏,可你怎麼就這麼無恥!…
20.6萬字8 11589 -
完結8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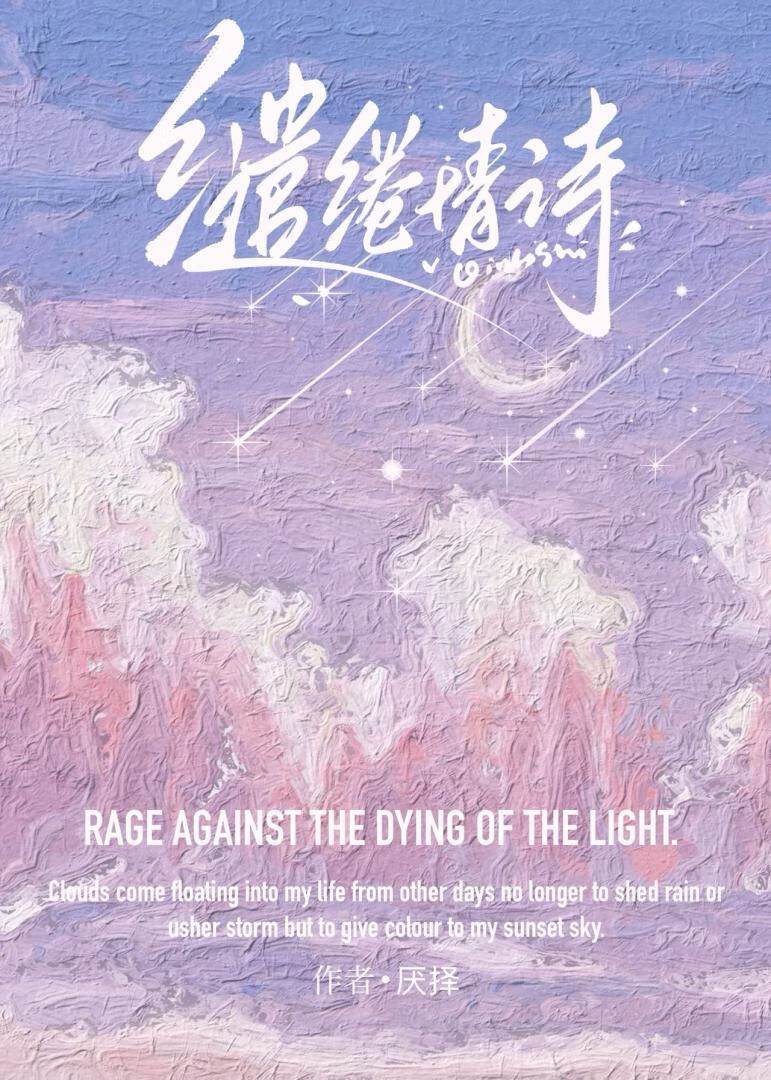
繾綣情詩
謝祈音從小泡在蜜罐子里長大,除了婚姻不能自主外可以說是過得順風順水。 未婚夫顧時年更是北城權貴之首,條件優渥至極。即使兩人毫無感情,也能護她餘生順遂。 可這惹人羨豔的婚姻落在謝祈音眼裏就只是碗夾生米飯。 她本想把這碗飯囫圇吞下去,卻沒想到意外橫生—— 異國他鄉,一夜迷情。 謝祈音不小心和顧時年的小叔顧應淮染上了瓜葛。 偏偏顧應淮是北城名流裏最難搞的角色,不苟言笑,殺伐果決。 謝祈音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小命和婚後生活的幸福自由度,決定瞞着衆人,假裝無事發生。 反正他有他的浪蕩史,她也可以有她的過去。 只是這僥倖的想法在一個月後驟然破碎。 洗手間裏,謝祈音絕望地看着兩條槓的驗孕棒,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 完了,要帶球跑了。 - 再後來。 會所的專屬休息室裏,顧應淮捏着謝祈音細白削瘦的手腕,眼神緩緩掃至她的小腹,神色不明。 “你懷孕了?” “誰的。”
26.2萬字8 1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