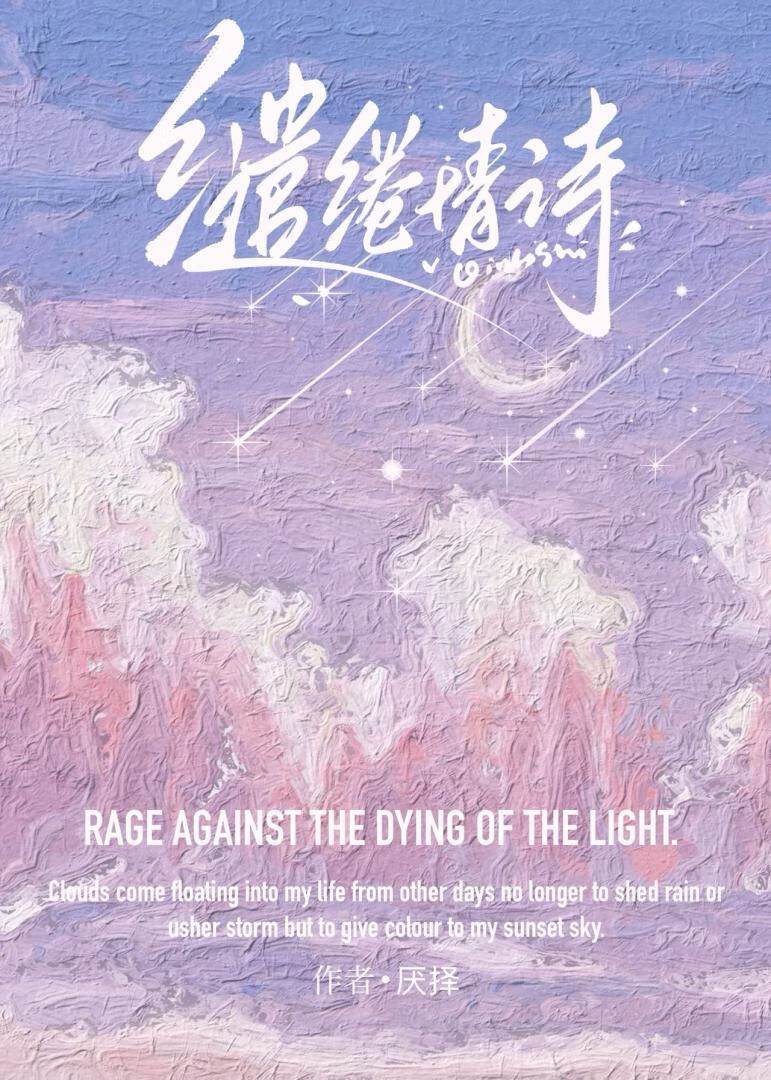《高甜!婚后她被冷厲首長捧上心尖》 第1卷 第112章 難道不是于家人先對我宣戰的麼?
消毒水刺鼻的味道爭先恐后地鉆鼻息,余依皺著眉頭慢慢睜開了眼睛。
模模糊糊中,看見一片橄欖綠的塊向湊近,而后矮下了子坐在床邊的椅子上。
“好些了嗎?”
暮寒玨擔憂地握起余依的手了一下。
接到陸斯霆電話的時候,暮寒玨還在忙著軍區的事。
一聽說余依傷的頭破流,心臟倏忽就在了一起,連軍裝都沒來得及換就匆匆趕來了定位上的醫院。
余依晃了晃腦袋,覺像是有什麼東西在顱炸開一樣,疼得想殺幾個人。
“有點疼……”余依的聲音弱弱的。
雙目呆滯地看了一圈病房的環境。
床邊還圍著陸斯霆和不得不坦白事實的簡糖。
“這是哪?”
“這是醫院。”暮寒玨前傾上,抬手握住了余依的下,“依依,你別嚇我。”
余依先是一陣茫然,旋即用力甩開了暮寒玨的手。
“先生,我和你就不認識,不要一上來就手腳好嗎?”
“什麼?”
暮寒玨僵住,瞳孔瞬間在一起。
他猛地站起來,不小心絆到了椅子,將那鐵質的椅子在地上拖行了兩下,發出尖銳刺耳的音。
“依依,你再看看我。”暮寒玨捧起余依的臉,強了一個笑容出來。
“你不可能不認識我……”
怎麼可能會不認識呢?
他們一起經歷了那麼多個日夜,他們還相互攙扶著度過了荒村的十七天。
怎麼可能會不認得他?
余依就那麼漠然地看著他。
那樣的眼神遠比看著一個陌生人時還要冰冷,以至于在很多年后,暮寒玨每每回想起這畫面都仍覺忐忑。
忽然,笑了。
兩眼彎彎,盈盈而笑,纏在頭上的紗布還更添了幾分與平日不同的清冷破碎之。
Advertisement
余依反捧起暮寒玨的下,在他額頭上輕輕吻了一下,笑著說:“我騙你的,你這麼張干什麼?”
心中的石頭穩穩落地,暮寒玨松了口氣,出手擰了把乎乎的臉蛋。
松開時,瓷白的臉上多了道紅痕。
余依痛得直皺眉:“干什麼呀?一言不合就手。”
“不準再和我開這種玩笑。”暮寒玨沉著張冷臉道,“我真的會害怕。”
余依拉著他的手,調侃道:“還有我們暮大首長怕的事呀?”
“和你沾上關系的事我都會擔心,更別說失憶這種狗到不能再狗的東西。”
他抱住了余依,下墊在的頸窩上,側臉的廓著的臉,像個了委屈的孩子。
“依依,別嚇我。”
“乖啦乖啦。”余依反扣住暮寒玨的腰,“以后再也不騙你了,好不好?”
“嗯。”
暮寒玨放自由,將險些被自己踢翻的椅子拉了回來坐下,與余依十指相扣的手像是不愿意松開。
陸斯霆嘆了口氣,將手搭在暮寒玨肩上按了按:“怪我,我也沒想到會出這樣的事,早知道我就帶回局里再聊了。”
暮寒玨沒抬頭,淡淡地說:“不怪你。”
簡糖心里也有些自責,余依要是不出面給撐腰也不會被撞到腦袋磕個大口子出來。
說:“我不該逞一時痛快和于姣起正面沖突的,這幾年在家待得腦子轉不過彎來。”
“于姣?”暮寒玨扭過頭來看了他們倆一眼,“于姣把推這樣的?”
簡糖點了點頭。
陸斯霆嘆口氣,摟著簡糖的肩膀拍了拍:“是啊。如果是別人,我當場就可以替余依出了這口氣,可偏偏是于家的人。”
雖然陸家和暮家的地位都遠遠凌駕于于家之上,但于家好歹也是撐起炎國半邊天的豪門世家之一。
Advertisement
如果真的因為這種事起了沖突,不是有損家族之間關系,甚至會導致時局變化。
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至陸斯霆不會去冒這個險。
暮寒玨就不一樣了,他冷呵一聲:“于家人又如何,犯了錯就能不承擔責任?”
陸斯霆說:“理是這麼個理,但余小依這不是沒事兒麼。為了這和于家結仇,值得麼?”
暮寒玨笑了一下,起眼皮瞅了陸斯霆一眼說:“難道不是于家人先對我宣戰的麼?打了我老婆,我還不能給他們點回禮?”
陸斯霆還想再勸勸,但還是沒來得及。
暮寒玨打電話給墨硯查來了于家老爺子的電話,而后毫不猶豫地撥了出去。
對面接起得很快,只是并不知道來者是誰。
于自修的聲音蒼老,聽起來像是在和誰說笑,接電話的語氣似乎都還帶著點若有若無的笑意。
“你好,哪位啊?”
暮寒玨也含著笑說:“于老爺子,最近忙麼?”
于自修聞言一怔。
這聲音……似乎上次在議會上聽到過。
于自修試探著問了一句:“暮首長?”
暮寒玨道:“是我。有些話想和于老面談,不知道于老現在方便麼?”
于自修心里為難,卻是不敢得罪了這煞神,“方便是方便,就是不知道寒部是所為何事啊?”
暮寒玨抬眸看了看天花板的一點,慢條斯理道:“大概是有關于小朋友的教育問題。”
于自修:“……?”
……
余依又休息了一會兒,醫生也過來檢查了一遍傷口,確認沒事之后才辦了出院。
病房里只有簡糖陪著。
簡糖握著的手,皺著眉頭說:“你為什麼要看的玉牌呀?你看看這傷口這麼大。”
“幸好不是在臉上,否則你都要破相了。”
余依垂著眼眸,慢慢地說:“那個玉牌和我爸爸送給我的那一個很像。”
Advertisement
簡糖嘆了口氣,說:“這世界上像的東西那麼多,于家在京城,而你是淮城人,怎麼可能……”
忽然停頓了一下,拉著椅子湊近了余依,低聲音說:“我曾經聽到過一個小道消息……”
這些年來簡糖一直裝瘋賣傻,和陸斯霆一起出席什麼宴會的時候,那些豪門千金或闊太說話也就從不避諱著。
也是靠著這樣才得到了一個旁門左道的小消息。
簡糖神兮兮地說:“聽說,于姣以前就是在淮城和養父母一起生活的……”
于姣來京城讀大學,因為家庭條件一般,生活費不夠花,在一家酒店當過一段時間服務員。
某天遭了人算計被送到了于放的房間,于放一眼認出了玉牌,這才讓于姣認祖歸宗。
“搞不好那玉牌還真是從你手里來的。”簡糖猜測道。
余依擰著眉喝了一口簡糖喂的水,問:“以前什麼名字?”
簡糖說:“就這個名字呀,改了姓而已。以前也姓同音字,是霸王別姬的那個虞。”
余依:“……”
好好好,和“紅綠燈的那個黃”有異曲同工之妙是吧。
不過這麼一來似乎說得通了。
余依說:“我讀高中的時候有個同班同學就做虞姣,難怪我第一次聽這個名字就覺得那麼耳。”
“可是……”余依咬著瓣想了半天,“我記得以前不長這樣啊。”
“整容唄,”簡糖說的云淡風輕,“現在整容技很發達的,不仔細看本看不出來。甚至男人能整人,人能整男人。”
簡糖又洗了幾個陸斯霆讓人送來的車厘子給余依吃。
說道:“不過我覺得你應該好好查一查,如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本該屬于你,憑什麼要便宜了一個小?”
余依里咬著櫻桃核,沉默著垂下眸子。
如果自己真的是于家人,那余欒到底為什麼一直反對在京城發展呢?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91 章
閻王愛上女天師
白梓奚只是隨師父的一個任務,所以去了一個大學。奈何大學太恐怖,宿舍的情殺案,遊泳池裡的毛發,圖書館的黑影……白梓奚表示,這些都不怕。就是覺得身邊的這個學長最可怕。 開始,白梓奚負責捉鬼,學長負責看戲,偶爾幫幫忙;然後,白梓奚還是負責捉鬼,學長開始掐桃花;最後,白梓奚依舊捉鬼,然而某人怒摔板凳,大吼:哪裡來的那麼多爛桃花,連鬼也要來?白梓奚扶腰大笑:誰讓你看戲,不幫忙?
33.8萬字5 34513 -
完結1074 章

我渣了死對頭的哥哥
司西和明七是花城最有名的兩個名媛。兩人是死對頭。司西搶了明七三個男朋友。明七也不甘示弱,趁著酒意,嗶——了司西的哥哥,司南。妹妹欠下的情債,當然應該由哥哥來還。後來,司南忽悠明七:“嫁給我,我妹妹就是你小姑子,作為嫂嫂,你管教小姑子,天經地義。讓她叫你嫂子,她不聽話,你打她罵她,名正言順。”明七:“……”好像有道理。司西:“……”她懷疑,自己可能不是哥哥的親妹妹。
90.2萬字8 35281 -
完結462 章

傅爺的王牌傲妻
寧洲城慕家丟失十五年的小女兒找回來了,小千金被接回來的時灰頭土臉,聽說長得還挺醜。 溫黎剛被帶回慕家,就接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警告。 慕夫人:記住你的身份,永遠不要想和你姐姐爭什麼,你也爭不過。 慕大少爺:我就只有暖希這麼一個妹妹。 慕家小少爺:土包子,出去說你是我姐都覺得丟人極了。 城內所有的雜誌報紙都在嘲諷,慕家孩子個個優秀,這找回來的女兒可是真是難以形容。 溫黎收拾行李搬出慕家兩個月之後,世界科技大賽在寧洲城舉辦,凌晨四點鐘,她住的街道上滿滿噹噹皆是前來求見的豪車車主。 曾經諷刺的人一片嘩然,誰TM的說這姑娘是在窮鄉僻壤長大的,哪個窮鄉僻壤能供出這麼一座大佛來。 兩個月的時間,新聞爆出一張照片,南家養子和慕家找回來的女兒半摟半抱,舉止親暱。 眾人譏諷,這找回來的野丫頭想要飛上枝頭變鳳凰,卻勾搭錯了人。 誰不知道那南家養子可是個沒什麼本事的拖油瓶。 南家晚宴,不計其數的鎂光燈下,南家家主親自上前打開車門,車上下來的人側臉精緻,唇色瀲灩,舉手投足間迷了所有女人的眼。 身著華服的姑娘被他半擁下車,伸出的指尖細白。 “走吧拖油瓶……” 【女主身份複雜,男主隱藏極深,既然是棋逢對手的相遇,怎能不碰出山河破碎的動靜】
176萬字8.46 260012 -
連載120 章

限時閃婚:傅少追妻不要臉
閃婚一個月后的某一晚,他將她封鎖在懷里。她哭:“你這個混蛋!騙子!說好婚后不同房的……”他笑:“我反悔了,你來咬我啊?”從此,他食髓知味,夜夜笙歌……傅言梟,你有錢有權又有顏,可你怎麼就這麼無恥!…
20.6萬字8 11589 -
完結8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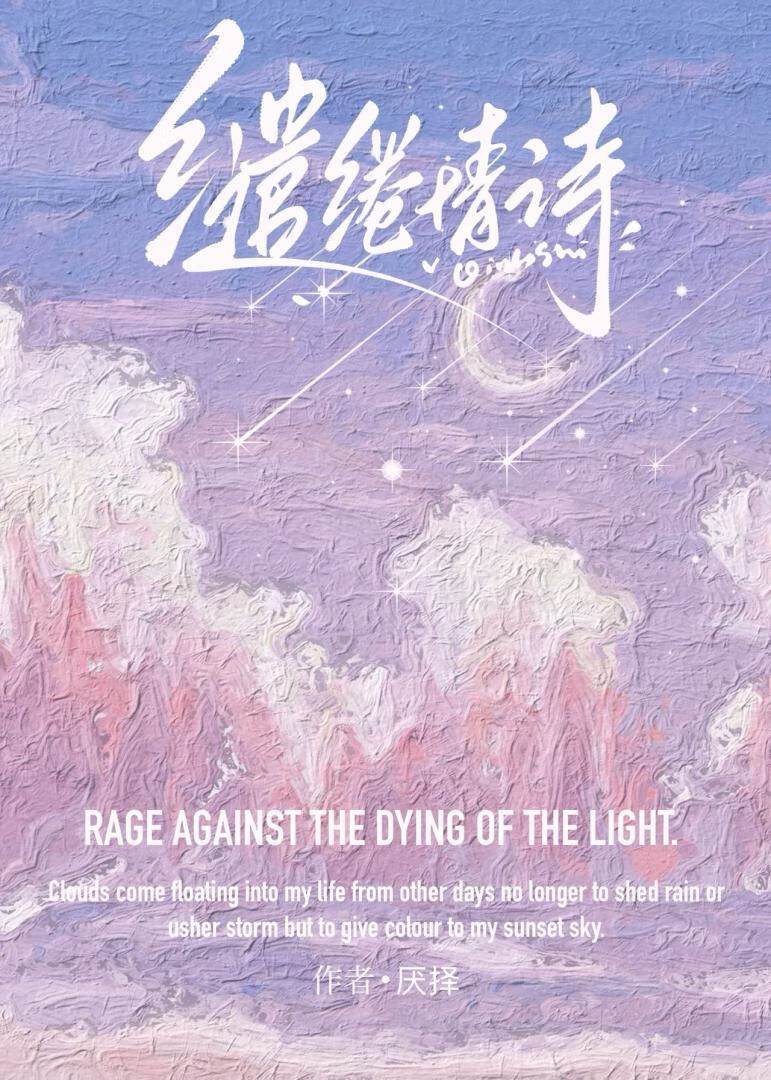
繾綣情詩
謝祈音從小泡在蜜罐子里長大,除了婚姻不能自主外可以說是過得順風順水。 未婚夫顧時年更是北城權貴之首,條件優渥至極。即使兩人毫無感情,也能護她餘生順遂。 可這惹人羨豔的婚姻落在謝祈音眼裏就只是碗夾生米飯。 她本想把這碗飯囫圇吞下去,卻沒想到意外橫生—— 異國他鄉,一夜迷情。 謝祈音不小心和顧時年的小叔顧應淮染上了瓜葛。 偏偏顧應淮是北城名流裏最難搞的角色,不苟言笑,殺伐果決。 謝祈音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小命和婚後生活的幸福自由度,決定瞞着衆人,假裝無事發生。 反正他有他的浪蕩史,她也可以有她的過去。 只是這僥倖的想法在一個月後驟然破碎。 洗手間裏,謝祈音絕望地看着兩條槓的驗孕棒,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 完了,要帶球跑了。 - 再後來。 會所的專屬休息室裏,顧應淮捏着謝祈音細白削瘦的手腕,眼神緩緩掃至她的小腹,神色不明。 “你懷孕了?” “誰的。”
26.2萬字8 1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