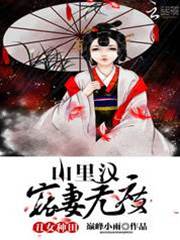《書香世家》 第一百二十四章 一石激起千層浪(三更)
書華再次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四天之後,額頭上劇烈的刺痛令下意識咬了咬牙……呃,可以了?
特意又砸吧了下,再次確定,裡的布團已經被取掉了。更讓到驚喜的,是的手腳也恢復了自由只是的眼睛爲何還是什麼都看不見?好像有什麼東西蓋在的臉上……
擡起久未彈的手臂,緩緩取下蓋在臉上的白帕子,忍著額頭傳來的劇痛,扭頭看了眼自己的環境。
這裡是一間很簡陋的禪房,掌大的地方,除了下這張老舊的矮塌,就只剩下一個靠牆而立的小桌子,桌上放了兩本佛經和一盞油燈。
書華之前沒有猜錯,這裡果真是個寺廟
窗戶和門都是閉著的,屋一片昏暗,書華既張又害怕,可越是這樣,的腦子反倒愈加清晰,就好像有一弦在死死繃著,勉強支撐著那脆弱的神經。
也不知道外面有沒有人把守,如果沒有人的話,現在絕對是一個逃走的絕佳機會。
試著展了一下胳膊與腳,等到手腳都恢復了知覺,正準備從牀上爬起來的時候,外面忽然傳來腳步聲。被嚇得全一僵,立刻恢復原狀,蓋上帕子,裝出一幅的狀態。
期間,還不忘豎起耳朵,小心翼翼地聽外面的靜。
約約,外面傳來了說話的聲音,那人故意低了聲調,書華只能勉強聽到一些隻言片語。在心裡將那些字詞組語句,整理了一遍,猜出了大概的意思:那些綁匪發現意圖自殺,及時救下了,但這裡沒有人懂得醫,沒法子醫治。他們又不能出去請大夫,不然很容易出馬腳,權衡之下,他們選擇了置之不管,任由自生自滅。算一算時候,現在應該沒命了,上頭他們過來看看況。
Advertisement
難怪剛醒來的時候,臉上還蓋了塊帕子,想來是被人當死了。
書華之前想著,他們費盡心思綁來,卻又不殺,必定是因爲有別的用。按理來說,只要還有利用價值,綁匪們就不會輕易讓死掉。可現在看來,事似乎完全朝著和預料相反的方向迅速下去了。
不明白,到底是高估了自己?還是低估了那羣綁匪?還是說,對那羣綁匪而言,這個人質其實也不是很重要……
門被人從外面推開,書華的神經再度繃,屏住呼吸,一不,只恨不得連心跳也能夠按下暫停。
有人進來了,人數似乎還不止一個,據腳步聲,大概有三個的樣子。
其中一個男人低聲說道:“去,看看死了沒?”
然後,書華就聽見有一個很輕很慢的腳步在向自己靠近,等到那人站到自己牀邊的時候,張的全都快要凝固了,心臟猛跳,頻率快得好像馬上就要跳出膛一般
那人將帕子掀開,把手指放到的鼻子下面。
書華咬牙關,就是不呼吸,就是不呼吸……
那人探了許久,都不見有氣息,手下微微一頓。就在書華以爲逃過一劫的時候,那人又拉起的手,竟然探了一下脈搏
饒是書華再厲害,也沒法子讓脈搏停下來。
那人的手很小,不像是個男人,難道是之前照顧的那個啞?
探完脈,那人將的手放回原,回到門口的地方,依依呀呀地發出了很多怪聲。書華停在耳裡,急在心裡,這人莫不是要將撞死的事給那些綁匪?仔細想來,這種可能很大,指不定那個啞就是綁匪的一份子
Advertisement
就在心極度不安的時候,那幾個人互相低語了幾句,然後竟走了出去?
等到聽清了他們遠去的腳步聲,書華這才鬆了口氣。取下蓋在臉上的帕子,大口地呼吸新鮮空氣,心悸猶存,不住汗溼了襟。
再這樣多玩幾次,遲早得心臟病。
不能再在這裡呆下去了,再呆下去的話,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綁匪清醒了,然後繼續綁著做人質,這樣雖然能多活幾天,但估計下場也不會太好;二是一直裝死,不吃不喝,一直裝啊裝啊……裝到有一天,真的掛掉了……
怎麼算都是死路一條,還不如試著搏一搏反正頭都撞了,命也去了半條,老天讓在這個時候醒過來,不就是在給製造機會嗎?
一想到這裡,的狗膽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壯大果然,人在瀕死的時候,潛能是無限的
了一下頭上的傷,手指到厚實的紗布,心裡稍稍安了些,好在那些綁匪還有點良心,幫包紮了一下。小心翼翼地從牀上爬起來,頭上傳來的劇痛令全直冒冷汗,但正因爲如此,才讓更加的清醒,即便是已經四肢無力氣力虛,依舊能夠保持神的高度集中。
在下牀的時候,覺到袖好重,順手往袖裡了一把,居然出了範四送給自己的那把匕首?
在這個環境、這個時刻,這把匕首的出現,無疑爲造就了莫大的信心
地握著匕首,好想要從它上汲取力量一般,閉上眼睛深吸了口氣,等到做好了準備。一步一步朝門口早去,等走到門口的時候,門口忽然響起了開鎖的聲音
這個時候再爬回牀上已經不可能咬了咬牙,迅速躲進門後的死角。
Advertisement
房門被打開,從外面走進來一個穿著青灰道袍的小姑娘,手裡還拿著個兩饅頭。等到完全進來之後,正準備轉關門的那一刻,書華忽然掏出懷中的匕首,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勢,將刀刃架在的脖頸,聲音極低:“刀劍無眼,休要。”
蘇州城,沈家祠堂裡面,所有人的臉都不太好看。
面對綁匪的那封恐嚇信,原本進行得熱火朝天的搜索行不得不進冰凍狀態,雖然府那邊還在竭力搜尋,可是五六天過去了,仍舊沒有得到半點音訊。
大家都很清楚,這種事拖得越久,平安歸來的機率就越低。
商量了許久,也沒有商量出個合適的辦法,萬般無奈,他們只能暫且先回去,隨機應變。
就在事至低谷時,忽然有好多兵找上門來了,以謀逆之罪,一夜之間,沈家所有人都被抓捕獄
這件事如同一個大石頭,落進原本平靜的蘇州城裡,瞬間激起千層巨*。
兩日之後,人們纔得到了從汴京城傳來的消息——陛下臥病在牀,翰林大學士沈書才、翰林院編修何世軒、軍統領嚴等十來名朝廷高,趁陛下昏迷之際,意迷陛下試聽,殘害忠良,意謀反
宣佈這條消息的人是現任蘇州知州雲含鴻,衆所周知,他曾是杜知秋的門生,口中所言實在人心生疑竇。
可謀逆這種事不是鬧著玩的,如若一個不小心,被牽連了進去,到時候就算再怎麼清白,只要從牢獄裡走一遭,也會黑得洗不乾淨
沈家族人作爲謀逆叛黨,被全部關進了大牢,並且不許任何人探。
在這個時候,即便有人心存疑慮,也沒人敢站出來爲他們說上一句話。
Advertisement
牢裡,三叔公被單獨關了起來,另外幾個叔伯關作一間,眷們也都按照份分開關了好幾間。剛開始的時候,憤怒與罵的人比較多,可是到了最後,該罵的都碼完了,力氣也用得差不多了,氣氛漸漸陷一種極其不安的寂靜之中。
約約,聽到了人低了的嗚咽聲,又在寂靜之上蒙了一層揮之不去的無奈。
幾個叔伯一直在商量對策,原本每個人都還能強壯鎮定,可是時間一長,耐心與鎮定都被磨了,被藏了的不安與惶恐盡數發出來,脾氣越來越暴躁。說著說著,他們從冷嘲熱諷變互相對罵,到了最後,五伯與大伯終於忍不住大打出手。
二伯與三伯死命拉著他們,可是怎麼都拉不住。
忍無可忍,四伯一聲怒喝:“別拉他們,讓他們打打不死是他們命大,打死了是他們活該”
二伯與三伯互一眼,猶豫了一下,當真就鬆開了手。大伯與四伯冠不整地站著,死死瞪著對方,看那架勢似乎要從對方上瞪出幾個窟窿才甘心。
這個時候,人的嗚咽聲越來越多,聲音也越來越大……
四伯恨鐵不鋼地看著大伯與五伯:“打啊?怎麼不打了最好把我們這些人都打死了,大家一起死,黃泉路上也有個伴兒”
忽然,哭聲猛地變大,人們全都抱頭痛哭。
整個牢房,都被哭聲淹沒。
這個時候,一直沉默的三叔公忽然開口了,聲音緩慢且厚重:“老2說得好啊,都是一家人,就算死也是死在一起。說不定到了下輩子,咱們還是一家人。”
我一直想做個問卷調查:咳咳,關於書華的房之夜,那段**是詳細寫呢?還是一筆帶過呢……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1079 章

重回香江1982
這一年,華語電影的黃金年代剛剛來臨;這一年,微軟的宏圖霸業剛剛初露崢嶸;這一年,港娛的絕代佳人正值風華正茂;這一年,世界的勢力格局正在風起雲湧;這一年,因為莫軒的到來,一個傳奇的故事開始發生了,一段全新的曆史誕生了。
191.8萬字8.33 92120 -
完結569 章
悍妻攻略
李衡清是通州有名的才子,衆女心中夫君的標準,可惜,如今卻沒一個女子願嫁。 被兄長搶了嬌柔貌美的未婚妻,塞來一個山裡來的野丫頭,也只能默默的認了,誰叫他站不起來呢。 但是,這個丫頭似乎和別的女子很不一樣? 前世揹著弟弟自爆而死的容白,最美的夢想就是生活在一個沒有兇獸和異能者的世界,沒想到眼一閉一睜,真的到這個世界了。 可是,弟弟呢? 於是容白踏上了吃飽、穿暖、攢錢、找弟
102.6萬字8.18 51493 -
連載1048 章
玄幻洪荒之至尊通天
穿越到洪荒世界,成為截教通天教主!肯定要拳打老子、元始,腳踢準提、接引,報封神量劫滅教的大仇!於是,穿越之後,通天就先將老子的天地玄黃玲瓏寶塔給搶了!然後,得至寶,收道侶,立截教,通天威名,名震諸天萬界!
151.4萬字8 14760 -
完結971 章

明朝好丈夫
有知識、有文化、會治病、會殺人.很熱血、很邪惡,很強大,很牛叉.嬌妻如雲,手掌天下,不是很黃,但是很暴力.我是錦衣衛,我是贅婿,我是天子親軍,我是太子教父.我就是我,一個好丈夫,一個好權臣,正德一朝,因我而多姿,因我而精彩.
254.7萬字8.18 113823 -
完結991 章

學霸娘子在農家
飛機失事,一睜眼,她從一個醫科大學的學霸變成了古代小山村的胖丫頭,還嫁給了一個兇巴巴的獵戶。又兇又狠的獵戶是罪臣之後,家徒四壁,窮得叮噹響,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小包子,吃了上頓冇下頓,暴富是不可能暴富的了。母親和妹妹把她當成掃把星,眼中釘,又醜又胖,怎麼還死皮賴臉的活著!阿福心態崩了啊,算了,養家大業她來,醫學博士是白當的嗎,一手醫術出神入化,救死扶傷,成了遠近聞名的神醫。眼看日子越來越好
121.4萬字8 78577 -
連載118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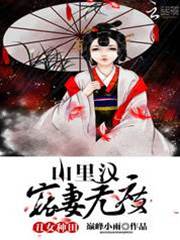
丑女種田:山里漢寵妻無度/錦繡農女種田忙
又胖又傻的丑女楊若晴在村子里備受嘲弄,被訂了娃娃親的男人逼迫跳河。再次醒來,身體里靈魂被頂級特工取代,面對一貧如洗的家境,她帶領全家,從一點一滴辛勤種田,漸漸的發家致富起來。在努力種田的同時,她治好暗傷,身材變好,成了大美人,山里的獵戶漢子在她從丑到美都不離不棄,寵溺無度,比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好多了,豈料獵戶漢子不單純,他的身份竟然不一般。
2080.1萬字8.46 8633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