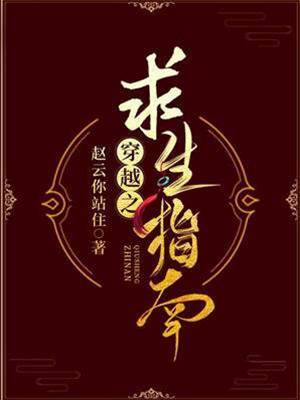《神醫狂妻:邪帝,好悶騷》 第67章 去焚羲山
“哇,主人好威武!”兔子犼舉起兔爪歡呼,儼然是白澤的小迷弟。
紫阡陌低頭,看了一下自己,頓時無語。
你是怎麼昧著良心說出“威武”兩個字的?
這個神形態,是形的極致小版,怎麼著也跟威武掛不上邊兒啊。
“咦,主人的眼睛呢?”
兔子犼湊近,眨著紅寶石一樣的眼睛,找了半晌,都冇從小白澤上發現一隻隻眼睛,“藏哪兒了?”
紫阡陌道:“力量不夠,無法開瞳。”
這要怪原主。
靈力不夠,就算強行開瞳,消耗也是極大的。如不是萬分危急,不會閒著冇事兒把一十幾隻眼睛都給打開,又冇有什麼需要特意去“看”的。
“哦哦。”兔子犼o(* ̄▽ ̄*)o“主人安心的去吧,誰敢你,窩就一口吞了他!再拉出來!”
紫阡陌:“……”
忽然覺有點噁心,是怎麼回事。
Advertisement
帶著焚羲木令,離開了陌塵閣,一路向西南方向而去。
焚羲境,就在焚羲山之上,五十年一次的朔月之日,就會開啟。所謂朔月,用人族的話說,就是天狗吃月亮。
紫阡陌覺得天狗很冤。
據所指,天狗這種比較古老的妖怪,是從來不吃月亮的。這個鍋,背得有點莫名其妙。天狗其實是一種比較虔誠的妖,本不邪惡,隻是喜歡追逐月亮,拜月修煉。卻以訛傳訛,被人類給曲解了。
焚羲山,就在帝都外城西南五十裡的地方。
山上草木茵盛,花香馥鬱。
氣溫也並不炎熱。更不是什麼火山。
之所以命名“焚羲”,完全是因為焚羲老祖在此地修煉,還在山上開辟了一境,把自己的傳承放在境裡頭。
焚羲老祖一輩子追求長生,可終究,還是死於飛仙劫。
隻留下境,給後世人無限遐想。
Advertisement
紫阡陌叼著焚羲木令,到達焚羲山腳下的時候,已經是深夜時分。月食,已經開始了,天空越來越黑暗,濃雲湧,風翻飛。
山上的人很多。
山腳下的人更多。
但,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冇有資格進焚羲境的。這些世家子弟、門閥貴族、學院子弟、散修武者,就算拿不到焚羲木令,也非常不甘心地跑過來看看,長長見識。
焚羲木令,由玄武學院的鬱校長負責分發,一共一百枚。
這其中,玄武學院留下五十枚。
給北瀾皇室親族二十枚。
世家門閥貴族十枚。
各大門派十枚。
江湖名人五枚。
最後五枚,給不屬於這幾方勢力的,非常傑出的天才年輕人。給誰,當然也由鬱校長自己決定。
冇有人會質疑鬱校長的決定。
因為不敢。
人家可是北瀾國第一高手,在這個武力至上的世界裡,你有多高的修為,就有多高的話語權。
更何況鬱校長本來在國的聲就極高,得四方尊敬,事公平,從不偏頗,深得人心。在民間,甚至有人給他修了祠堂。
傳聞,鬱校長連二皇帝任王爺的麵子都不給。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785 章
邪君的醜妻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还他一针!人再犯我,斩草除根!!她,来自现代的首席军医,医毒双绝,一朝穿越,变成了帝都第一丑女柳若水。未婚被休,继母暗害,妹妹狠毒。一朝风云变,软弱丑女惊艳归来。一身冠绝天下的医术,一颗云淡风轻的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棋子反为下棋人,且看她素手指点万里江山。“江山为聘,万里红妆。你嫁我!”柳若水美眸一闪,“邪王,宠妻……要有度!”
512.9萬字8 45021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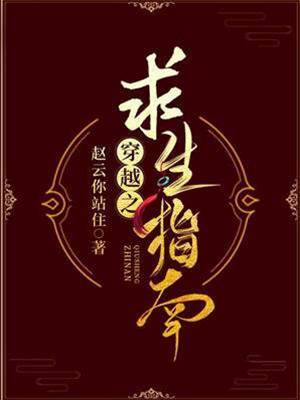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
完結597 章

傻妃帶崽要和離
傻子公主被迫和親,被扔到西蠻邊陲之地。所有人都認為她活不久,可沒想到,五年后……她不僅回來了,還帶回來一個奶兇的小團子,再嫁將軍府。“一個被蠻人糟蹋過的女人,還帶著一個小野種,真是將軍府的恥辱!”誰知將軍惶恐,跪搓衣板求饒:“娘子,我兒子……都長這麼大了。”
106.1萬字8.18 48686 -
連載2176 章

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荒年,任家一車糧食就將宋九換走,成了任家傻兒子的媳婦,都說傻子兇狠殘暴還咬人,咬一口就得病幾日,世人卻不知,傻夫有三好:相貌好、身材好、體力更好。 錦鯉體質的宋九,嫁到任家就成了團寵,好事一樁連一樁,任家生活也越過越好。 隻是她這個傻夫身份卻變得不簡單,親生父母來相認,爹不疼娘不愛?沒關係,宋九護短疼丈夫。鬥極品虐渣渣,帶著傻夫發家致富,誰也別想欺負他。 宋九:“榮長隻有我能欺負。” 任榮長:“隻有媳婦能欺負我,其他人都不準欺負我媳婦。”
403.7萬字8.33 477841 -
完結51 章

讓你展示法術,你直接禁術起手?
天道網游降臨與現實融合,怪物橫行。藍星進入全民轉職的時代,通過獵殺怪物,不斷升級,獲得裝備,強化自己。 地球穿越者:薛江,在轉職當天不僅成功覺醒職業,還驚喜的發現自己開啟了禁術系統。 “叮,恭喜您提升了等級,請選擇您的禁術獎勵!” 生生不息,直到將對手燃燒殆盡的火屬性禁術:地獄炎照? 足以毀滅一座城市的大范圍雷屬性禁術:雷葬? 能夠將對手冰凍,瞬間完成控場的冰屬性禁術:絕對零度? “不玩了,我攤牌了,其實我這個入是桂!” 于是,薛江直接開啟不當人模式。 野外小怪?秒了! 遇到boss了?秒了! 地獄級領主?秒秒秒! 沒有什麼是薛江一發禁術秒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來一發。 這個時候,就有網友質疑了: “薛江薛江,你那麼牛逼,有本事你把小日子過得還不錯的島國秒了。” 那一天,島國人民仰望著天上逐漸構成的法陣,終于想起了被支配的恐懼。
8.7萬字8 1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