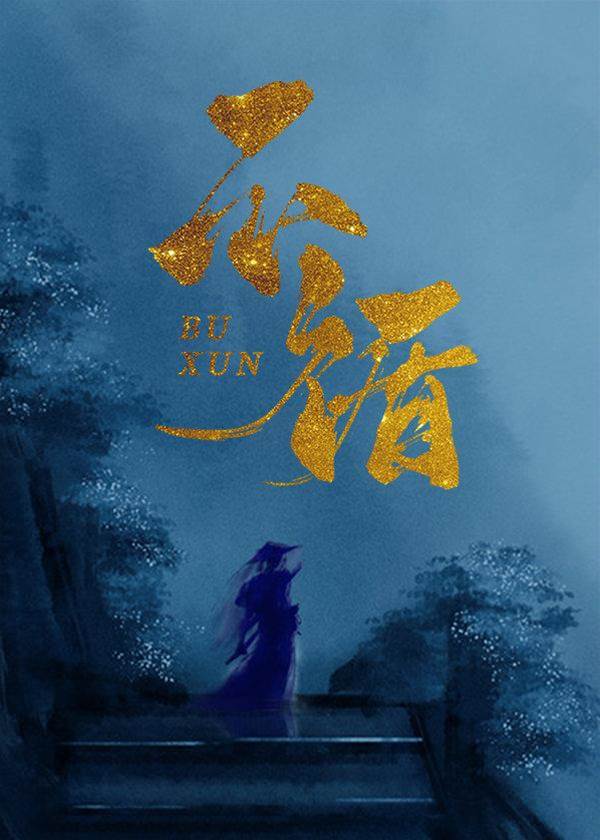《休夫》 番外:小公子的情竇初開(1)
初春的夜一場倒春寒後,夜裡的風刮在臉上,猶如刀割,梅山之上的青竹小院裡頭,現下,早已漆黑一片,不見一燈,而在門外,裹著一墨黑鬥篷的年,現下,藏在這月之下,小心翼翼的推開了竹們,打算不聲的,不驚醒了任何一個人。書趣樓()
躡手躡腳的向前行走時,鬥篷下的他,因為張額頭鼻尖已經沁出了一層薄汗,鬥篷下,年有著一張俊非凡的臉,潔白皙的臉龐,斜飛英的一雙劍眉,十四五歲的年紀,卻已經有著一種人的氣勢。
年好不容易在消無聲息時,走到了自己的房間之中,長舒了一口氣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壞笑之時,房的燈卻在瞬間點亮,正院側院,三進的院子裡頭,燈火通明,而一旁,紫檀木圓椅旁的杌子上,先下正端坐著一個橫眉冷目,銀牙咬著的艷婦人,邊跟著的則是長得一對一模一樣的俏麗姑娘,現下,這麼一群人就這麼的盯著這位年。
「小爺回來的早,這天都還沒亮呢,你怎麼不幹脆死在外頭不要回來了!」沈輕舞角勾起一抹很是溫和的笑,角微揚,滿臉的冷意,隨後,手裡的一把戒尺便是狠狠的敲打在了旁的圓木桌上,戒尺打的圓木桌椅「乓乓乓」的響,聽得一旁的顧欣沅和顧欣汝這對雙胞胎姐妹花,嚇得越發把皮給綳得的。
「說吧,小爺這次又跟著誰出去見識了大場麵,見識了些什麼連你親娘都不知道的,出來了,也讓你娘樂嗬樂嗬。」沈輕舞繃著一張臉,看著顧曄,手不住的挲著戒尺的邊緣,磨牙謔謔著。
「我就是跟他們出去喝了一頓酒,他們說,海晏街那兒有世界上最的溫鄉,與最好喝的人釀,我就是去看了下,我也不知道那兒是青樓,後來知道了,我就趕的回來了,可回來了,又怕您生氣,所以我這纔想著的回來,母親,我都招了,您能不能不罰我呀!」
Advertisement
顧曄在見到沈輕舞這般氣惱的神之後,趕的向著母親下跪認錯,十分可憐的看著自己的母親說道。
「把手舉起來。」沈輕舞努了努,眉頭鎖著,卻沒看自己兒子的求,讓他把手抬起來,隨後一把戒尺直接到了邊的大兒手裡頭。
「長兄如父,你為兄長竟然自己不學好,在外頭跟著人出去花天酒地,小小年紀,就已經出青樓,開始喝酒貪杯,你父親十四歲那會已經在戰場之上殺敵為自己建功立業,你現在你父親留下的蒙蔭,卻學的這樣紈絝子弟的作風,這些年,教給你的道理白教了是不是?欣沅,打,好好的給你哥哥長長記,你們也記住了,膽敢在外麵胡作非為,這算輕的。」
火冒三丈的沈輕舞隻對著自己的兒子,厲聲嗬斥著,顧曄自舞槍弄劍,不讀書,不文人的迂腐之氣,顧靖風樂意隨他,便將他放到了宋至的軍中,跟著那些軍中的將士們舞槍弄棒,本事倒是學的不,可這陋習卻也沾染了不回,小小年紀學會了好酒貪杯,好江湖義氣,讓沈輕舞很是頭痛。
今兒個說好了日中到家,沈輕舞親自下廚做了滿桌子的菜等他回家,可等了到晚都不曾見他回來,派了王安出去打聽,聽到的就是小公子跟著人去花樓這幾個字,氣急了的沈輕舞連飯都沒吃,就這麼端坐在這兒等著這位小公子回家。
「母親……」顧欣沅抓著那戒尺手有些發抖,又有些捨不得,隻看著沈輕舞,猶豫不決著。
「怎麼了,你捨不得,那就給我來打。」見兒在那兒帶著哭腔的直皺眉,沈輕舞自了手,對著大兒道。
顧欣沅抿了,最終還是沒捨得把這手裡的戒尺到沈輕舞的手裡,知道,自己的母親要是真的發了怒,那當真不論是誰都勸說不了的,下手,自然也不會有任何的一點留。
Advertisement
「哥哥,我打的輕些,你把樣子做足了。」顧欣沅咬著牙,蹲下子,小聲的對著顧曄道。
「再嘀咕,是不是想要我連帶著你們兩個一起打,一個為長兄,一個為長姐,還想著竄通一氣的幫著你哥哥是不是,這麼多人深更半夜的不能夠睡是為了什麼,是因為你哥哥,你看著你哥哥這次好像是知道錯誤早早的回了來,可這次帶著的是去了青樓,那麼下次呢,要是有人帶著他去鳴狗盜的事,本來不及懸崖勒馬的時候,該怎麼辦,你們可曾想過?」
「母親從不乾涉你們到底是否文武雙全,是否在學問上,琴棋書畫上高人一等,是這京中的翹楚,母親隻要你們做一個正大明的人,就這一點,你為兄長,卻還要給兩個妹妹起個壞頭,你可知錯。」
沈輕舞氣急了,臉現下已經變了鐵青,咬著牙,尋常溫和的眼眸之中現下充滿著冰冷。
「兒子知錯,兒子以後一定再去那種煙花場所,讓母親擔憂,請母親不要生氣。」顧曄見沈輕舞現下是當真的發怒,又聽得對於自己的諄諄教誨之後,自對著沈輕舞磕了一個頭後,便從自己的妹妹手中接過了那一把戒尺,將它奉於沈輕舞麵前「請母親教誨。」說罷,便是出了手,等著沈輕舞,親手的打下去。
沈輕舞將那一把戒尺接過,沒有毫的猶豫,便是用盡了力氣的兩記,打在了顧曄的手心,狠厲的兩下,打的顧曄手心火辣辣的疼,鼻頭一酸,眼淚便已經滾在了裡頭。
「當初你舞刀弄槍,你父親把你送到軍營裡頭去,我隨了他,不曾管你,可現在,我發現你越發的沒了規矩,讀了兩年聖賢書,一點道理都不懂了,為兄長還沒有你的兩個妹妹來的懂事,明兒個,我便讓你王叔給你準備了衫,你便去博軒裡頭,跟著師傅好好的把禮儀仁義這些個道理學個遍,母親不要你考狀元,隻要你知曉些道理,免得將來走了歪路,再有幾年你便要行弱冠禮,你的婚事,你的姨父前些時候也與你父親略提了提,母親現在覺得,若在不讓你好好學學聖人之言,往後,你就真的是要了隻會打架好勇的街邊無賴,往後,誰嫁給你,你也隻是坑害了人家,這件事,你隻有聽的份做的份,沒有你反駁的份,若是懂了,那你就回去休息,明兒個早早的起來,就跟著你王叔去博軒,你記著,你要敢再裡頭闖一點的禍,小心我把鞭子沾好了茱萸水來等著你!」
Advertisement
打在兒疼在娘心,看著顧曄手心上那兩記紅的印子,沈輕舞亦是無比的心疼,忍著心裡頭的不忍,隻咬著牙,將把顧曄送進博軒的事與他下了命令道。
顧曄最怕的便是博軒學聖人之言的事,從前與顧靖風與他提過無數次,可每次他都能夠混過去,今兒個,顧曄知道自己混不過去了,他去到青樓,就算什麼都沒做,就已經犯了母親的底線,所以,他隻能乖順的點了點頭,隨後隻端著自己那被打痛的手,就這麼默默的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折騰了一晚上的顧曄連澡都沒洗,就這麼囫圇躺在了自己的架子床上沉沉的睡去,手還這麼向上出微張著,上頭紅的印記未褪,而手心裏麵卻是長年累月習武練劍所留下的厚厚一層繭子。
在這三進的小院子又陷安寧與沉睡之中後,沈輕舞小心的帶著葯,自己推開了顧曄的房門,看著他睏倦沉睡的模樣,沈輕舞將圓缽的消腫化瘀的膏藥抹開,一點一點塗抹在了顧曄了戒尺的紅淤青那兒,幫其抹勻之後,看著他沉睡的容,深吸了一口氣,長長的輕嘆一聲著。
「睡了?」幫著顧曄把被子蓋好後,沈輕舞又輕手輕腳的幫其合上門,自回了自己的院子,彼時,床榻上半靠在後枕上的顧靖風放下了手中拿著的雜記,對著沈輕舞出聲道。
「睡了,你說,表兄已經為顧曄選定了親的人選,是誰家的姑娘?」沈輕舞點了點頭,撐著頭看著顧靖風道。
這些年,顧靖風說是掛名坐著這鎮國大將軍的位置,可該他乾的事,他一樣也沒乾,如今四海昇平,是個十足的太平盛世,可顧靖風在皇帝的麵前,依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前些時候他進宮,皇帝便與他說起了關於顧曄的婚事。
Advertisement
「選得是左翼前鋒營統領家的兒,我看過那丫頭的畫像,模樣十分俊俏,是個文武雙全的丫頭,前些日子,已經扮男裝去到博軒中以學子的份在那兒聽課,和曄兒,倒是十分互補,皇上有意栽培曄兒將來接我的班,選得人家自然不會錯!」
「所以你們這對君臣,現在是打算來個什麼,變相相親,日久深,顧靖風,你連親兒子都算計,你是不是親爹?」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63 章

丞相府的小娘子
沈梨穿越了,穿到一窮二白,剛死了老爹的沈家。上有瞎眼老母,下有三歲幼兒,沈梨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她擼起袖子,擺攤種菜,教書育人,不僅日子越過越紅火,就連桃花也越來越多,甚至有人上趕著給孩子做后爹。某男人怒了!向來清冷禁欲的他撒著嬌粘上去:“娘子,我才是你的夫君~”沈梨:“不,你不是,別瞎說!”某人眼神幽怨:“可是,你這個兒子,好像是我的種。”沈梨糾結:孩子親爹找上門來了,可是孩子已經給自己找好后爹了怎麼辦?
87.5萬字8 21269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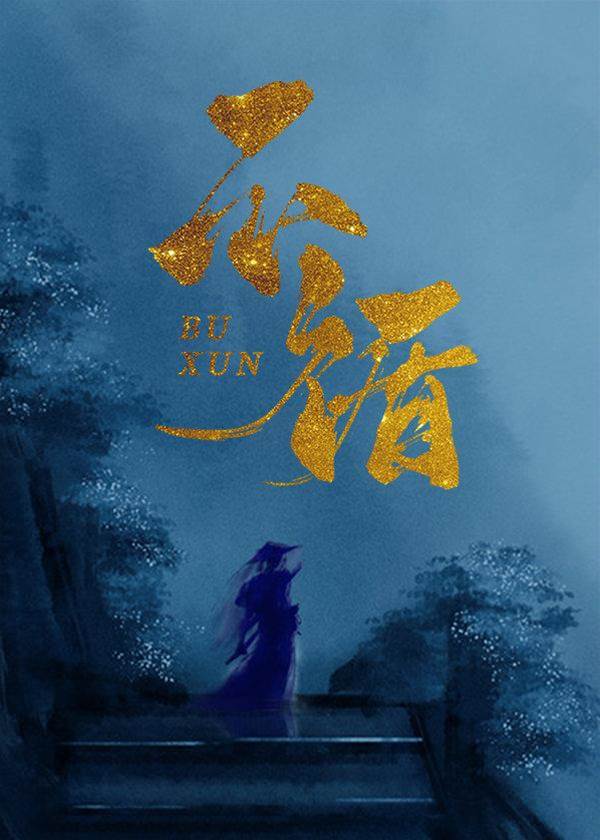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432 章
舔狗太纏人,王爺他又吃醋了!
前一世,柳落櫻錯將惡人當良人,落得個焚火自戕,慘死在冷宮無人收屍的下場。 重生後,她強勢逆襲! 抱緊上一世兵部尚書的大腿,虐得渣男後悔不已。 鬥惡毒伯母,虐心狠表妹,她毫不留情! 唯有在對待身份神秘的私生子二表哥時,那顆冰冷的心才會露出不一樣的柔情。 哪曾想,報完仇,大腿卻不放過她了。 洛霆:“櫻兒,這輩子,你只能是我的妻......”
76.7萬字8 9086 -
完結207 章

都說她不配,偏偏清冷權臣他超愛
【先婚后愛+古言+女主前期只想走腎、經常占男主便宜+共同成長】江照月穿書了。 穿成男配愚蠢惡毒的前妻。 原主“戰績”喜人: 虐待下人。 不敬公婆。 帶著一筆銀錢,和一個窮舉子私奔。 被賣進青樓。 得了臟病,在極其痛苦中死去。 這……這是原主的命,不是她江照月的命! 她可不管什麼劇情不劇情,該吃吃、該喝喝、該罵人罵人、該打人打人、該勾引男配就勾引男配。 一段時間后…… 下人:二奶奶是世間最好的主子。 公婆:兒媳聰慧賢良啊。 窮舉子:我從未見過這麼可怕的女人! 男配摟著她道:時辰尚早,不如你再勾我一次? 江照月:???
39.5萬字8 13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