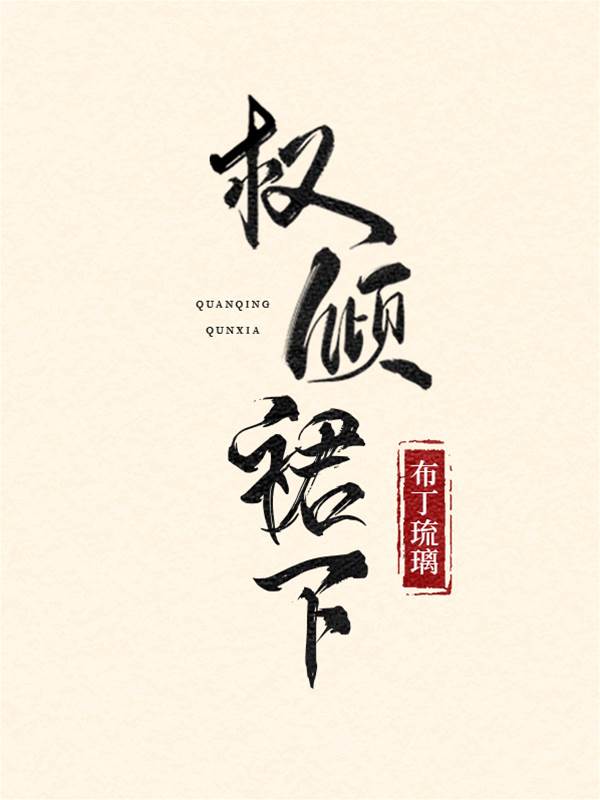《重生之將門毒後》 第147章 折花贈佳人
謝長武一時不知道該害怕還是該大罵明安公主蠢貨,明安公主竟然將自己的名諱就這麼說了出來。不過轉念一想,今日之事明顯就是個陷阱,對方怕是早已知道了明安公主的份,否則明安公主接到的那封信也就說不清了。
可是此時他們又能如何?謝長武心道,總不能在這裡大聲呼救,眼下能不能被人聽到且不說,便是真的被人發現,他一個明齊的臣子,和秦國公主半夜三更來萬禮湖,渾上下都是也說不清了。
進退維谷,謝長武反倒冷靜下來。他看著對方,冷笑道:“謀害一國公主,這個罪名可是不輕。閣下若是不怕死的話,大可以一試。嚐嚐被人追殺到天涯海角,如喪家之犬一般惶惶不可終日是什麼覺。”
有謝長武說話,明安公主心中稍稍安,雖然也怕,可到底仗著一國公主份旁人不敢拿如何。就道:“不錯,本宮這樣的份,不是你們這些人能的起的。今日你們要是敢本宮,來日秦國皇室定會將你們挫骨揚灰!”
“是嗎?”黑人羣中,忽然突兀響起了一個男聲。
那聲音低沉帶著幾分沙啞,卻彷彿冬日裡溫好的酒般甘醇,讓人覺得極爲聽悅耳。明安公主和謝長武看去,便見黑人中,有一個人往前走了出來。
因著都是黑人,方纔他們也未曾看清楚。眼下倒覺得這黑人和旁人有些不一樣,在微弱的火摺子映照下,此人的量明顯更高更拔一些,便是和這些黑人一樣的裝束,亦是掩飾不了骨子裡的貴氣人,彷彿一眼就能同別人辨別出來似的。
“你是誰?”明安公主怒道:“你難道不知道本宮是誰嗎?本宮乃大秦的公主,本宮一聲令下,就能讓你們這羣人全都掉了腦袋!”
Advertisement
聞言,那黑人頓了頓,卻是輕輕笑起來。即便是蒙著布巾看不到對方的臉,分明他的笑聲也是愉悅的,可謝長武和明安公主卻似乎能隔著這布巾瞧見對方面上的嘲諷。
明安公主面漲得通紅,還從未被人這般不放在眼裡過。可是心底又有一些疑,總覺得這人的聲音似曾相識,似乎在哪裡聽過一般,怎麼也想不起來。問:“你笑什麼?”
“笑你不自量力。”
“你!”明安公主大怒。
“區區秦國公主,算得了什麼?”那人聲音好聽,話說的卻惡劣:“死了,照樣白骨一堆。”
“大膽!”明安公主喝道。
“本王就是大膽,你又如何?”那人不不慢道。
本王?明安公主一愣,電石火間突然想到了另一人,那人亦是如此讓人著迷的聲音,擡眼看去,蒙著面巾看不到人臉,在外頭的一雙眼睛卻是如桃花釀一般醉人,彷彿眼中都是含的笑意,可認真去看,又盡是冷漠。
“你是……睿王殿下!”明安公主失聲道。
睿王殿下?謝長武猛地朝黑人看去,他也覺得這黑人給他一種悉的覺,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可萬萬沒想到竟然是大涼的睿王殿下。
黑人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看在二人眼中便是默認的意思。謝長武猶豫了一下,問:“睿王殿下來這裡,所爲何事?”
便是謝長武想破腦袋也想不出爲什麼睿王會出現在這裡,要知道睿王和他可是八竿子也打不著的關係,和明安公主似乎也沒什麼往來,那他爲什麼會出現在這裡?又想幹什麼?
明安公主自從認出了面前人是睿王之後,方纔的恐懼倒是盡數消散,轉眼盡是,輕聲道:“睿王殿下深夜來此,所爲何事呢?”
Advertisement
謝長武覺得明安公主是真的蠢,對方既然都殺了他們二人帶來的護衛,顯然便不是過來敘舊的。況且這個睿王給人的覺極爲危險,謝長武心中有些發。
睿王沒有理會明安公主,反是看向謝長武,道:“你似乎有話要問本王?”
謝長武勉強笑道:“敢問殿下,可曾見過我三弟?”
那封信是謝長朝的字跡,來人卻是睿王,莫非謝長朝落了睿王手中?謝長朝和睿王又有什麼過節?
黑人一笑:“見過。”
謝長武瞪大眼睛:“他……”
“被我殺了。”
此話一出,明安公主和謝長武齊齊一愣,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
頓了許久,謝長武才問:“睿王殿下爲何要殺我三弟?”
“他惹了不該惹的人。”
惹了不該惹的人?謝長武心中狐疑,誰,莫非是沈妙嗎?謝長朝如今得罪的人便只有沈妙了。可睿王又爲何要替沈妙出頭,睿王和沈傢俬下里有什麼?謝長武覺得自己彷彿窺見了一個驚天的冰山一角,卻因爲看不到全貌而將自己的腦子攪得一團。
“睿王殿下前來,不知所爲何事?”明安公主被對方殺了謝長朝一事激的終於清醒過來,似乎終於覺察到這夜籠罩下的危險,試探的開口,心卻開始劇烈的跳起來。
那人的聲音和如風,卻又像是萬禮湖上自長空落下的冰雪,看著麗,卻令人發寒。他道:“這樣好的景,做埋骨之地不是很好?”
謝長武道:“你爲何要這麼做?我與你無冤無仇,你不能放過我們?”明知道對方了殺心,自己卻沒有退路,謝長武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懼,大呼出聲。
Advertisement
“無冤無仇?”對方好似聽到了什麼笑話,道:“你未免太過健忘了。”
“謝長武,這麼多年,你和你愚蠢的弟弟一樣不知長進。”他道。
謝長武覺得這話有些悉,接著,他就看到那黑人慢慢的扯下臉上蒙著的面巾來。
即使是極其微弱的火摺子芒,都不能將這人的彩掩蓋。長眉鬢,鼻若懸膽,薄脣如往常一般帶著嘲諷的笑意,一雙桃花眼卻好似隔了漫長的時看過來,分明是極溫和的笑意,卻帶著淡淡的輕蔑。
那是謝長武終其一生的噩夢。
“謝景行!”
明安公主正沉迷於這男子勾魂奪魄的容之中,想著睿王面下的臉果真如傳言一般驚人,卻被謝長朝這一聲打斷了思索。
謝景行?那不是臨安侯府,兩年前戰死沙場,令人扼腕嘆息的謝家嫡子嗎?
“難爲你還記得我。”謝景行微微一笑,那原本俊的笑容看在謝長朝的眼中卻分外可怕。他轉就要逃跑,那是從骨子裡帶出來的本能,就像獵遇到危險後下意識的反應,腦中不會思考這可不可以。
他的子被人按住了,亦是被人堵住,全上下都彈不得。和他同樣遭遇的還有明安公主。
畫舫在萬禮湖的中央,深夜子時,街道上空無一人,便是遠亮著燈火的酒樓,也被笙歌曼舞淹沒了這微妙的靜,就像是投了一塊石子在潭水裡,連水花都激不起來一朵,便慢慢的沉沒下去。
謝長朝和明安公主被黑人們按著,眼睜睜的看著那爲首之人轉走出了畫舫。
即便是在冰面上,他亦是走的風姿盎然,而他的聲音隔著萬禮湖上漫天的大雪,如冬日的寒冰一般人涼到心裡。
Advertisement
“遊戲結束了。”
……
沈妙自夢中驚醒。
不知爲何,今夜睡得竟是有幾分煩躁,到了此刻,乾脆便是醒了過來。外頭沒有一一毫的靜,想來正是深夜好眠時。
了額心,覺得腦袋有些生疼,卻是無論如何都再也睡不著了。屋中的爐火燒的很旺,卻覺得中有些生悶,想了想,乾脆從一邊拿過外裳隨意披著,走到窗前將窗戶打開,想要散一散心中的悶氣。
窗戶被打開,窗前的大樹樹影婆娑,外頭還在下雪,大片大片的雪花落下來,有的吹到屋裡去,沈妙出一隻手,看那雪花在掌心漸漸融化。
不知爲何,竟然生出了幾分孤獨。
在這樣的夜裡,無心睡眠,獨自一人披看雪,實在是有幾分造作。可是的腦子裡卻又不由自主的想到前生的一些事,譬如婉瑜,譬如傅明,便覺得藏匿在心裡刻意被掩蓋的舊時傷痕作痛起來。
一小朵花從天上墜落下來,恰好落在沈妙攤開的掌心裡。沈妙一愣,藉著樹上掛著的風燈籠看的清楚,並非是什麼雪花,而是一朵嫣紅的海棠。
這季節,哪裡會有什麼海棠?這樹也不是長海棠的啊?
沈妙下意識的擡頭看去,便見那樹影綽綽中,正躺著一人,雙手支在腦後,如年人一般愜意。見看來,便微微低頭,自上而下俯視沈妙,眉目英俊,笑的玩世不恭,挑眉道:“發什麼呆?”
沈妙:“你在這裡做什麼?”
謝景行好端端的沒事跑別人家院子樹上睡覺,大涼的睿王這好似乎也過於令人稱奇。
“睡不著。”那人嘆了口氣,忽而從樹上掠下,落到沈妙面前,隔著窗,一人在窗外,一人在窗裡。他朝沈妙掌心努了努:“折了支花,過來送你,又怕你睡著了,所以在樹上等你醒來。”
胡言語,沈妙白了他一眼,卻見這人雖是笑意盈盈,今日卻看起來不似往日神。
心裡一,不知爲何,沈妙便口而出:“進來吧,屋裡有剩的點心。”
------題外話------
謝哥哥一生氣就去殺人滅口,好壞= ̄w ̄=
加油!妹子在朝你招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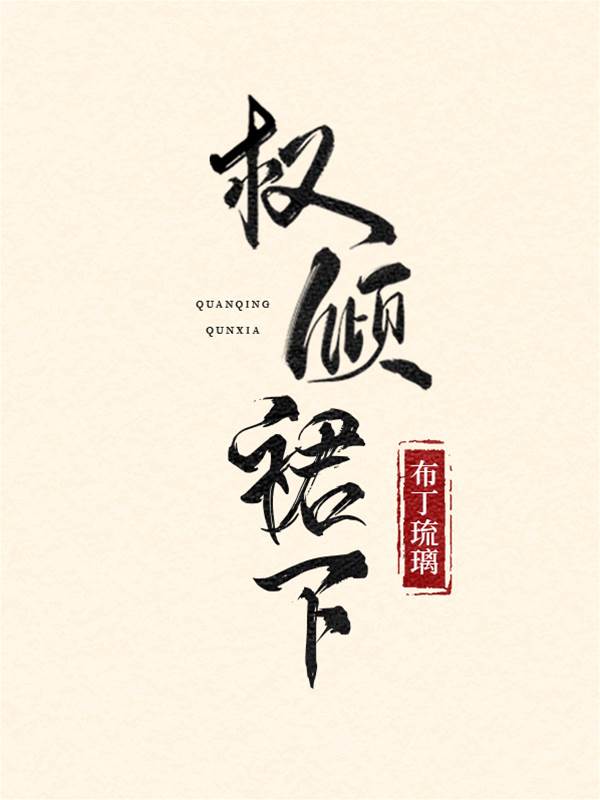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967 章
神醫王妃她拽翻天了
秦語穿越成炮灰女配,一來就遇極品神秘美男。 秦語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因為相遇是妹妹陷害,大好婚約,也不過是她的催命符。 秦語輕笑:渣渣們,顫抖吧! 誰知那令人聞風喪膽的燕王,卻整天黏在她身邊.
170.1萬字8 23384 -
完結119 章

太子妃實在美麗
尚書府的六姑娘姜荔雪實在貌美,白雪面孔,粉肌玉質,賞花宴上的驚鴻一現,不久之後便得皇后賜婚入了東宮。 只是聽說太子殿下不好女色,弱冠之年,東宮裏連個侍妾都沒養,貴女們一邊羨慕姜荔雪,一邊等着看她的笑話。 * 洞房花燭夜,太子謝珣擰着眉頭挑開了新娘的蓋頭,對上一張過分美麗的臉,紅脣微張,眼神清澈而迷茫。 謝珣:平平無奇的美人罷了,不喜歡。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晚上,她換上一身薄如蟬翼的輕紗,紅着臉磨磨蹭蹭來到他的面前,笨手笨腳地撩撥他。 謝珣沉眸看着她胡鬧,而後拂袖離開。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月,她遲遲沒來, 謝珣闔目裝睡,等得有些不耐煩:她怎麼還不來撩孤? * 偏殿耳房中,姜荔雪正埋頭製作通草花,貼身宮女又一次提醒她:主子,太子殿下已經到寢殿好一會兒了。 滿桌的紛亂中擡起一張玉琢似的小臉,姜荔雪鼓了鼓雪腮,不情願道:好吧,我去把他噁心走了再回來… 窗外偷聽的謝珣:……
36.6萬字8 7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