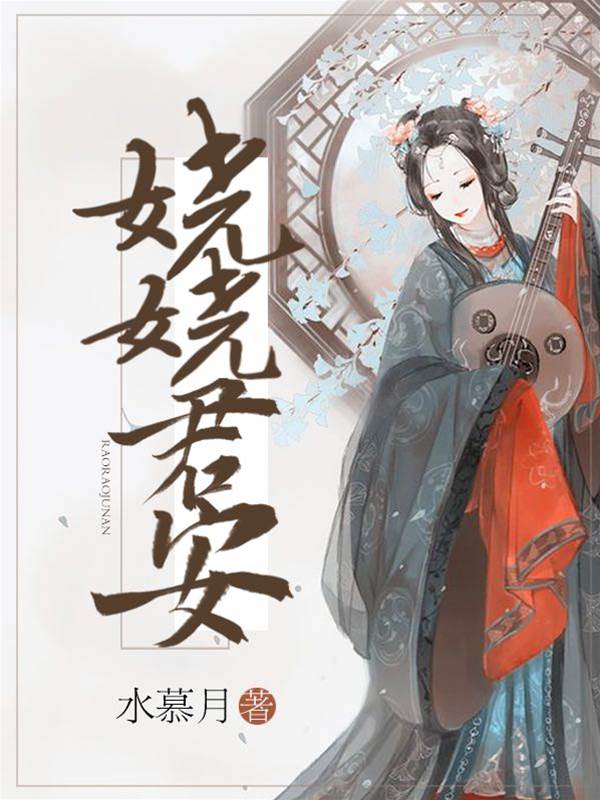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邪王追妻:神醫狂妃不好惹》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章 背後搞事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章背後搞事
蕭容雋輕笑一聲並沒有多言。
他用兩隻手捧住阮清歌的下顎,輕聲詢問道:
「夫人此言,何意可是?懷疑什麼?」
阮清歌微瞇起眼眸。
「我懷疑你背著我搞事!」
說著阮清歌麵上滿是不厭其煩。
「為什麼你總是不告知於我?直白的說出來不好嗎?」
蕭容雋輕笑著搖了搖頭,抬起指尖著阮清歌的小腦袋瓜。
「這不是想讓你自己理解,讓你變得更加聰明嗎?我這樣有何不可?」
阮清歌眉頭皺,「難道我這聰明的腦袋還是你練就的不,若是這般到來,我還要謝你了,是嗎?」
蕭容雋垂眸在阮清歌的邊了個香,心悅道:「好了,夫人莫要生氣。
其實對於你所說的事,我並不知,不過是猜測罷了。我也並沒有什麼好瞞的。」
阮清歌微瞇積眼眸看去。
「難道你說這句話的時候心裡就不心虛嗎?咱們著良心說話不好嗎?」
當阮清歌說完這句話,蕭容雋卻是抬手向手所在的位置。
「好,咱們著良心說話,當真沒有騙過夫人。」
阮清歌垂眸看去,麵紅,一把將蕭容雋的手臂甩開。
用一本正經的語氣卻做著這樣的作,怕是隻有蕭容雋能夠幹得出來。
見阮清歌麵上有些惱火,蕭容雋抬起手指放在腦側。
「夫人!我與你發誓,當真沒有做瞞你何事。」
雖然蕭容雋這麼說著,但是在心中卻是告知自己。
『就算說出來的,就不算是欺瞞,雖然可能存在一些偏差。』
阮清歌凝重地向著蕭容雋看了半晌,最終還是點了點頭。
「好吧,我暫且就相信你。」
阮清歌眉頭微皺,「那麼接下來我們該做何?」
蕭容雋抬起手臂,索著下。
Advertisement
凝視阮清歌片刻,嘆息道:「既然你心中已經有計劃,為何還要詢問我?」
阮清歌眉心了。
「可現在還不知蕭淩是否站在我們側。
若他與之反目,咱們也好進行下一步。」
蕭容雋抬起手指在空中搖了搖。
「不,你要知道,蕭淩是一定會答應你的。」
阮清歌疑看去,「你為何能夠這般肯定。」
蕭容雋爽朗一笑,「他現在已經沒有靠山,既然認出了你。
他心中應該也已經有算。
畢竟跟任何人親不如跟自己人親,總的來說我也是他的叔叔。」
阮清歌聞聲在暗撇了撇。
這叔叔讓蕭容雋說的還真是自然。
真的不說,當初這叔叔竟是搶了侄子的媳婦。
雖然這件事並不關蕭容雋,但是兩男相爭一。
自然是引起一番鬥爭。
而蕭淩還是輸得最慘的那一個。
蕭容雋抬手阮清歌微皺的眉心。
「好了,不要再想了,今晚回去嗎?」
阮清歌點了點頭,「我此次前來便是與你說起這件事,既然你沒有旁的意見,那麼我便在宮中與蕭淩涉。」
蕭容雋點了點頭,麵上卻更顯凝重。
「你要看好你自己,我不在你邊。
更多勞累一些。」
阮清歌輕輕一笑,拍了拍懷中的錢袋。
「說那些虛的不如用實際行來證明。」
蕭容雋挑起眉心。
「你是知道的,我這錢財都屬於你。」
阮清歌撇了撇角,站起,向著門口走去,回道:「不與你吹噓,我去看看若白就離開了。」
蕭容雋頷首,「若白還沒有醒來,你看看也應該的。」
阮清歌一邊行走,一邊凝重看去,「還未醒來?一點蘇醒的跡象都沒有嗎?」
「沒有。」
阮清歌嘆息一聲,走到門口,將之開啟,一道不小的氣流自裡麵傳出,將阮清歌垂在麵頰兩側的長發吹揚。
Advertisement
阮清歌微微瞇起眼眸看去,隻見阮若白被一道金籠罩著全。
皺眉向旁看去,隻見蕭容雋眼底亦是詫異。
阮清歌出手指指了指前方,「我不再的時候也是這般?」
蕭容雋搖頭,「今晚才如此,晚間我來檢視並未。」
阮清歌緩步上前,卻是被那一道金給阻攔,並不能近。
蕭容雋將阮清歌拉了回來,但在那一瞬間,金所覆蓋之傳出如劍刃一般的白,向著阮清歌去。
阮清歌剛轉,那簇竟是將的手臂劃破,頓時腥味充斥著整個屋。
阮清歌大驚,這還帶有攻擊!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阮若白這是在經歷著什麼?
蕭容雋與阮清歌對視一眼,均是覺得這件事不簡單。
蕭容雋連忙這在竹櫃上一陣翻找,找出紗布包裹著阮清歌的手臂。
阮清歌搖了搖頭,「我不能包紮,太過於顯眼。」
說著從襟拿出止藥以及諸靈,不多時傷口恢復,但是腥味還在,隻好拿出掩蓋氣味的藥,將之覆蓋。
而那道金也吸引了不人前來。
「我的天!這是什麼東西!?」
穆湘從人群中了進來,站在阮清歌側。
想要上前,卻是被阮清歌給拽住,「這有危險,莫要上前。」
「唉…」
阮清歌皺眉看去,卻是並未瞧見穆湘。
穆湘疑看著阮清歌,「你這麼看著我作何?」
「該來的還是要來…」
那道聲音再次想起,阮清歌銳利眼眸掃視周圍,卻是並未找到聲源,那聲音好似隔空傳遞一般。
蕭容雋似乎看出阮清歌的不同,站在的側,拽住了的小手。
阮清歌到那抹力量,將心驚下。
轉對著眾人道:「多派人手將這裡看管,發現任何問題都要告訴我。」
Advertisement
花無邪點了點頭,沐訴之卻是凝重看向阮清歌,一副言又止的模樣。
阮清歌眼眸閃爍,隨之拉著蕭容雋向著遠走去,大門關上,徹底將視線隔絕。
阮清歌與蕭容雋回到屋,蕭容雋拿出手帕拭著阮清歌額頭上的薄汗,「剛纔是怎麼了?為何那般表?」
阮清歌撲倒蕭容雋懷中,抱住了他的腰。
知道,就算自己說出來,蕭容雋是一定不會相信的,甚至會將當怪。
但是…剛剛那道聲音是的確存在的,清清楚楚就在耳邊炸開。
可那聲音…竟是帶著一悉,可阮清歌就算有過耳不忘的本領也想不起來。
「你到底怎麼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229 章
帝凰之神醫棄妃
大婚當天,她在郊外醒來,在衆人的鄙夷下毅然地踏入皇城…她是無父無母任人欺凌的孤女,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血王爺.如此天差地別的兩人,卻陰差陽錯地相遇.一件錦衣,遮她一身污穢,換她一世情深.21世紀天才女軍醫將身心託付,爲鐵血王爺傾盡一切,卻不想生死關頭,他卻揮劍斬斷她的生路!
448.5萬字8.38 388648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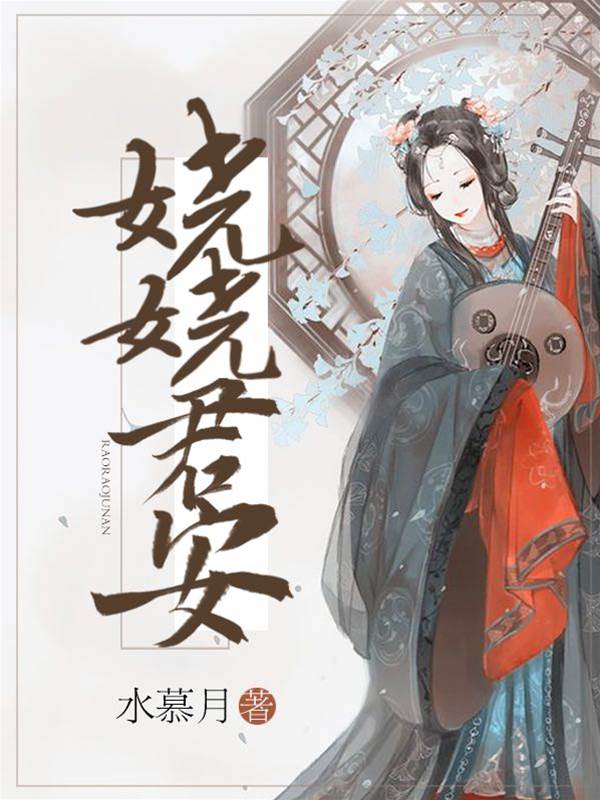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648 章
重生后,我成了渣男他皇嬸
因道士一句“鳳凰棲梧”的預言,韓攸寧成了不該活著的人。外祖闔府被屠,父兄慘死。太子厭棄她卻將她宥于東宮后院,她眼瞎了,心死了,最終被堂妹三尺白綾了結了性命。再睜開眼,重回韶華之時。那麼前世的賬,要好好算一算了。可慢慢的,事情愈發和前世不同。爭搶鳳凰的除了幾位皇子,七皇叔也加入了進來。傳說中七皇叔澹泊寡欲,超然物外,
116.3萬字8.18 58167 -
完結242 章

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傳統古言 廢殺帝王權極一時假太監 寄人籬下小可憐 倆人八百個心眼子】少年將軍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軟軟的小兔妹妹,引人垂涎。將軍一朝戰死沙場,輕躁薄行的權貴們掀了兔子窩,不等嚐一口,半路被內廠總督謝龕劫了人。謝龕其人,陰鬱嗜殺,誰在他跟前都要沐浴一番他看狗一樣的眼神。小兔落入他的口,這輩子算是完……完……嗯?等等,這兔子怎麽越養越圓潤了?反倒是權貴們的小團體漸漸死的死,瘋的瘋,當初圍獵小兔的鬣狗,如今成了被捕獵的對象。祁桑伏枕而臥,摸了摸尚未顯孕的小腹。為了給兄長複仇,她忍辱負重,被謝龕這狗太監占盡了便宜,如今事得圓滿,是時候給他甩掉了。跑路一半,被謝龕騎馬不緊不慢地追上,如鬼如魅如毒蛇,纏著、絞著。“跑。”他說:“本督看著你跑,日落之前跑不過這座山頭,本督打斷你的腿!”
42.7萬字8.18 15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