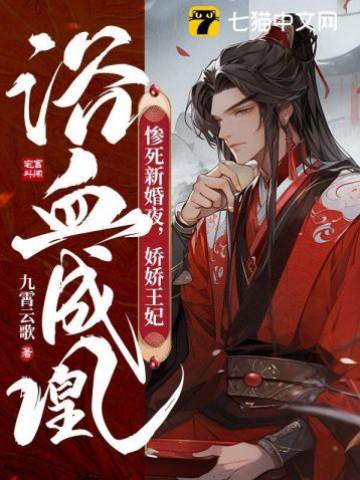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重生之鋼鐵大亨》 第937章 年夜(2)
沈淮走到門口,停下來轉頭看了慵散坐在沙發上的孫亞琳一眼,見一斜,一蜷起,長髮披散下來,出半張豔到極致的臉蛋,迷離的眼眸張出風萬種,他看了心裡一陣陣的發:孫亞琳這一年來很在國,他心裡終究還是念想著的,但越是如此,越是不敢在此輕留,只能搖頭輕嘆而去。
看沈淮落荒而逃又有些舍不去的樣子,孫亞琳不住要笑出聲來,笑罵道:“瞧你多大點出息!”站起來上樓,進房間見胡玫站在窗前,猶看著沈淮在夜下裹離去。
見孫亞琳這麼快就上樓來,胡玫問道:“沈淮怎麼就走了,他不找宋總、姚總他們說話嗎?”
“這個沒良心的,現在連膽子都沒了……”孫亞琳坐到窗臺前,看著沈淮給枝葉遮掩的影,轉回頭來跟胡玫說道。
“怎麼膽子都沒有了?”胡玫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疑的問道。
“我跟他說,他要是敢留到十二點過後再走,我們倆人就陪他——他就這樣給嚇走了。”孫亞琳撇撇說道。
“啊,”胡玫瞠目結舌,沒想到孫亞琳會跟沈淮說這種話,但想到沈淮落荒而逃的樣子,又忍唆不,嗔怪道,“你怎麼什麼都敢胡往外說啊——沈淮以前的子很蛋的,你就不怕他把你的玩笑話當真呀?”
“他要是當真,你陪不陪他?”孫亞琳眼眸子盯著胡玫的臉。
胡玫的臉瞬時染紅,嗔的瞪了孫亞琳一眼,然而這一眼卻是嫵飛豔,將心猶豫掙扎都風纖致的張顯出來;孫亞琳看了心裡想,要是沈淮在場看到,多半骨頭又要幾分,連路都走不了。
Advertisement
孫亞琳見沈淮的影消失在拐角那頭,便將窗簾拉上,不再往窗外的夜看去,舒服的坐在沙發上,不住慨道:“這小子如今個腥都心驚膽,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真不是他以前的風格啊,也好沒趣啊……”
看孫亞琳坐在那裡胡說八道,胡玫忍唆不,笑道:“以前他看到件好東西,他恨不得都糟踏了,你就喜歡了?”
“可他現在一副承擔不起責任的樣子,也實在不討人喜歡啊,”孫亞琳瞅著胡玫的臉蛋,笑道,“我不是說我,我是在說你。”
“怎麼又扯到我上來了,我有什麼喜歡不喜歡的,關我什麼事呀?”胡玫撇清道。
“不是你,那是誰喝多酒半夜抱著我發卻喊那渾蛋的名字?”孫亞琳瞇起眼睛看著胡玫窘得發紅的臉蛋。
“不跟你在這裡胡說八道了,我回房間睡覺了……”胡玫見孫亞琳又提起四天前發生的糗事,的臉蛋染得通紅,都不好意思再留下來說話,扭著子就要離開。
“陪我說說話吧,我今夜真不想孤零零的一個人過,”孫亞琳拉住胡玫,說道,“我們躺到牀上來說話……”
“好吧,不過不能再在牀上喝酒了;除了要頭痛兩天外,你還藉機趁人家便宜。”胡玫說道。
胡玫長期以來都是孫亞琳的私人助理,算不上衆信投資的正式員工,所以兩人不是老闆跟員工,平時的關係已經很是親近。
四天前接到沈淮的電話,得知他跟怡當天已經領證,孫亞琳心裡也有說不出的不痛快,是拉胡玫到酒吧裡陪著喝酒。
喝到興致起,兩個人又帶著酒回房間喝。
胡玫回房間就沒有節制,喝醉將當沈淮,將這些年埋在心裡的都渲泄出來,孫亞琳才知道胡玫沈淮的“傷害”是如此之深,們兩人的關係也就因此更進一步,變得越發的親。
Advertisement
胡玫也知道孫亞琳以前喜歡人的事實,也知道與楊麗麗的“親”關係,但在看來,孫亞琳喜歡人或許已經是以前的事了,此時的孫亞琳與楊麗麗之間,更像是兩個寂寞人找不到寄託之前的互相藉,而如今不過又多了一個而已。
孫亞琳見胡玫只穿著的鑽進被窩裡來,胡玫的高不顯,但材的比例極好,高高的聳起,裡面的罩摘掉,的卻無關點下墜,外緣撐出完的弧形,至腰下漸收一束,至又優的張開來,襯出滿翹的|,雙比例顯長,收直一線,整個人顯得盈纖巧、亭勻合度,渾著迷人人味——孫亞琳在的腰肢上了一下,說道:“那渾蛋要是看到你這樣子,肯定就不會走了……”
胡玫給孫亞琳得腰,笑著扭開腰,說道:“你就這麼想他留下來啊,那你給他看呀——你這麼有料,不給他看,他怎麼會知道?”笑著手過來,在孫亞琳的上掐了一把。
胡玫這一掐算是捅了馬蜂窩,孫亞琳要將逮過來、一定要回本,胡玫笑著閃躲,但人還沒有閃開,就給孫亞琳撲在牀上,兩個人打鬧滾一團。
胡玫終究是力氣小,最終無力的橫枕在孫亞琳的小腹上,累得直氣,呆呆的看著天花板,跟孫亞琳說道:“我們倆長得都還可以吧,不算差吧,怎麼就像是沒人要的老似的,連新年夜都只能相互藉呀?”
“你是真想了?”孫亞琳問道,“要不哪天我們趁著怡不在,試試勾引那渾蛋?”
“胡說八道什麼?”胡玫笑著擡手打了孫亞琳一下。
Advertisement
孫亞琳撐起子,看胡玫紅撲撲的臉蛋;胡玫拿手蓋住臉蛋,孫亞琳的話彷彿一劑最猛烈的春藥,心裡春涌,心裡要是沈淮這時候死皮賴臉的爬上牀來,自己真是沒有半點掙扎的力氣……
沈淮卻是不敢想賓館房間裡的香豔,從小巷子裡穿過,回到怡家,文也剛從外面忙碌回來。
怡見沈淮沒走多久就返回來,問道:“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
沈淮將手機攤開怡看,說道:“半道上就接了好幾通電話,還不知道接下來會有幾通電話打進來,想著還是明天再找鴻軍跟姚行長他們說話好了——走到賓館裡又走回來了。”
劉雪梅說道:“每年的除夕、春節,應該改天接電話日、上門日……”
“沒電話接,沒人上門,你又得嫌冷清了。”文笑呵呵的說道。
文話音未落,沙發角幾上的電話就應景的響了起來,劉雪梅嗔怪著跟丈夫說道:“你去接。”
文也曉得今晚沒空跟沈淮說話,說道:“你們也早點睡吧,咱爺倆有什麼話,明天再說……”
沈淮回到房間,將幾個拜年電話打完,又跟杜建通過電話,有什麼急事他打怡的手機聯繫自己,就直接將手機關了機,跟怡說道:“這下子清靜了……”
“不怕給別人說不近人?”怡問道。
“我打電話給人家拜年,也是帶著忐忑的心;要是電話打不通,心裡也就踏實下來。別人打電話給我拜年,多半也是這種心態,手機關掉,方便自己,踏實別人,”沈淮笑道,“再說了,春宵一刻值千金,也不住這些電話浪費啊……”
見沈淮死皮賴臉的纏過來,怡嚇得直躲——前幾天在沈淮的住所,大門一關,兩人自然胡天黑地的大搞特搞,但今天在自己家裡,姥爺、姥姥睡的客人房就在他們隔壁,要有點靜兩個老人家聽見,還不得死人?
Advertisement
再者,怡有時候也癡,也不知道怎的,每回牀上都要做溼一片——這要媽看見,還有臉再跟沈淮一起回家來?
除了這個,怡還要考慮用過的避孕套怎麼收拾,總不能明正大的丟垃圾桶裡去;扔水馬桶,萬一水馬桶堵上呢?
想到這些事,怡就打定主意,在石門這幾天不沈淮自己。
只是沈淮心火都給孫亞琳勾得快燒起來,這時候怎麼可能輕易放過怡?
怡心志再堅定,只是洗漱過穿著保守的睡上牀,跟沈淮兩人摟在被窩裡一起睡覺,卻哪裡經得住沈淮糾纏?
沈淮先是將整個人都抱在懷裡,然後再手進裳裡抓住那對大白兔百玩不厭的,得怡渾發,得怡只能背過去不理會沈淮。
只是沈淮在後,死皮賴臉的將的子強下來,又那堅如杵的什不要臉的往前湊,到的兩之間,說是讓夾著就好——怡那的極,大緻,夾如握,覺也十分的好,但沈淮不會滿足如此。
而怡那大如丸的杵頭抵在桃花源頭,還不時躡手躡腳還往裡杵頂兩下,也是心慌意迷,也不知道何時下面就溼了一片;起初是不經意沈淮將那粒大的杵頭進來,經多日依舊還有的脹裂,當即的心魂都差點要給顛出來。
見沈淮在後面起來不是很方便,怡只能暗暗的偏著子,沈淮方便能進得更裡面些,很快就會慾的洶涌狂涌淹沒,剩下的最後理智,也不是拿自己的睡墊在下,避免弄溼被單,又強抑住嗓子眼的不出來,微欠著子,好自己能更方便承……
這樣的姿態,沈淮不方便作,但怡的子往後微微欠起,|的部抵在他的小腹上,與他輕撞廝磨,則帶給他多重的極致。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90 章

慶余年2
當范閑腹部中了一劍后,不是死亡,而是重生。不止一次的被人算計,當做棋子,是范閑一步步地蛻變。待他重返之日,便是那些人付出代價之時,當他想與那些人真正對決時,權術謀略,小菜一碟。困獸之爭,究竟誰才是最后的贏家?!
128.5萬字8.25 578423 -
完結1490 章
重生九零之神醫商女
前世为了挣钱争气,忽略自己忽略父母的大龄剩女苏简,在一次碰瓷被人乌龙打死以后,重回到了1997年十五岁的时候,此时亲人朋友安康。再次来过的人生,苏简杜绝遗憾,靠着灵活的经商头脑,异能之手,过目不忘之能,成为神医,成为商业女王,势要带着父母朋友过上幸福安康谁也不敢欺负的生活。
278.7萬字8.18 87606 -
完結1019 章

重生成偏執大佬的心上人
關於重生成偏執大佬的心上人: 【甜爽寵文】“死,也別想擺脫我。” 他的聲音駭人悚然,湛藍的眼眸中卻帶著濃稠的深情偏執。 重活一世,薑瑟決心擺脫前世的命運。於是,她主動成為了‘怪物的妻子’。 世人傳聞聶家長孫陰狠、暴戾,殺人如麻,死在他手中的人不計其數。 傳聞他偏執成性,凡是看上的就一定會千方百計的握在手中。 但薑瑟不怕他,他見過他最恐怖駭人的一麵,是在她的墓前。 那個男人在她的墓前,眼裏有她讀不懂的情愫:“我們注定是要糾纏在一起的。” 重生後,聶家主辦的晚宴上,冷戾矜貴的男人在他的妻子麵前自然的彎下身子,輕柔的為她揉著略微紅腫的腳後跟,語氣縱容無奈“又嬌氣又愛美。” “......” 眾人:是檸檬蒙蔽了她們的雙眼。 【1v1超甜寵文!】
144.9萬字8 115196 -
完結6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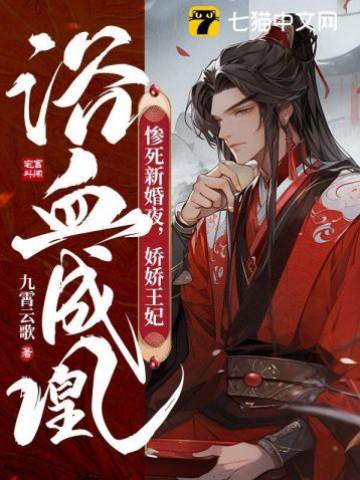
慘死新婚夜,嬌嬌王妃浴血成凰
葉沉魚身為被抱錯的相府假千金,被自己最在乎的“親人”合謀欺騙利用成為毒殺攝政王的兇手,含冤而亡。一朝重生,她回到了真千金前來認親的那一日。 葉沉魚決定做回自己,她洗脫自己的污名,褪下一身華服,跟著鄉野出身的父母離開了相府。 本以為等待她的會是艱苦難熬的生活。 誰料,她的父母兄長個個都是隱藏的大佬,就連前世被她害死,未來權傾天下的那位攝政王,都成了她的……小舅舅。 葉沉魚一臉的郁悶:“說好的苦日子呢?” 蕭臨淵:“苦了誰,也不能苦了本王的心尖尖。”
109.2萬字8.18 14418 -
完結78 章

重生回到退婚前
沈雲商在夫家殫心竭慮,最後落得重病纏身,悽悽慘慘,臨死前,她不由想起,她曾有位未婚夫,雖狗嘴裏吐不出象牙,說句話能給你嗆死,但俊朗闊綽,若是當初跟他服個軟…… 裴行昭在妻家拼死拼活,最後將性命搭進去,臨死前,他不由想起,他曾經有位未婚妻,雖是個狗脾氣,跟炮仗似的一點就炸,但美貌善良,若是當初跟她服個軟…… 一朝醒來,二人回到鬧崩後,退婚前。 沈雲商偷偷瞥向身旁年輕俊朗的少年,恰好對上那雙久違的勾魂奪魄的桃花眼。 視線一觸即分,兩道聲音同時響起:“婚不退了。” 沈家長輩:...昨日不還說天下男人死光了都不嫁裴行昭? 裴家長輩:...昨日不還說寧打一輩子光棍都不娶沈雲商? 沈雲商詫異的用胳膊肘碰了碰少年,彆彆扭扭:“你什麼意...” 裴行昭:“我錯了!” 沈雲商:“嗯?” 裴行昭眼神閃爍:“我們,再試試唄?” 沈雲商愣了愣後,抿着笑高傲的擡着下巴:“試試就試試唄。” 後來,真相揭露。 沈雲商磕着瓜子紅着眼抱臂諷刺:嘖嘖嘖,跑去給人當牛做馬,卻被算計死在了詔獄,真出息! 裴行昭端着盞茶靠在柱上聲音沙啞:貴爲世家大族少夫人,卻連一碗藥湯都喝不到,真有本事! 二人雙雙擡頭望天。 半斤八兩,兩人誰也刺不到誰。 既然這樣,那就一致對外,刺仇人吧。
30.2萬字8.18 4081 -
完結224 章

八零小辣媳:我被最強糙漢抱住了!
穿到了一個破鞋的身上,蘇瑩覺得自己真是大冤種。她可是根正苗紅的好青年。 病美人怎麼了?她也要維護和平民主法治社會! “蘇家那對不正經的姨兩個最近干啥?”八卦村民好奇問。 村長眼含淚光:“她們救人種樹,扶老奶奶過馬路,現在已經去市里面領取好市民獎了……” 蘇瑩在康莊大道上狂奔,結果被人一把抱住。 “媳婦,三胎多寶了解一下?”
40萬字8 1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