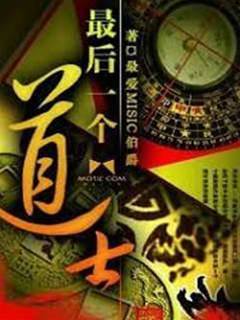《我當陰陽先生的那幾年》 第151章 北上列車(下)
正所謂冤家路窄,馬瘦長,銼漢子還看不上醜姑娘。晚上八點半,我蹲在火車的吸菸區,覺到我自己好像已經要崩潰了。他大爺的。
吐出了一口煙,站起了,將菸頭狠狠的在吸菸區的菸灰缸上掐滅,著窗外一片漆黑,連個都看不見,車廂的腳下咣噹咣噹的,由於不是學生放假或者什麼法定節日,相對於以往,現在火車的客流不是很多,但是車廂裡依舊沒有空位。
其實我喜歡坐火車的,因爲可以和很多陌生的人相遇,有時候我會幻想他們是正在踏上歸途,還是剛剛開始一個人的旅程,就像是人生,我苦笑了一下,沒想到我有時候還能哲學的,儘管和我的外表一點兒都不像。
漆黑一片,看不到車窗外,只能在車窗上看到自己的倒影,以前的那個濃眉大眼兒的年現在早已青蔥不再,相反的,眉宇之間竟然多了一風塵,一市儈,還有一無奈,這麼多年了,也不知道爲什麼,一個人的時候有時候竟然會忽生傷,可能每個人都是這樣子的吧。
我小的時候聽說,社會是個大熔爐,熔鍊千萬種鋼鐵,爲國家做貢獻,可是我長大了的時候才發現,像我這種破銅爛鐵,不是被煉了渣,就是被煉了破鋸鈍刀,
我剛步社會的時候覺得社會並不是熔爐,而是一條濤洶涌的大河,人是河水,浪打浪,男人是河裡的石頭,漸漸的被這社會磨平了棱角,使我們變的圓起來。
到了現在在社會磨練了幾年後,我才發現,社會其實不能說是一條狗屁大河,相反的,我覺得社會是一個人,一個強犯,我們都被社會給了。
Advertisement
但是現在可不是想這些事的時候,我胡思想什麼呢?我苦笑了一下,什麼時候我變的這麼憤青了?
讓我現在覺到頭疼的不是被社會強暴,而是文叔和林叔兩個老傢伙的事,想想剛纔我就哭笑不得,當兩個老傢伙發現竟然是面對面的坐著,他們的表都跟吃了沒翅膀的蒼蠅一樣的難看,於是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想換座位,誰知道那車廂中竟然沒人願意和我們換,這兩個老傢伙沒有辦法了,只能互相仇視著坐在椅子上,一聲不吭。
我和老易只能像是兩個鵪鶉一樣的坐著,一聲都不敢吭,也不敢對視,因爲我倆明顯的覺到了這周圍的火yao味兒實在是太足了,生怕一不小心就當了炮引子導火索。
還好,火車剛開的半個小時裡平安無事,兩個老傢伙只是互相的瞪著,一不,就像是兩個著屁的思想者。僵持了半個小時,我和老易漸漸地放下了心來,他大爺的,看來這兩個老神還是有些廉恥的嘛,他倆也應該知道這大庭廣衆的公共場合吵架是很丟人的事。
於是我和老易便漸漸的放下了心,而這時候文叔開口了,說是要嗑瓜子兒,我便從包裡拿出了一袋兒瓜子兒,和一個塑料袋兒撲在桌子上,讓他往這裡面扔瓜子皮,見文叔和我說話的語氣平和的,我就放下心了,看來文叔這次還真出息了,於是我也拿出了一瓶兒可樂。剛纔沉默了那麼久,終於能放心了,可是我剛喝了一口時,卻發生了一件讓我大跌眼鏡的事。
只見文叔十分悠閒的抓起了一把瓜子兒,然後用牙磕開,接著又十分優雅的把瓜子皮吐到了林叔的臉上,彷彿是把林叔當了人垃圾桶一般。
Advertisement
這不找事兒呢麼!!嚇得我一口可樂沒有嚥下去,直接噴到了坐在我對面的老易臉上,老易眼睛好像被迷了,只見他哎呀哎呀的著。
要知道本來氣氛就張,而林叔也不啥善男信,本來剛纔因爲出租車的事他就憋了一肚子火,這下子好了,這兩個老東西馬上就站起了玩兒起了自由搏擊,我和老易連忙上前拉架,這兩個糟老頭子,怎麼跟小孩兒似的呢?
邊的那些旅客見到有人打架,並沒有人上來幫著勸架,而是都把我們四個當了猴兒看,還有些好事兒的,從大老遠跑過來看熱鬧,他大爺的,這就是人。
這倆老神竟然怎麼拉都拉不開,一邊打,裡還不消停,你一句老X我一句雜碎的罵著,不出所料,果真把乘警招來了。把我們四個一起帶到了車長辦公室好一頓思想教育。我和老易心裡這個冤枉,關我倆啥事兒啊。
還好,這世上還是有公道的,由於沒我和老易什麼事兒,我倆就先出來了,老易由於一臉的百事可樂,雖然幹了,但是很黏,於是他跑到吸菸區旁邊的洗手間洗臉去了,而我則蹲在了吸菸區起了上火煙兒。
不一會兒,老易出來了,他走到我前管我要了菸點著了,他好像也上火的,問我:“你說爲啥臥鋪都賣了呢?這不過年不過節的,真愁人,還有這倆活爹,這一晚上可怎麼熬啊?”
我苦笑了一下,沒有回答他,的確,現在要是有選擇的話,我寧願跟個惡鬼幹一架也比這夾在兩個老神中間夾板兒氣強。
不一會兒,兩個老傢伙灰頭土臉的出來了,看樣子是沒挨訓,都這麼大歲數了,還這麼好鬥,真是的。
Advertisement
只見他倆一聲不吭的往回走,我和老易慌忙跟在了後面,回到座位上,氣氛又變得尷尬了起來。
不一會兒,只見文叔和我說:“給我拿點兒紙,我肚子疼。”
我便拿了包面巾紙遞給了他,他起往衛生間走去,沒走兩步卻又折了回來,他趴在我耳朵邊小聲的對我說:“這老X要是趁我不在的時候跟你說什麼,回來記得告訴我。”
我苦笑的對這文叔點了點頭,他好像著急,便一路小跑奔衛生間去了,我心想,告訴你的話,我這不是找事兒呢麼?
果然,文叔出恭的時候,林叔這老傢伙真的有所行,只見他笑了下,然後跟我說:“上次在醫院見過你,你是崔作非是吧?”
我點了點頭,林叔又和我說:“你跟易欣星認識?”
我了老易一眼,我敢說認識麼?那樣的話,他就別想有好果子吃了,於是我搖了搖頭說道:“不。”
誰想林叔竟然笑容滿面的說:“哎呀,沒關係,認識就認識,別把我和你師父想一種人,其實我是很開通的,你們都是年輕人,既然不的話,那現在就悉一下吧。”
我也不知道這老東西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但是我也不好卷他面子,畢竟都這麼大歲數了,於是我只好對著老易出了手,和他說:“我崔作非,你好。”
老易的呆病好像又發作了,他也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於是他不敢看我,生怕出什麼破綻,只好低著頭想個小媳婦兒似的和我握了握手,裡說道:“幸會,幸會。”
林叔見我倆握完手後,便對我壞笑著,笑的這個難看,就好像是那種看到了的人一樣,弄的我起了一的皮疙瘩,只見他對我說:“小崔啊,想不想聽聽你師父以前的榮歷史啊?”
Advertisement
我明白了,他大爺的,這林叔是想趁文叔不在而背後放毒啊,在我和老易面前損文叔,讓我這個小學徒都替自己的師父到丟人。
我笑了,那老神的事跟我有什麼關係,要知道我可是正宗的白派弟子,看到你們這些藍道神就跟看笑話似的,我心想著這林叔的如意算盤算是打錯了,但是反正現在閒著也是閒著,就當相聲聽了吧。
於是我點了點頭,林叔見我倆好像都想聽似的,於是便開口和我說道:“從哪兒說起呢?要知道那個老騙子之前可出過不笑話,對了,既然這次去是爲甄家遷祖墳,就說說他三十多歲時的一個遷祖墳的笑話吧。”
於是林叔就跟我講了一個據說是文叔以前發生過的一個糗事兒,林叔說,文叔很早開始就幹這行兒了,由於天生一張好,所以特別吃的開,以前有名的先生一般除了道號外,都有個響亮的外號,這文叔的外號便是‘文明白’。說的是不管婚喪嫁娶或者什麼事,找到他,都能辦的明明白白。那時候他還沒在哈爾濱,而是在吉林,有一個土大款請文叔幫忙遷祖墳,說是辦妥當了給八千。
要知道八千塊錢可真不了,快二十年前,二三級城市一共才幾個萬元戶啊,於是文叔很爽快的就答應了,可是他想不到的是,那土大款以前家裡很窮,他的爺爺是埋在葬崗旁邊兒的,現在纔想起來,自己富了,不能再讓自己的爺爺苦了。
於是便找到了文叔,文叔聽這土大款說完,心裡竊喜,心裡想著這可真是算得上白撿的錢,要知道遷墳只要遷到個差不多的地方就行,畢竟這現實世界中哪兒來的那麼多風水寶地啊?
於是他便選了個良辰吉日,讓他土大款準備了必備的品,又找了十多個大小夥子,開了兩輛貨車前往了那片荒地。
一到地方,文叔便傻眼了,這可真是葬崗子,都是小土包,就連那個土大款都不記得自己的爺爺到底是睡在哪座墳裡了。文叔愣了,他終於明白了,這錢不是那麼容易掙的,但是好在死人是不會說話的,這片地裡埋的死人應該都只剩下一副骨頭了,隨便找一個差不多就能糊弄過去。
於是文叔又裝仙風道骨的模樣,要了那老頭兒的生辰八字後,沉思了一會兒,又裝模作樣的從地上抓起了一把土聞了聞,然後便對著那土大款和十多號人點了點頭,儼然一副有竹的模樣。
文叔說:“老夫剛纔已經向地下的亡者們詢問了老爺子的宅,跟我來吧。”
那土大款早就聽說過這‘文明白’的外號,沒想到今日一見果然這麼邪乎,居然只聞了聞土就知道了,可是他想不到的是,文叔其實只是個演員而已。
於是十多號人在文叔的帶領下,來到了一個小墳包前,文叔對著後的那些人說:“這便是老爺子的宅所在了,等我做完法事後,大家便土吧。”
於是文叔便花了半個小時忙活做戲,等他弄完了,便招呼著大家開始挖吧,衆人聽文叔這麼說,便圓了板鍬鋤頭開始挖土,果不其然不一會兒,一口漆黑的棺材便出了頭角。
文叔心想這可真是老天保佑,要是這下面什麼都沒有可就壞了,還好有棺材,因爲有棺材就好說了。
但是文叔想不到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竟然是他做夢都想不到的。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310 章

千年龍棺
天才少年蘇柏因緣際會成為神秘古董店店主,又與茅山少年嶽青結識,一個是天生龍鱗,一個是手有金印,兩人因為各自的命運相互扶持,下古墓,尋找同樣擁有金印的古屍,曆經生死,揭開千年前一段陳年往事,卻也掀開少年蘇柏的體質之謎,昏血癥少女的神秘出現,帶出十二條龍脈與蘇柏的不解之緣,究竟是福是禍?
63.3萬字8.18 19766 -
完結5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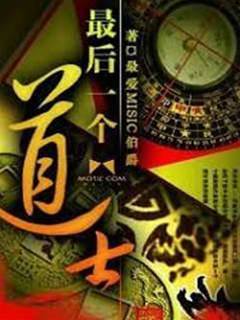
最後一個道士
查文斌——中國茅山派最後一位茅山祖印持有者,他是中國最神秘的民間道士。他救人於陰陽之間,卻引火燒身;他帶你瞭解道術中最不為人知的秘密,揭開陰間生死簿密碼;他的經曆傳奇而真實,幾十年來從未被關注的熱度。 九年前,在浙江西洪村的一位嬰兒的滿月之宴上,一個道士放下預言:“此娃雖是美人胚子,卻命中多劫數。” 眾人將道士趕出大門,不以為意。 九年後,女娃滴水不進,生命危殆,眾人纔想起九年前的道士……離奇故事正式揭曉。 凡人究竟能否改變上天註定的命運,失落的村莊究竟暗藏了多麼恐怖的故事?上百年未曾找到的答案,一切都將在《最後一個道士》揭曉!!!
129.6萬字8 1454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