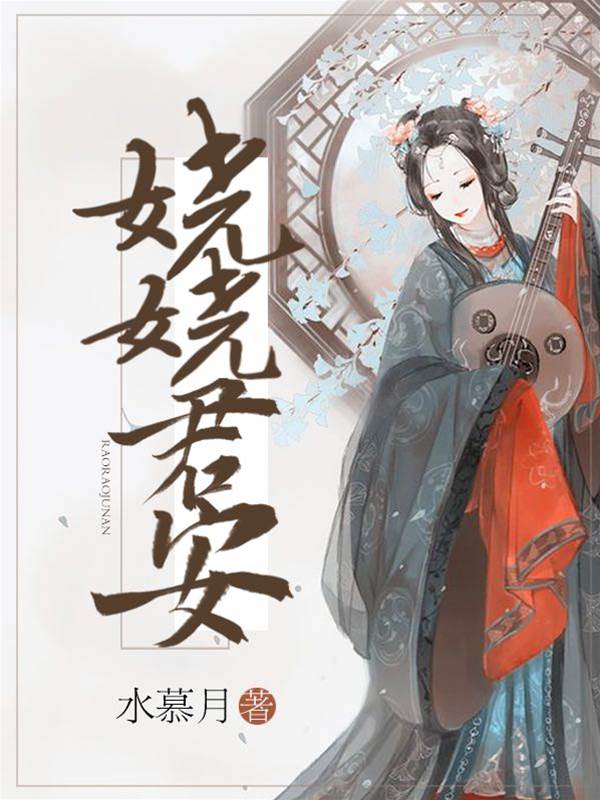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春雪欲燃》 第89章 第89章 退位 “謝謝你,阿姊。……
第89章 第89章 退位 “謝謝你,阿姊。……
侍從們都安靜地退下了。
整座園子十分空曠, 唯有楓葉簌簌飄零,和著潺潺的流水聲、夜風四周紫錦步障的挲聲,溫地彙向這方無人的小天地。
月傾瀉, 照亮了狼藉的杯盤, 亦照亮了那盞傾倒于案幾上的、鮮豔滴的鹿酒。
酒泛著紅寶石般亮的澤,正順著桌沿蔓延淌下, 髒污了下方曲肘仰躺的青年那潔淨的白, 又一點點滲嚴合的襟深。
一聲裂帛的脆響, 名貴的料陡然被撕開,出一片泛著酒意微紅的、薄而結實的膛, 在月下泛著玉般瑩潤的澤。
沈筠慌忙擡手, 按住試圖欺更進一步的某人, 眉頭微皺:“不行, 這不合統。”
“不行嗎?”
蕭青璃輕輕啜飲他口沾染的酒水, 指尖自他清豔無塵的臉龐劃過,沿著滾的結往下, 一寸寸碾過理繃之, 揚眉輕笑,“你的小此君,可不是這樣說的。”
形倏地繃, 玉般的面容染上昳麗的霞, 不知是,還是惱。
今夜月的確人,眼前之人有著比紅葉更為明豔張揚的眉眼。
自上而下地審視, 既帶著上位者睥睨天下的英氣,亦帶著人間俏皮的戲謔,笑看他一個人兵荒馬。
目, 躲閃,糾纏,掙紮……然後漸漸燒出炙熱的火。
沈筠的結幾番滾,終是猛地擡首,幾乎不管不顧地撞上那片含笑的紅,如將死之人拼命汲取水分。
理智斷線,一敗塗地。
猩紅的酒還在流淌,一滴,兩滴。
清噴湧而出,被收束于年的舌間。
蕭燃自下方擡頭,如同一只喝飽飲足的蒼狼,舌尖舐去上薄紅的水,瞇睞著眼,盯了他下一步要攻伐的獵。
Advertisement
飲了鹿酒的人,如同沾了生食的,難免會野一點,難纏一點。
“把手給我。”
他攥住那截纖細的腕子,往前帶了帶,聲音低啞蠱,“不給本王一點獎賞嗎?好歹一下嘛。”
沈荔手腕一,燙著般蜷起了指尖,下意識道:“不行,拿不……”
“撒謊。”
聽磕磕絆絆地說完,蕭燃輕笑一聲,撒般嘟噥:“你這手握竹簡時,不是握得穩的嗎?怎麽就拿不住了?”
沈荔平複呼吸,抿移開視線:“太累了,酸得很。”
一說“累”,蕭燃就拿沒法子。
沈荔只覺自己像一只剛吐過水的蚌,哪怕是輕若羽的,也能讓立刻戰栗地蜷起子。偏生有人掰開了尚未合攏的蚌殼,一邊念叨著“沈令嘉你是不是腎氣虛”,一邊毫不留地撞了上來。
炙熱的風,又沉又急,吹得紗幔搖搖墜。
床邊矮櫃哐當哐當地響著,堆疊的典籍震落在地,仰面攤開,出了其中夾著的草葉書簽。
蕭燃一眼便認出來了,那是半年前他從賑災之地的荒山腳下帶回來的“薜荔”芳草。
後來沈荔告訴他,那并非薜荔,而是形似薜荔的烏韭。
鬧了個大烏龍。
“你還留著它呢?”
他氣息沉沉地笑,鼻尖汗水懸落,砸在緋紅的臉上,“是誰上不說,心裏卻喜歡得很哪。”
“我沒有……”
“沒有?沒有你抓著我不放?”
他惡劣地重重碾,隨即倒吸了一口氣,笑得氣十足,“你看,抓得這樣。真厲害啊,沈令嘉。”
沸騰,燒得人臉皮燥痛,幾近崩潰。
意識在某一瞬徹底斷線,再睜眼時,蕭燃那片汗的膛仍在眼前激,烙著幾點小巧的紅印,在霜白的上格外醒目。
Advertisement
很是豔麗的,沒有破皮,不是方才抓咬出來的。
“這是……傷疤嗎?”
努力睜開被汗水打的眼睫,指尖輕輕過那幾點牙印般的紅痕,“是何時留下的?從前似乎沒有。”
蕭燃低頭看了眼,眼神變得別有深意起來。
“你在我上畫荔枝時留下的,忘記了?”
“……”
好像是有這麽回事……
那時不住,咬了他一口,染料混著汗水淌進傷口裏,便留下了這抹痕跡。
“疼麽?”有些愧疚地問。
“貓撓一下,不痛不。反正平日也看不見。”
說著,他輕輕住沈荔的下頜,迫使轉過紅的臉來,“不許躲!看著,這可是本王的戰功。”
于是沈荔便眼睜睜看著那點牙印在眼前越發豔麗,混著淋漓的汗水,綻放出灼然而妖冶的澤。
恍惚間,想:規矩果然是用來打破的。
什麽一旬一次、不談真心,什麽沐浴更、焚香掃榻……那些曾經鄭重其事的約定,都在本能的歡喜面前不堪一擊。
那些條條框框的束縛,已紛紛揚揚,散做遙遠的過去。唯有此刻的自由與放縱如此真切,正一點點,一寸寸,將厚繭中那個的迷茫的、痛苦的、逃避的自己擊垮、碾碎,再于炙熱中重塑新。
燈花裂,發出嗶剝一聲細響。
沈荔腦中也起一聲清越的回音,仿若靈乍現。
連氣都沒勻,便下意識推開蕭燃,披下榻飛速尋找紙墨,試圖將那稍縱即逝的念頭留于紙上。
蕭燃被推得仰躺于榻上,汗水順著理淌壑,隨手抓起被褥的一角蓋住小腹,支起一道:“好好的,這又是作甚?”
沈荔落筆如飛,連潤墨不足的筆尖開了叉也恍若不覺,只擡指挽了挽松散淩的鬢發,凝神息道:“想起件事,需問一問父親。”
Advertisement
當沈府的仆從揣著這封家書,奔向百裏之外的青山觀時,最後一恬靜的秋意也被驟然卷起的北風吹散,冬日的冷刃悄然出鞘,向世人亮出了凜冽的鋒芒。
十月底,一樁誰也不曾料到的意外發生。
冷宮的廢後,早産了。
……
廢後生了個男嬰。
那孩子雖提前了五十日出生,哭聲細弱如貓,卻是一位實實在在的小皇子。
朝中原本倒向攝政長公主的風向,似乎又有了微弱的變化。
“小皇子生于冷宮,其母又罪孽滔天,依律本無為皇儲的資格。”
長公主府中,幕僚爭相諫言,“然他終究是陛下的骨,若有一日得勢翻,恐禍患。還請殿下早做決斷!”
立即有人厲聲反對:“閣下此言,莫非要讓殿下對一個襁褓中的兒下手?”
“皇室多一子,便多一變數。待其長,後患無窮矣!”
先前那人堅持道:“近日天象示警,熒守心,災異頻生,正是天子失德、當禪賢能之兆。如此良機,殿下更應順應天命,早登大寶才是!”
廢後素來食不佳,早産的孩子能活下來,是誰也不曾預料到的。
心腹重臣的諫言猶在耳畔,蕭青璃深知其中厲害:陛下雖癡傻,卻很喜歡這個羸弱的兒子。若他佞之徒的蠱,執意要立此子為太子,則這些年嘔心瀝的謀劃,全了為他人做嫁的笑話。
屆時小皇子的生母楊氏,亦會跟著一同赦免,重新走向外戚幹政、世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荒唐局面。
而今之計,唯有趁朝中謝楊二黨倒臺,尚無勁敵之際,順應民心,做出那個最後的決定。
謀臣們分為兩派——
一派溫和些的,是希能勸帝主遜位,禪讓于攝政長公主。
Advertisement
一派激進些的,認為應該一步到位,免得廢帝將來又會被人利用,為世家卷土重來的棋子。
“阿姊府中快要吵翻天了,你不去看看麽?”
蕭燃剛從宮中回來,上還穿著郡王的朝服,盤坐在靜心撰寫策論的沈荔面前,“一定很需要你。”
“需要的,是自己的決斷。”
沈荔捉袖擡眸,清明道,“我既已選擇了,便信。”
西殿,四下無人。
年天子跪趴在搖籃前,清澈的眸子一眨不眨地凝視著襁褓中那個皺的小嬰兒。
人心真是複雜。
蕭青璃想:明明他的心智也是個孩子,卻已經學會如何疼另一個更弱小的孩子了。
“他們說,北方的冰災是因為朕失德,南方的洪災是因為朕不仁,天狗食日是天神對朕的懲罰……”
年低著頭,蒼白秀氣的臉皺一團,很輕地問,“阿姊,朕真的有這麽壞嗎?是因為朕打碎了湯碗,不肯乖乖上床安寢,所以才惹怒了上天?”
“不是。”
蕭青璃放緩聲音,又重複了一遍,“不是陛下的錯。”
他什麽都沒做過,自然什麽都沒做錯。
“陛下在宮中,開心嗎?”
聽阿姊發問,蕭含章茫然地點點頭,又搖了搖頭。
蕭青璃換了個問法:“若陛下有機會出宮,重新開始,陛下可願意?”
年怔愣許久,遲疑著,小心翼翼地點了下腦袋。
片刻,更用力地點了點頭。
著年蒙著一層水霧,如迷途林鹿般惶的眼睛,蕭青璃定了定神,將一旁的托盤輕輕推至他面前。
盤中放著一卷大虞疆域的輿圖,一只白瓷藥瓶。
將選擇的權利,還給了這位一生都被各方勢力裹挾著的可憐年。
“若陛下選擇輿圖,則可在上面任擇一郡,帶著孩子離開宮廷,做個自在閑散的王公貴胄。”
蕭青璃淺吸一口氣,竭力維持語調的冷靜,“若陛下選擇這瓶息丸,便可拋卻眼下的一切桎梏,與你的孩子換個份,換種人生,徹底重新開始。”
當一個從來都沒有選擇的機會的人,驟然擁有選擇的權利時,接踵而至的并非欣喜,而是惶然。
蕭含章看了看輿圖和藥瓶,又看了看蕭青璃,眼底漸漸蓄起了水,揪著袖道:“重新開始後,朕是不是……就再也見不到阿姊和阿兄了?”
“元照會去看你,吾也會,悄悄的。”
蕭青璃頓了一息,方繼續道:“當然,你還有第三個選擇。”
“第三個……選擇?”
“是。”
蕭青璃微微頷首,“第三個選擇便是,繼續做大虞的天子。”
蕭含章微紅的鼻翼翕合,近乎茫然地問:“朕做天子,或是不做天子……有區別嗎?”
蕭青璃一怔,似是被問住了。
是啊,一個沒有實權的傀儡天子,當或是不當……于天下而言,又有何區別?
孩的思緒總是跳的,問出疑後,也不急于得到答案,反而專心致志地觀其托盤中的什來,時而這個,又時而那個。
猶豫許久,久到日頭下沉,殿中逐漸漫上一層冬日的寒。
蕭含章仿佛終于下定了決心,一鼓作氣地拿起了那只藥瓶。
“這個……”
單薄的年握著那只小小的瓷瓶,訥訥問出了一個天真的,令蕭青璃心碎的問題:“吃了後,會不會很疼?”
這個傻瓜,竟以為這是毒-藥。
“不疼。”
蕭青璃眼眶酸,輕輕了弟的臉,如待他兒時那般耐心地解釋,“它只會讓你睡三日。三日後,便是嶄新的開始。”
蕭含章似懂非懂地點頭。
“不過,此藥僅此一顆,你要想清楚。”
蕭青璃道,“普通人的日子,沒有你想象中的輕松。”
“可朕覺得,阿姊遲早能讓天下的普通人,都過上好日子。”
這個懵懂的年如此說道,“既然如此,朕做個普通人,又有何不好呢?”
蕭青璃眸微,酸漫上鼻腔,又化作明麗的笑意滲進眼底。
“吾還以為,你會選擇做個閑散王侯。”
蕭含章聽了,只是搖頭如撥浪鼓。
“朕看不懂政務,也不會治理百姓呀。”
他眨著漆黑純淨的眼睛,很是認真地說道,“封王封侯,也不過是將我們父子,從王宮關進郡宮而已。還會有許多討厭的人登門絮叨,煩得很……朕又不是小傻子,難道不明白這樣的道理?”
孩子氣的話語,逗得蕭青璃撲哧一笑。
“是,含章最聰明了。”
靜了片刻,又輕聲問,“含章不怨阿姊麽?”
讓一個什麽都不懂的年寫罪己詔,將那些天災人禍攬于己,再禪位讓賢,終究是一種殘忍。
可放任他繼續混沌下去,為各家爭權奪利的籌碼,對于天下人來說,亦是一種殘忍。
“為何要怨?”
蕭含章著實不能理解,甚至不自覺朝前傾了傾子,遲鈍道,“從小到大,只有阿姊會問朕……真正想要什麽啊。”
蕭青璃此番乃是宮,今日談話斷不能讓第二人知曉。
剛起,便聽後傳來一聲細弱的呼喚:“阿姊!”
英姿颯爽的大虞君回首,只見瘦弱的年天子立于斜暉中,習慣地揪著袖邊,朝綻開一抹大而真誠的笑容。
“謝謝你,阿姊。”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229 章
帝凰之神醫棄妃
大婚當天,她在郊外醒來,在衆人的鄙夷下毅然地踏入皇城…她是無父無母任人欺凌的孤女,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血王爺.如此天差地別的兩人,卻陰差陽錯地相遇.一件錦衣,遮她一身污穢,換她一世情深.21世紀天才女軍醫將身心託付,爲鐵血王爺傾盡一切,卻不想生死關頭,他卻揮劍斬斷她的生路!
448.5萬字8.38 388648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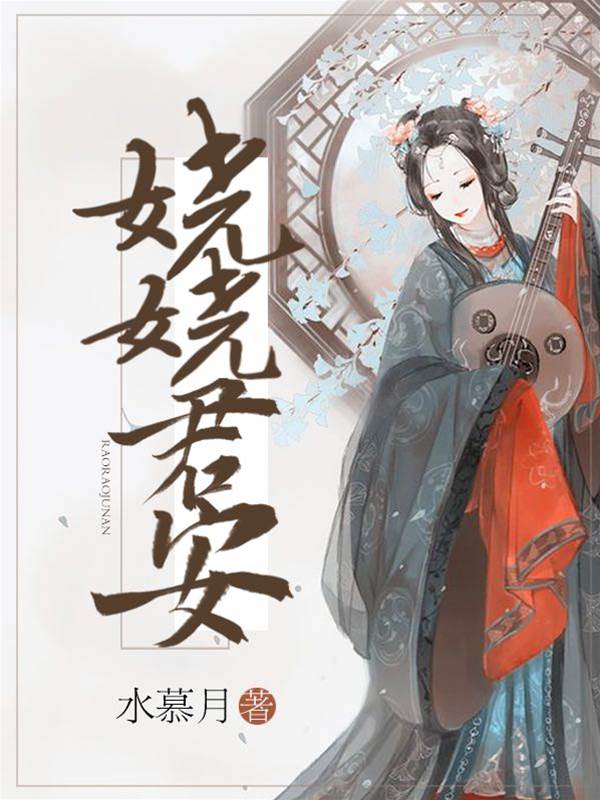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648 章
重生后,我成了渣男他皇嬸
因道士一句“鳳凰棲梧”的預言,韓攸寧成了不該活著的人。外祖闔府被屠,父兄慘死。太子厭棄她卻將她宥于東宮后院,她眼瞎了,心死了,最終被堂妹三尺白綾了結了性命。再睜開眼,重回韶華之時。那麼前世的賬,要好好算一算了。可慢慢的,事情愈發和前世不同。爭搶鳳凰的除了幾位皇子,七皇叔也加入了進來。傳說中七皇叔澹泊寡欲,超然物外,
116.3萬字8.18 58167 -
完結242 章

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傳統古言 廢殺帝王權極一時假太監 寄人籬下小可憐 倆人八百個心眼子】少年將軍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軟軟的小兔妹妹,引人垂涎。將軍一朝戰死沙場,輕躁薄行的權貴們掀了兔子窩,不等嚐一口,半路被內廠總督謝龕劫了人。謝龕其人,陰鬱嗜殺,誰在他跟前都要沐浴一番他看狗一樣的眼神。小兔落入他的口,這輩子算是完……完……嗯?等等,這兔子怎麽越養越圓潤了?反倒是權貴們的小團體漸漸死的死,瘋的瘋,當初圍獵小兔的鬣狗,如今成了被捕獵的對象。祁桑伏枕而臥,摸了摸尚未顯孕的小腹。為了給兄長複仇,她忍辱負重,被謝龕這狗太監占盡了便宜,如今事得圓滿,是時候給他甩掉了。跑路一半,被謝龕騎馬不緊不慢地追上,如鬼如魅如毒蛇,纏著、絞著。“跑。”他說:“本督看著你跑,日落之前跑不過這座山頭,本督打斷你的腿!”
42.7萬字8.18 15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