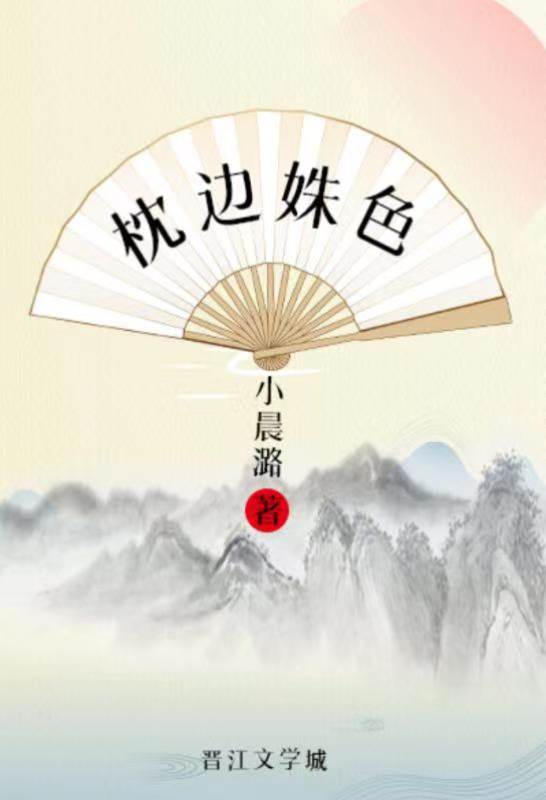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春雪欲燃》 第47章 第47章 重逢 我夢見你怪我…………
“不錯。”
“龍門關的軍報,未必快得過本王的鐵騎,故而他此刻尚不知龍門關失守的消息。在未瞧見本王的大軍主力前,他不會輕舉妄。”
“是這個理。”
“那麽,何不讓他以為,本王的大軍主力正蟄伏于暗,伺機合圍邑呢?”
蕭燃薄扯出一抹沒有溫度的笑來,布滿的眼一片冷冽殺意,“只要故布疑陣,讓烏桓進確認本王主力在此,他自覺目的達,便不會戰。”
荀靖心中有了底,那些騎兵與戰力不足的陳郡兵多半被遣去布疑陣了。
現在他們要做的,便是等待時機。
可北淵兵等不及了,迫不及待要辱大虞將士一二,引他們發兵。
“怎麽有個士人在城牆上?”
荀靖瞇著眼睛看了半晌,狐疑道,“那群儒生投誠了?!”
“絕無可能!”
“不可能。”
蕭燃與商靈異口同聲,神冷靜而篤信。
他記得沈荔據理力爭時的錚錚風骨,有在,那群學宮師生斷不可能折腰事賊!
他信。
周晦被數名北淵兵押上城牆,路過牆頭懸掛的邑太守首級時,他渾一,險些跌倒。
“天命有歸,聖主膺期……”
然不容他遲疑,踉蹌的形已被北淵兵推至城牆邊,面朝城下河畔的數千大虞將士,抖著手展開降表,哆哆嗦嗦地念道,“神武蓋世,德被九州……”
“大聲些!”
北淵兵厲聲大喝,毫不客氣地推了他一把。
周晦駭得雙發,手中的降表抖得嘩啦啦作響,不得不加大聲音,發出一聲嘶啞怪異的破音:“今大淵駐邑,非為不德,乃解蒼生倒懸之苦……”
此言如滴水油鍋,瞬間激起人群中的一陣。
一名“儒生”憤而振袖,高聲質問:“看看這滿地的骸!汝為人言否?!”
Advertisement
“什麽人在吵嚷?”
烏桓進手按刀柄,鷹目如刀刃掃過人群,朝後一隊士卒厲聲喝道,“去,把鬧事的人揪出來!”
執長矛的北淵兵暴地撥開人群,見那幾名鬧事者穿著虞朝的文士袍,到底不敢當街斬殺殺儒,只大聲呵斥著同那幾名扮做儒生的漢子推搡拉扯。
幾乎同一時間,城牆上。
北淵守軍瞳仁微,眼中升起了一陣遙遠的狼煙——
那是南城門的方向,黃沙滾滾,如風暴席卷而來,遮天蔽日的黃霧中似有千軍萬馬奔襲而至!
南北城門相距甚遠,這群北淵兵當然不會想到,這所謂的“千軍萬馬”只是千餘不擅征戰的陳郡兵沿途堆放狼煙,八百騎兵馬尾綁著樹枝來回奔跑,所營造出的兵馬地而來的假象。
北城門下的蕭燃實在是過于鎮定從容,于是連同烏桓進在的所有北淵兵便理所當然地以為,北門下的這伶仃二千餘人不過是障眼法,真正的虞朝主力正于南門外伏擊突襲。
“有敵襲!”
烏桓進反出了一個如釋重負的神,後退一步,嘶聲吼道,“是虞朝的主力!全軍戒備!”
北淵兵立刻來回奔忙,卻并不見多鬥志。
他們只負責將虞朝主力引來邑,任務便算完,實在沒必要同這支銳之師正面鋒,尋個時機突圍撤退才是正理。
當然,突圍前得殺了這剩下的幾萬人質,讓虞朝回援一座空城才痛快!
正當烏桓進如此盤算時,學宮衆人也下定了最後的決心。
這是個極佳的時機,比那幾名喬裝儒生的青年鬧出的靜更大、更。
沈荔與崔妤等人換了一個眼神,略一點頭示意,便見元繁擊掌為號,高高舉起了早準備好的筆。
紅玉筆在下反出醒目的。
Advertisement
後那群“儒生”見狀,便高呼道:“就是現在!兄弟們,奪城門——”
近二十餘人趁著敵軍混之際一擁而上,有的人去擡門閂,有的人沖上門房,有的人以攔住守衛,還有幾個人見北淵人兇殘勢衆而臨陣逃,但多數人仍是按照計劃一步步接近他們要搶奪的陣地……
劉家姊妹形瘦小,能靈巧地避開守衛刺來的長槍,從他們的腋下鑽出逃,故而最先登上吊橋絞盤所在的門房。
已有兩名一同攻占門房的青年倒在泊中,但們不能停下!
沖開門房鎖鑰,一行人同裏頭守衛的數名北淵兵扭打在一起。
“六合之,莫不稽首……”
牆垛旁的周晦仍在巍巍念著降表,負重傷的劉家姊妹已越過重圍,搶到了絞盤。
“旌旗蔽空,鐵騎如雲,始知螻蟻不可撼樹……”
劉家姊妹對視一眼,咬牙拼盡全力,共同轉左右兩只絞盤。
被鮮染的手掌極為黏膩,幾乎難以使勁……就在此時,一雙雙染的手相繼覆上絞盤,齊聲呼喝著,帶著們共同用力!
“今共沐大淵雨,若執迷不悟,則伏百萬,流千裏……”
絞盤發出一聲初始啓時的響,繼而鐵鏈嘩啦啦碎響,如流水般一瀉千裏!
吊橋如巨的緩緩開啓,即將搭上彼岸的一瞬,一隊北淵兵破門而,出彎刀狠狠紮劉家阿姊的,將連人帶絞盤釘在了一起。
周遭響起一片同袍倒下的悶響,那片可惡的刀鋒卡絞盤的齒機括中,發出一聲尖利的哀鳴後,徹底停止了轉。
吊橋離岸不過丈許,便停在了半空中。
時間仿若靜止。
“惟願垂日月之明,施雨之恩,止戈興仁……”
Advertisement
周晦的聲音越來越低,越來越弱,而後終于停了下來。
他怔怔著城下攢的人影。
那一張張年輕的、和他兒子年紀相仿的面孔,此刻正浸在泊中,倒在沉重的門閂之下。
恍惚間,一切似乎變得扭曲而怪陸離,喧嘩如水般灌他的耳中,夾雜著上司的叱罵,人的鄙笑,最終定格在兒子那雙憤恨的眼睛上。
“你那些卑躬屈膝、為人奴婢換來的錢,我嫌髒!”
枯槁的胡須微微,周晦沉默著將降表折好,收袖中。
“怎麽不念了?”
一旁的北淵兵本長脖子朝人群中張,見他止聲,便回頭怒視。
周晦了,囁嚅道:“想說之言已在心中,不用照念了。”
他轉向城下引頸戮的惶然百姓,徐徐吐出一口濁氣。
有那麽一瞬,他覺得牆頭的寒風似乎不再刺骨,這殘朽的軀殼中,正有溫熱的東西在複蘇湧。
“同袍們,莫做待宰羔羊!”
周晦突然向前趴在城垛上,扯著脖子嘶聲大喊,“奪城門!去奪城門啊——”
這聲嘶吼沖破雲霄,如巨浪蓋過城下喧嘩,連正與北淵兵對峙的沈荔與崔妤都愕然擡首。們從未想過,那幹瘦的膛裏竟然能發出如此驚天地的高呼!
一名北淵兵惱怒,竟忘了國主“不傷儒士”的命令,拔刀猛沖了上去!
繼而一點寒芒自周晦的口出,那枯瘦的形猛烈晃了晃,緩緩朝後傾倒。
最後映他眼簾的,是一片廣袤而自由的澄淨碧空。
人群中靜默了一瞬,隨之發出更為嘈雜響亮的聲音。
“北淵人殺儒了!北淵人殺儒了!”
“連文士都能殺,何況我等黔首!”
“奪城門,拼一線生機!”
霎時間,憤怒的人群儒浪一疊推著一疊向前,用短、用掃帚、用拳頭,沖向那群手持染彎刀的北淵兵!
Advertisement
就差一點……
就差一點啊!
劉家阿姊邊溢出沫,飄逸潔淨的文士袍已被暗紅浸。艱難側首,最後看了一眼絞盤旁氣絕的妹妹,緩緩擡起抖的指尖,徒勞地握住再也無法轉的絞盤。
最後一力氣耗盡,的手緩緩垂落,黯淡的眼眸半睜,卻再也映不進半點天。
正在此時,絞盤上的鐵索驟然一!
城門外,紅玄甲的年武將手持長槍,策馬若猛虎躍起,穩穩落在懸在半空的吊橋上。
繼而槍尖橫掃一片寒芒,吊橋鐵索應聲斬斷。
橋轟然砸落,激起塵土飛揚,穩穩架在護城河兩岸。
“殺——”
無數將士怒吼著沖上吊橋,隨著他們的將軍湧往城門。
城門,門閂下已經積了一座小小的山。
濃重的腥氣刺得沈荔間發,眼前一陣接著一陣的眩暈。
大口息,將崔妤與張晏推去一旁的安全地帶,這才提而起,穿過紛的人群爬上那堆溫熱的、間或搐的山,用盡全力氣頂起門閂。
雙手的力量不夠,便用肩頂,用扛!
冷汗浸衫,無暇顧及腳下踩的是什麽,濺上臉頰的溫熱黏膩又是什麽,只燃燒命般朝上頂去!
一雙手了過來,同一同使勁,是額上破了道口的元繁。
繼而越來越多的手了過來,有的糙,有的纖細,有的指腹帶著日夜紡織的老繭……是後那萬衆的百姓突破北淵兵的屠刀湧了上來,喊著號子,嘶吼著,用盡全力朝上頂去。
沉重的門閂砸落在地,大門徐徐打開,一線明亮的晨伴隨著那襲如火的紅傾灑進衆人眼中。
槍尖所至之,摧枯拉朽,一片橫飛。
北淵兵被那一騎沖破防線,以決堤之勢飛速潰敗。
百姓歡呼著讓開一條道來,沈荔也隨之退步,極度力的軀搖晃兩下,跌坐道旁。
一桿黑漆銀刃的霸王槍破空而來,帶著淩厲的風響,將後那名潛行的北淵士兵紮了個對穿。
鮮噴濺,的眼睫也隨之一,滿目都是年策馬飛奔而來的影。
僅是視線的短暫接,蕭燃已越過拔下上的長槍,迎向正在集結潰兵的北淵主將。
烏桓進已聽到了後近的馬蹄聲,以及那熾烈而洶湧的殺意!
他知道自己無法在這樣冷酷強悍的殺意中逃,索調轉馬頭,握手中的彎刀,拍馬俯沖上去!
他在北淵也算是得上名號的驍勇之將,曾于萬軍之中創下一人連挑九名烏池勇士的不敗戰績。
然而此刻,他的卻像是一片破布般輕飄飄起,從馬背上飛了起來。
兩匹戰馬錯的瞬間,蕭燃手中的長槍已貫穿烏桓進的膛,將他高高挑飛在槍尖上。
哐當一聲,嵌著寶石和人骨的沉重彎刀落地。
這個高壯的北淵將領不可置信地瞪大雙眼,濃稠的鮮淅淅瀝瀝地自口鼻溢出,淌出一條黏膩的瀑,如同檐下的“風鈴”,如同道旁倒掛的首,如同每一位被他屠殺的邑百姓,毫無還手之力地結束了他那可悲的命。
蕭燃將敵將的摔落道旁,如同甩掉一袋破爛的渣滓。
繼而手中長槍橫掃,斬斷了那面侵占邑六日之久的敵軍戰旗,繼續朝那拼命逃跑的北淵兵追去。
沈荔最後看見的,便是那道所向披靡的影——蕭燃如無人之境,殺出的道竟無人敢上前填補。
知道,現在不是相認敘舊的時機。
在確認并無命之憂後,蕭燃須得斬殺敵將,砍倒敵旗,而後領著大虞將士乘勝追擊,橫掃戰場。然後……
然後如何?
已無力思考,這半日的鮮與殺戮不住沖擊著的神智,腔急劇起伏,耳畔盡嗬嗬的呼吸聲……
“郎!”
“王妃!”
失去意識的一瞬,兩道悉的影下馬奔來,穩穩接住倒的形。
……
再次醒來時,已是日暮黃昏。
周圍很安靜,靜謐得仿佛一場遙遠而陌生的夢境。
沈荔晃神片刻,擡起酸痛的手臂,緩緩推開上的錦被。
剛試著撐坐起,榻邊立刻傳來了茶盞打翻的聲響。
商風袖袍沾,手臂上還纏著繃帶,幾乎連滾帶爬地跪挪過來,驚喜道:“公子醒了!”
沈荔張了張,幹的嗓子卻發不出半點聲音。
“公子舊疾複發,萬不能激。”
商風在後背墊了兩只枕,小心地扶躺下。
沈荔輕輕握住他的袖子,指了指他的手臂,又朝門外看了一眼,蒼白的面上浮現些許焦急。
“今晨公子走後,我與學宮衆人便按照公子的吩咐加固門窗,搬來重抵住各大門。一個時辰後,外邊果然傳來,有北淵兵意圖沖進學宮,趁屠戮百姓。”
商風解釋道,“所幸防備得當,他們未能得逞。雖有數十人了輕傷,但并無命之憂。我等幸不辱命,守住了學宮!”
見沈荔眨了眨眼,商風心領神會,複又補充道:“丹郡王馳援及時,城中幸存的數萬百姓,也都保住了。”
沈荔這才稍稍放下心來,目掃過葦席上那件疊放齊整的破舊灰狐裘,微微一凝。
正怔神間,廊下傳來了靜。
商風起出門瞧了一眼,詫異道:“殿下?公子剛醒,正在室養……”
話還未說完,一道渾染矯健的影已越過他闖進房中。
吧嗒一聲,解下的戰甲墜地。
剛起的沈荔什麽都沒來得及看清,就被擁一個朗寬闊的懷抱,沉重的力道撞得後退一步,就著相擁的姿勢跌坐在地。
“我夢見你怪我……”
蕭燃抱著,微的呼吸掃過的耳畔,間發出破敗不堪的風響,“怪我來得太晚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85 章

登堂入室
元執第一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在和她的乳兄謀奪家業; 元執第二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在和她的乳兄栽贓陷害別人; 元執第三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那個乳兄終於不在她身邊了,可她卻在朝他的好兄弟拋媚眼…… 士可忍,他不能忍。元執決定……以身飼虎,收了宋積雲這妖女!
72.5萬字8.18 8869 -
完結1000 章

逆天神醫妃:鬼王,纏上癮
“王爺,不好了,王妃把整個皇宮的寶貝都給偷了。”“哦!肯定不夠,再塞一些放皇宮寶庫讓九兒偷!”“王爺,第一藥門的靈藥全部都被王妃拔光了。”“王妃缺靈藥,那還不趕緊醫聖宗的靈藥也送過去!”“王爺,那個,王妃偷了一副美男圖!”“偷美男圖做什麼?本王親自畫九十九副自畫像給九兒送去……”“王爺,不隻是這樣,那美男圖的美男從畫中走出來了,是活過來……王妃正在房間裡跟他談人生……”墨一隻感覺一陣風吹過,他們家王爺已經消失了,容淵狠狠地把人給抱住:“要看美男直接告訴本王就是,來,本王一件衣服都不穿的讓九兒看個夠。”“唔……容妖孽……你放開我……”“九兒不滿意?既然光是看還不夠的話,那麼我們生個小九兒吧!”
176.8萬字8.18 149187 -
完結972 章

一胎三寶:神醫娘親腹黑爹
四年前,被渣男賤女聯手陷害,忠義伯府滿門被戮,她狼狽脫身,逃亡路上卻發現自己身懷三胎。四年後,天才醫女高調歸來,攪動京都風起雲湧!一手醫術出神入化,復仇謀權兩不誤。誰想到,三個小糰子卻悄悄相認:「娘親……爹爹乖的很,你就給他一個機會嘛!」讓天下都聞風喪膽的高冷王爺跟著點頭:「娘子,開門吶。」
175萬字8 25431 -
完結1546 章

醫女天下:冷麵王爺欠調教
被嫡姐設計,錯上神秘男子床榻,聲名狼藉。五年後,她浴血歸來,不談情愛,隻為複仇,卻被權傾天下的冷麵攝政王盯上。“王爺,妾身不是第一次了,身子早就不幹淨了,連孩子都有了,您現在退婚還來得及。”垂眸假寐的男子,豁然睜開雙目,精光迸射:“娶一送一,爺賺了。”
268.2萬字8 25872 -
完結3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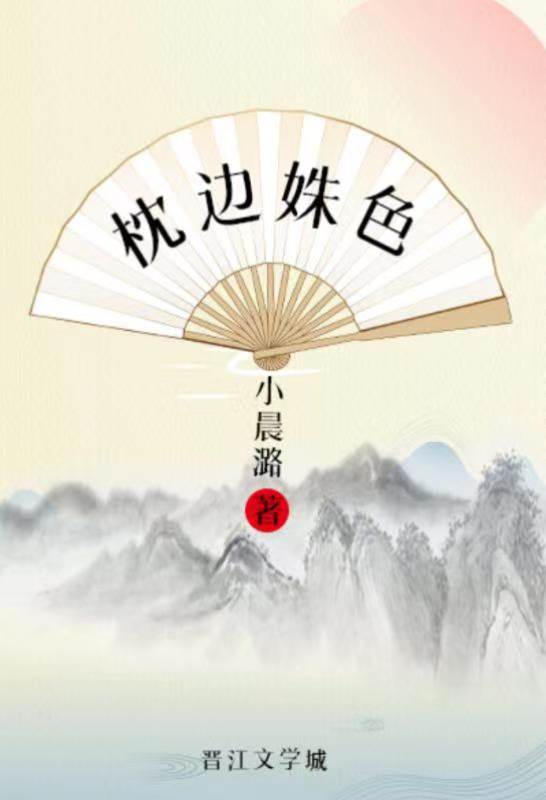
枕邊姝色(重生)
阮清川是蘇姝前世的夫君,疼她寵她,彌留之際還在爲她以後的生活做打算。 而蘇姝在他死後,終於明白這世間的艱辛困苦,體會到了他的真心。 得機遇重生歸來,卻正是她和阮清川相看的一年。她那時還看不上阮清川,嫌棄他悶,嫌棄他體弱多病……曾多次拒絕嫁給他。 再次相見。蘇姝看一眼阮清川,眼圈便紅了。 阮清川不動聲色地握緊垂在身側的右手,“我知你看不上我,亦不會強求……”一早就明白的事實,卻不死心。 蘇姝卻淚盈於睫:“是我要強求你。” 她只要一想到這一世會與阮清川擦肩而過,便什麼都顧不得了,伸手去拉他的衣袖,慌不擇言:“你願意娶我嗎?”又哽咽着保證:“我會學着乖巧懂事,不給你添麻煩……我新學了沏茶,新學了做糕點,以後會每日給你沏茶喝、給你做糕點吃。” 她急切的很,眸子澄澈又真誠。 阮清川的心突然就軟成一團,嗓音有些啞:“願意娶你的。” 娶你回來就是要捧在手心的,乖巧懂事不必,沏茶做糕點更是不必。
58.5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