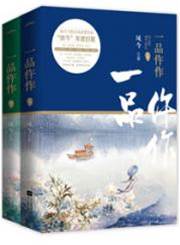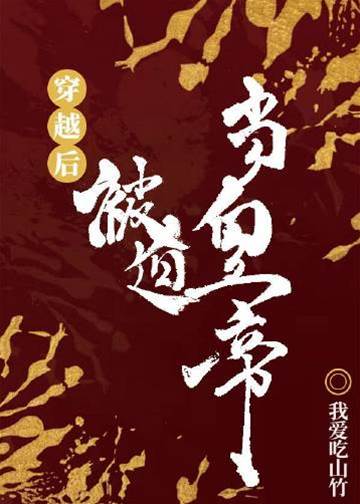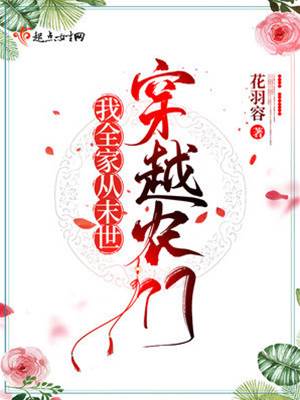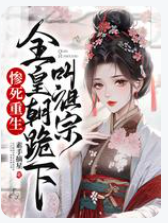《媚妾為后》 第183頁
而且自己才剛和父兄團聚,是不可能舍得就此分別,從此不見的。
阿嫵這麼前后思量一番,竟也有些糾結,發現自己很貪心,既想要那青袍白巾的俊郎君,又想要父兄,最好是不要缺了榮華富貴,當然了還必須順過昔日那口氣來。
想到最后,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腦門:“哎呀,太貪心了!”
**************
接下來幾日,寧家幾兄弟時不時想從阿嫵這里試探口風,比如皇帝年紀不小相貌尚可,比如往日皇帝待你如何,比如太子多大年紀如何如何,當然也會試探著問起阿嫵在宮中生下的一對兒。
阿嫵自從回到家鄉后,過去的事都忘了七七八八,就像做了一場夢一樣,甚至連一雙兒都忘差不多了,如今景熙帝出現,又被阿兄這麼詢問,難免也記起來一些,竟添了幾分別樣思。
反倒是寧蔭槐,對此不悅,斥責幾個兒子:“你們日日絮絮叨叨,聞著阿嫵問來問去,何統?”
說著,命令阿嫵:“不許搭理他們。”
寧家幾兄弟一聽,頓時做鳥散。
葉寒此時也住在鎮子上,知道皇帝追來了,并不曾多言語。
他心里自然明白,皇帝不會善罷甘休,他親自部署安排,要自己帶著阿嫵回來故鄉,必是有后手的,如今他要太子監國理事,自己駕親征前來東海,顯然是為了阿嫵。
其實事到如今,他也開始想,對于阿嫵來說,怎麼樣才是最幸福的,以及皇帝做到哪一步,寧家父子以及自己才能徹底放心,將阿嫵到他手中。
就在眾人各懷心思的忐忑中,這一日景熙帝特意投了拜帖。
拜帖中言語恭敬,禮數講究,對寧蔭槐稱先生,自己卻以名自稱,拜帖中以名自稱,這是謙遜之舉,對于他這樣的份,已經把姿態放得很低了。
Advertisement
拜帖中提到,他邊有一楷書字帖,為趙子昂所書《神賦》,只是不知真假,想登門請寧蔭槐品鑒。
寧蔭槐看著這拜帖,沉半晌不能言語。
阿嫵對于自己阿爹有些了解的,一看便明白,心想這老男人可真有心機。
他當然也知道,但凡他有所舉措,難免落下以權相的嫌疑,反而惹得自家不快,所以他便弄來了什麼名帖,關鍵還不是直接送給你,是不知真假,所以需要你品鑒。
品鑒是什麼意思,就是大家一起看看,探討探討,請你幫忙鑒別下。
這樣的說辭可以說是給足了自己阿爹面子,人家看中你才華呢,請你欣賞鑒別呢。
對于一個讀書多年的儒商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個更為的了,顯然阿爹已經心。
阿嫵道:“那就請他上門唄!”
這一說,寧家父子四人全都看過來,那眼神……別提有多復雜了。
阿嫵:“他若來了,我可不見!我出門去玩!”
寧三郎贊同:“三哥帶你出去玩,讓他們在家招待這個人!”
他對景熙帝的稱呼是“這個人”,“那個人”。
寧蔭槐略沉了下,也就應了。
畢竟這個人已經來了這偏僻小鎮,他所為何來大家都清楚,一味躲避也沒用,對方禮數如此周全,他們也不可能失禮。
于是寧蔭槐便寫回帖,寫回帖時,怎麼稱呼自然要細細思量,對于景熙帝的份,大家看破不說破,但該敬重還是要敬重。
阿嫵:“那就寫他的字吧,他的字是執安。”
這一說,寧家父子四人的視線再次匯聚到上。
阿嫵:“就是執安啊……”
寧蔭槐其實是知道的,讀書十幾年,怎麼可能不知道當今天子的表字,只是聽兒這麼大咧咧地說出來,還是有些不適應。
Advertisement
那是天子啊,讀書人都要避諱的……
他輕咳了聲:“那就以表字稱呼吧。”
寧三郎嘀咕:“這是什麼表字,不好聽!”
寧蔭槐道:“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阿嫵道:“對,這句話出自道德經,意思是執守大道之德,天下人因此歸附的意思。”
這一解讀,父子四人又同時看向。
阿嫵愣了下:“……我說錯了嗎?”
寧三郎心緒復雜:“阿嫵如今倒是很有些學問了。”
阿嫵想起往日,被老皇帝著讀書,抱在懷中手把手地教,還要這樣那樣的……
臉紅,喃喃地道:“人家宮中有規矩,進宮后都要讀書的,我可是當過皇貴妃的,我當然會讀!”
寧大郎想起之前阿嫵的言語,也終于明白了:“你會算學,也是在宮中學的了?”
阿嫵:“嗯,他非要我學!”
他……
父子幾人自然明白,這個“他”就是天子。
寧蔭槐不著痕跡地問道:“和海外諸國通商一事,自然也是皇帝說給你的?”
面對父親的詢問,阿嫵有些心虛,眼神飄忽:“……是,反正隨口說說,他當時說要去海外尋你們的,于是順便提起。”
寧蔭槐便沉默了,此時這時候回想起來,他們上岸后不曾為難的府,也包括那些早早知會他們、要他們候著的州府,這自然是皇帝的安排。
皇帝知道他們歸來,知道他們發財了,才要葉寒把阿嫵送回來和他們骨團聚的。
這個男人手握至權,自始至終不曾想過放手,如今更是萬里迢迢而來,微服私訪,謙遜地放低姿態,在自己面前執晚輩之禮。
而此時的寧家兄弟,回想著這事,一時也都不吭聲。
Advertisement
他們覺,他們的妹妹仿佛沒變,但又實實在在地變了,曾經站在大暉權利巔峰之側俯瞰,眼界,見識,想法,都和以前不太一樣了。
良久,寧蔭槐道:“先回帖吧。”
***********
寧蔭槐回帖后,景熙帝便登門造訪了,這天一大早,阿嫵早早出去,跟著寧三郎去附近捉魚玩蝦去了。
景熙帝登門時是帶了禮的,并不是什麼特別貴重的,只是尋常果子,聊表心意而已,對于這一點,寧蔭槐明白,皇帝的分寸拿得很好。
寧家自然早就灑掃廳堂,周到款待。
上次寧三郎打了景熙帝,好在如今看著早已沒任何痕跡,彼此都沒提這件事。
至于那字帖,果然為趙子昂所寫,應是祭奠亡妻的,筆勢收放自如,絞轉運腕一搨直下,大有魏晉之風,寧蔭槐看得贊嘆不已:“堪稱小楷之最了!”
這麼一番品鑒后,彼此自然都添了幾分欣賞,兩個人的話題便慢慢提提到了東海水師以及賊寇之患,也提到了海外遠航以及通商之策。
剛開始寧蔭槐還有些放不開,略顯拘謹,后來在景熙帝的循循善下,他也開始講起自己的抱負,自己年時的策論,以及這幾年游歷海外的所思所想。
兩個人深談一番,有些想法竟不謀而合。
景熙帝提起如今自己的航海船只制造,鎮安侯府雄霸東海多年,他們在艦船和遠航上都很有些積累,不過鎮安侯府陸允鑒叛逃后,這些資料中一部分最要的卻不見了。
對此,寧蔭槐也有一番想法:“鎮安侯府多年積累的航海輿圖以及一些航海志,這自然是大有助益,不過他們的船只,恕在下直言,若在東海,自然能稱霸于一時,但若是遠洋航行,卻大有不足。”
Advertisement
景熙帝聽此,誠懇地道:“懇請先生指點一二。”
寧蔭槐不敢托大,先是一拜,之后才侃侃談及。
原來他在外航海多年,也仔細觀察過,發現那些番邦船只自然是勝于大暉航船,但是若大暉照搬了來做,在東海海域,卻不盡如人意。
至于大暉東海的船,若是行至遠洋,也并不便利。
景熙帝:“這是為何?”
寧蔭槐:“在下觀察數年,認為這和風有關。”
景熙帝:“風?”
寧蔭槐:“遠洋航海船只,必須適應不同地域的洋流,風向,風速。”
景熙帝蹙眉,之后了然:“我中華海域東海一帶的洋流海風和番邦之國迥然不同,若將國外船只圖紙照搬,必然有所欠缺。”
寧蔭槐:“是。”
當下便詳細提及,船只制造中的耐用,穩定,以及適應不同水域和氣候等。
他在外航海多年,這些都是如數家珍,景熙帝這些年關注遠洋通航和船只制造,自然也略通一些,兩個人一番深談,倒是對景熙帝啟發極大。
談至深,寧蔭槐對這位自己青年時便崇敬過的天子越發敬佩,而景熙帝則嘆道:“昔年海寇一案,牽連甚廣,如今看來,倒是平白埋沒了多棟梁之才,這是朝廷之失,帝王之過。”
這番話說得寧蔭槐倒是有些慚愧。
在他弱冠之年時,也曾意氣風發,但十幾年苦讀竟折戟沉沙,誰曾想有一日,恍惚間已經是不之年,卻因為自己兒的緣故,得見天子,高談闊論。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https://.52shuku.net/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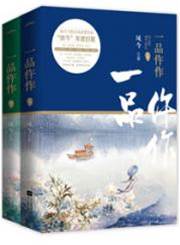
一品仵作
這是一個法醫學家兼微表情心理學家,在為父報仇、尋找真兇的道路上,最後找到了真愛的故事。聽起來有點簡單,但其實有點曲折。好吧,還是看正經簡介吧開棺驗屍、查內情、慰亡靈、讓死人開口說話——這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乾了。西北從軍、救主帥、殺敵首、翻朝堂、覆盛京、傾權謀——這不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也乾了。但是,她覺得,這些都不是她想乾的。她這輩子最想乾的事,是剖活人。剖一剖世間欺她負她的小人。剖一剖嘴皮子一張就想翻覆公理的貴人大佬。剖一剖禦座之上的千麵帝君,步惜歡。可是,她剖得了死人,剖得了活人,剖得了這鐵血王朝,卻如何剖解此生真情?待山河裂,烽煙起,她一襲烈衣捲入千軍萬馬,“我求一生完整的感情,不欺,不棄。欺我者,我永棄!”風雷動,四海驚,天下傾,屬於她一生的傳奇,此刻,開啟——【懸疑版簡介】大興元隆年間,帝君昏聵,五胡犯邊。暮青南下汴河,尋殺父元兇,選行宮男妃,刺大興帝君!男妃行事成迷,帝君身手奇詭,殺父元兇究竟何人?行軍途中內奸暗藏,大漠地宮機關深詭,議和使節半路身亡,盛京驚現真假勒丹王……是誰以天下為局譜一手亂世的棋,是誰以刀刃為弦奏一首盛世的曲?自邊關至盛京,自民間至朝堂,且看一出撲朔迷離的大戲,且聽一曲女仵作的盛世傳奇。
203萬字8.18 29155 -
完結69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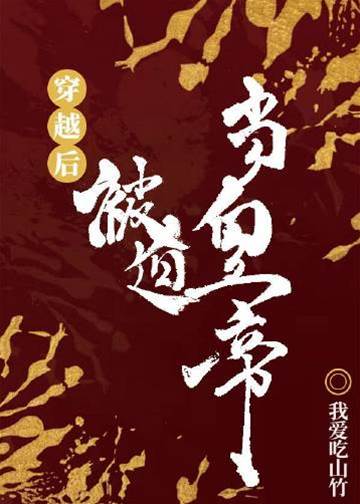
穿越后被迫登基
一朝穿越,葉朔成了大周朝的九皇子。母親是最得寵的貴妃,外祖父是手握重兵的鎮國公,他剛出生就一躍成為了最熱門的皇位爭奪者前三,風頭直逼太子。最關鍵的是,母親同樣有奪嫡之念。寵妃+兵權+正直壯年的皇帝,這配置一看就是要完,更何況,他前面還有八個…
106.4萬字8 8694 -
完結49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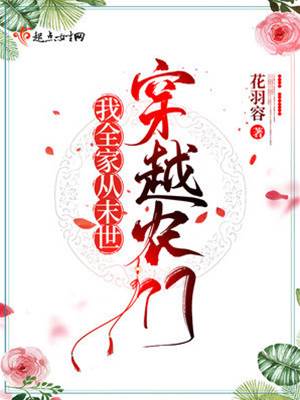
我全家從末世穿越農門
一場爆炸讓一家三口從未來穿越農門,面對全新的環境,可憐的老太太,一家三口慶幸又感激,沒說的全家老小一起奔小康。
90.7萬字8 30702 -
完結5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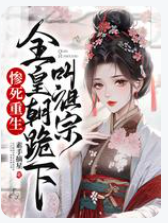
慘死重生,全皇朝跪下叫祖宗
段明曦嫁給高湛后循規蹈矩,三從四德,尊重孝順公婆。高湛扶持新帝登基有了從龍之功,第一件事情便以不敬公婆,沒有子嗣為由休了她,請陛下賜婚將他的心上人迎娶進門。成親
104.2萬字7.92 394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