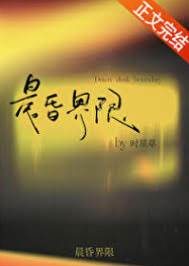《孤山烈焰》 第2卷 第 133 章 西伯利亞雪原·1
“酒店已經安排好了。”他突然開口,聲音低沉,“紀隨的兒房就在我們隔壁。”
“我們?”初穗猛地轉頭,發甩在真皮座椅上發出細微的聲響。
車,顧淮深的目在后視鏡里與初穗相撞。
眼中閃過的慌和抗拒猝不及防撞進眼底,顧淮深指尖在方向盤上微微收。
...
“總統套房有三個臥室。”他聲音忽然平靜下來。
角那抹若有似無的笑意也跟著淡了下去,“紀隨一間,保姆一間,你一間。”
車有一瞬間一直沒有任何聲響。
初穗這才意識到自己反應過度,手指無意識地攥了的角。
再抬頭,駕駛座上的男人早已經移開視線,側臉在雨夜的車燈映照下顯得格外冷峻。
“我...”張了張,卻不知該說什麼。
顧淮深打了轉向燈,車子平穩地駛輔道。
雨刮有節奏地擺,在玻璃上劃出清晰的扇形。
“初穗。”他突然開口,聲音很輕,“用不著這麼防備我。”
這句話像一細針,輕輕扎進初穗心口。
“我不是...”聲音發,“我只是...”
初穗想解釋,但是發現自己無法說出什麼有說服力的言語。
車的暖氣突然變得令人窒息。
“到了。”顧淮深停下車,聲音已經恢復平靜。
他解開安全帶,作利落地下車繞到后門,小心翼翼地把睡的紀隨抱出來,全程沒有再看初穗一眼。
初穗站在原地,看著顧淮深高大的背影在雨中微微前傾,為懷里的紀隨擋住風雨。
車后座有一把剩下的黑傘。
雨聲漸大,初穗撐開那把黑傘挪腳步追上去。
——
林景早已經在大廳等候。
將房卡給顧淮深之后,他便退到一邊。
電梯門在后無聲地閉合。
Advertisement
初穗站在鋪著厚重地毯的走廊上,看著顧淮深抱著紀隨走在前方的背影。
他肩頭的西裝布料被雨水洇出深痕跡,卻依然將紀隨護得嚴嚴實實,連小家伙的一發都沒讓淋。
走廊的壁燈將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初穗踩著他的影子往前走,聽見自己的鞋跟陷進地毯里的悶響。
剛剛在車,顧淮深傷的眼神揮之不去。
想說些什麼,可嚨像是被雨水堵住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顧淮深刷卡開門的作——他的指尖在門卡上停頓了一瞬,指節微微發白。
“顧淮深...”終于開口。
他卻已經推開門,側讓保姆抱著紀隨先進去。
總統套房溫暖的燈流瀉出來,照在他半邊臉上,而另一半臉依然在走廊的影里,看不清表。
“早點休息。”他說完這句話就轉離開,聲音輕得像是在對待一個陌生人。
初穗下意識手,指尖卻只到他西裝袖口冰涼的雨水。
再轉眼,他已經消失在轉角。
“顧淮深——”
的聲音在空的走廊上顯得格外清晰。
電梯門已經打開,顧淮深的背影停了不到一秒,沒有回頭。
初穗顧不上還在滴水的發梢,快步追了上去。
地毯吸走了腳步聲,只有急促的呼吸在腔里回。
但已經來不及了,等初穗趕到,面前的電梯門已經緩緩關上。
隙中,看見男人冷淡得沒有一緒的雙眼。
心底突然好像被人攥起。
...
忽然。
“叮”的一聲,金屬門重新打開。
顧淮深站在電梯角落里,領帶不知何時松開了,漉漉的劉海垂在額前,遮住了眼睛。
“我...”初穗的指尖還沾著雨水,在電梯按鍵上留下漉漉的痕跡,“你別走。”
Advertisement
顧淮深終于抬眼看,眼底泛著初穗從未見過的紅:“為什麼?”
電梯開始自關門,將兩人困在這個狹小的空間里。
初穗看著樓層數字不斷下降,突然意識到自己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他,也不知道找到后要說什麼。
的聲音越來越小,“你上都是的...至把頭發吹干再走。”
顧淮深輕聲笑了下,似乎在笑違心的話。
電梯很快到達一樓。
提示音響起,男人忽然手按下關門鍵,重新按了頂層的按鈕。
電梯門緩緩合攏,將外界的一切聲響隔絕在外。
閉的空間里,只剩下兩人錯的呼吸聲,和滴水落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輕響。
顧淮深突然抬手,修長的手指穿過初穗的發間,水珠順著他的手腕進袖口。
初穗呼吸一滯。
男人溫過的襯衫傳來,燙得指尖發。
電梯開始上升,失重讓不自覺地往前傾,額頭幾乎要上他的鎖骨。
剛要開口,顧淮深另一只手猛地撐住后的鏡面,將徹底困在雙臂之間。
的西裝布料著的手臂,帶著雨水的氣息和灼人的熱度。
顧淮深忽然用拇指按住的下,力道不輕不重,指尖沿著的線游走,最后停在角,“穗穗,你應該明白你追過來代表了什麼。”
電梯“叮”的一聲再次停在頂層,初穗站在原地沒,怔怔看著他前的襯衫下那道約可見的疤痕。
這道疤,是因為留下的。
——
兩年前。
初穗跟著科考隊到了西伯利亞雪原,在那里,遇到了顧淮深。
不是偶遇。
那個時候,西伯利亞的雪下得很大。
初穗跟著科考隊駐扎在極地觀測站,負責記錄冰川活的影像資料。
Advertisement
那邊氣溫常年低于零下三十度,暴風雪來臨時,連呼吸都會結冰。
傍晚的時候,獨自扛著攝像機從冰原回來,睫上結滿了霜,手指凍得幾乎失去知覺。
觀測站的木屋亮著暖黃的燈,推門進去時,熱氣撲面而來,融化了眉梢的雪。
然后,看見了顧淮深。
幾乎一點征兆都沒有,他就這樣猝不及防地出現了。
男人就坐在壁爐旁的木椅上,修長的指間著一杯伏特加,冰藍的火焰在杯壁上靜靜燃燒。
爐火的映在他廓分明的側臉上,將他的影子投在后的原木墻壁上,像一幅沉默的剪影。
初穗僵在門口。
攝像機都差點從肩上落。
火堆前,男人目像灼熱的烙鐵,一寸寸碾過凍紅的臉頰:“抱歉,我控制不住自己不來找你。”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晚安,蘇醫生
作為一名醫術精湛的外科醫生,卻被人用威脅用奇葩方式獻血救人?人救好了,卻被誣陷不遵守醫生職業操守,她名聲盡毀,‘病主’霸道的將她依在懷前:“嫁給我,一切醜聞,灰飛煙滅。”
35.7萬字8 19772 -
完結209 章

日日招惹,矜貴男主被勾纏失控了
【極限撩撥 心機撩人小妖精VS假禁欲真斯文敗類】因為一句未被承認的口頭婚約,南殊被安排代替南晴之以假亂真。南殊去了,勾的男人破了一整晚戒。過後,京圈傳出商家欲與南家聯姻,南家一時風光無限。等到南殊再次與男人見麵時,她一身純白衣裙,宛若純白茉莉不染塵埃。“你好。”她揚起唇角,笑容幹淨純粹,眼底卻勾著撩人的暗光。“你好。”盯著眼前柔軟細膩的指尖,商時嶼伸手回握,端方有禮。內心卻悄然升起一股獨占欲,眸色黑沉且壓抑。-商時嶼作為商家繼承人,左腕間常年帶著一串小葉紫檀,清冷淡漠,薄情寡欲。卻被乖巧幹淨的南殊撩動了心弦,但於情於理他都不該動心。於是他日日靜思己過,壓抑暗不見光的心思,然而一次意外卻叫他發現了以假亂真的真相。她騙了他!本以為是自己心思齷鹺,到頭來卻隻是她的一場算計。男人腕間的小葉紫檀頓時斷裂,滾落在地。-南殊做了商家少夫人後,男人腕間的小葉紫檀被套入了纖細的腳踝。男人單膝跪地,虔誠的吻著她。“商太太,今夜星光不及你,我縱你欲撩。”從此,做你心上月。
31.5萬字8.18 15202 -
完結156 章

掌心獨寵:錯撩權勢滔天的大佬
【雙潔 先婚後愛 頂級豪門大佬 男主病嬌 強取豪奪 甜寵 1V1】人倒黴,喝涼水都塞牙去中東出差,沈摘星不僅被男友綠了,還被困軍閥割據的酋拜,回不了國得知自己回敬渣男的那頂「綠帽」,是在酋拜權勢滔天的頂級富豪池驍“能不能幫我一次?”好歹她對他來說不算陌生人“求我?”看著傲睨自若的池驍一副不好招惹的模樣,沈摘星咬牙示弱:“……求你。”聞言,男人突然欺身過來,低頭唇瓣擦過她發絲來到耳邊,語氣冷嘲:“記得嗎?那天你也沒少求我,結果呢……喂、飽、就、跑。”為求庇護,她嫁給了池驍,酋拜允許男人娶四個老婆,沈摘星是他的第四個太太後來,宴會上,周父恭候貴賓,叮囑兒子:“現在隻有你表叔能救爸的公司,他這次是陪你表嬸回國探親,據說他半個身家轉移到中國,全放在你表嬸的名下,有900億美元。”周宇韜暗自腹誹,這個表叔怕不是個傻子,居然把錢全給了女人看著愈發嬌豔美麗的前女友沈摘星,周宇韜一臉呆滯周父嗬斥:“發什麼呆呢?還不叫人!”再後來,池驍舍棄酋拜的一切,準備入回中國籍好友勸他:“你想清楚,你可能會一無所有。”池驍隻是笑笑:“沒辦法,養的貓太霸道,不幹幹淨淨根本不讓碰。”
28.6萬字8 15484 -
完結578 章

億萬寵婚:神秘老公狠兇猛
他是A市帝王,縱橫商界,冷酷無情,卻唯獨寵她!“女人,我們的契約作廢,你得對我負責。”“吃虧的明明是我!”某宮少奸計得逞,將契約書痛快粉碎,“那我對你負責!讓你徹底坐實了宮夫人的頭銜了!”婚後,宮總更是花式寵妻!帶著她一路虐渣渣,揍渣女,把一路欺負她的人都給狠狠反殺回去。從此人人都知道,A市有個寵妻狂魔叫宮易川!
106.2萬字8.18 544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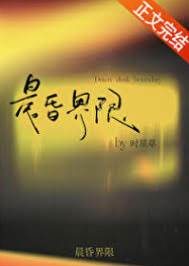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