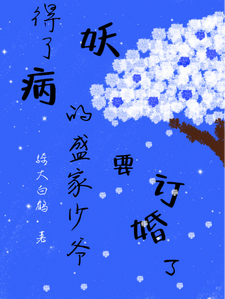《夏夜旖旎》 第185章 親子鑒定
謝天齊臉赤黑,仍舊一副自嘲而篤定的模樣:“用得著麼,不說長相,單說基因問題,我謝家全族百年來都沒出過一個天生近視戴眼鏡的,而你,十歲不到的年紀就戴上了與他一樣的眼鏡!”
指向柳書白的那食指的抖帶了整個手腕,謝天齊幾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緒。
他并非對謝祁延沒有,畢竟那是自己滿懷著期待等待著降生的孩子。
可他控制不住自己,尤其是看到戴上眼鏡之后的謝祁延時,他便控制不住地聯想到柳書白,聯想到自己被背叛了的那份恥辱。
謝祁延眉頭微蹙,沒對自己近視還是不近視做出解釋,只是看謝天齊的目多了幾分慶幸:“我應該到高興,智商這一塊兒,我也隨了我媽。”
扶著門框歪頭打探的夏晚梔一時沒忍住短促地笑了聲。
這一笑,倒是很神奇地化解了此刻沉重的氛圍。
笑是因為看到謝祁延還有心開玩笑。
知道他沒有因為謝天齊那番話影響,心里跟著輕松了許多。
有些尷尬地走進來,夏晚梔剛要手去挽著謝祁延,便見他已經先把手遞過來牽著。
“還麻煩柳叔也給我一頭發。”謝祁延側目看向柳書白,特意強調,“要黑的,好區分,我倒要看看,過兩天我能不能如愿改姓。”
柳書白很樂意,大大方方連薅了幾下來:“好兒子!盡管拿去。”
說完又試探地問了句:“改姓的話……我要不先提前把相關證件準備好?”
話當然是故意說給謝天齊聽的,是看到他又黑又白又難看的那張臉柳書白心里就暢快無比。
快五十歲的人了,說話還這麼沒大沒小,姚琴看了他一眼,言又止,只好無奈嘆了口氣。
Advertisement
思緒得厲害,只覺腦子嗡嗡囂著離開,于是手跟自己兒子要人:“丸子陪我出去走走吧。”
早春晴朗,宜散心。
夏晚梔樂意之至:“好。”
謝家老宅不完全算是傳統的四合院,真要逛起來也不是一會兒就能逛完的,但夏晚梔只帶姚琴去了南院。
那是屬于謝祁延的院子。
逛一圈下來,姚琴格外安靜,見著院中那些打理得井井有條的盆栽出神,夏晚梔提了一句:“阿延說您喜歡文竹。”
夏晚梔從小就來謝家串門,對謝家算得上格外悉,謝家各個院子都有花有樹,但只有謝祁延的南院才會出現文竹。
門前這幾棵,便是謝祁延從小養到大的。
哪怕他十二歲就出了國,南院的一切都被人打理得很好。
謝祁延在謝家不待見是真的,但老爺子私下對他好也是真的。
要不然,不會單獨將南院給了他。
姚琴眼神有些呆滯,聞言笑了笑:“是他太喜歡。”
姚琴是屋及烏,謝祁延也是。
是習慣,是懷念,也是眷形的喜歡。
“醫生說了要趁春日多出去走走,哪天神好一些了,跟阿延一起去個地方吧。”夏晚梔手指拂過那文竹葉子,記起小時候一向冷漠的謝祁延會因為文竹葉子變黃掉眼淚,不由慨,“文竹不好養,但您瞧,這一棵爬滿墻的文竹,郁郁蔥蔥。”
文竹枯萎是真的,后來又被救活了也是真的。
謝祁延十幾歲就被送出國,姚琴是知道的。
所以這棵文竹是經誰吩咐被細心照料著,已經不言而喻。
姚琴沉默著,垂眸掩去自己的緒。
當初揚言死都不允許進謝家大門的那個人,卻是信守承諾的人。
老爺子答應會對謝祁延好。
他沒失言。
Advertisement
而那個曾經想許下山盟海誓一輩子對好的那個人,卻早已忘記初心,傷徹底。
可笑。
可笑至極。
-
親子鑒定結果最快都要等兩天,謝祁延倒是不著急,著急的是謝天齊。
夜半三更,噩夢驚醒,謝天齊忽然害怕。
他不知道在害怕什麼。
明明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他都如此篤定謝祁延非自己親生。
可就是莫名地心悸。
被司法鑒定通知去拿報告當天,謝家出現一位不速之客。
小小年形單影只站在謝家大門前,雙手握,抬頭時眸中含著倔強的淚水,卻遲遲不敢邁進這道門檻。
直到有人發現了他。
“小桉哥哥!”正要去上舞蹈興趣班的謝檀尖細的嗓音響亮徹,充滿震驚的同時幾乎是飛奔到謝桉面前,從小一起長大的分還在,正要開口說些什麼的時候,看清了對方眼里強忍住的淚水。
一瞬間,謝檀下了所有的雀躍。
負責送謝檀去上興趣班的司機早已經將消息傳到了老爺子那邊。
謝祁延掌權之后,這位小爺就不知所蹤,私生子一事被傳得沸沸揚揚的時候,謝桉也從未過一面。
可想而知,侯夢秋將這事兒瞞得很。
到底是自己看著長大的孩子,老爺子猜出其中緣由,親自到門口接的謝桉。
“瘦了。”對視的瞬間,老爺子只說了兩個字。
沒有喊他的名字,也沒有慈藹的笑容,只有深深的無奈。
謝桉被謝家所有人的表刺痛著心,那強忍的淚水終于落下,哽咽著:“爺爺……”
如果不是聽到自己母親和安必華吵架,他至今還被蒙在鼓里。
從小喊到大的爺爺不是爺爺,爸爸不是爸爸……
家人不是家人。
當知道謝家的一切都與他無關的時候,謝桉只覺天塌了下來。
Advertisement
“自己回來的?”老爺子輕嘆一聲,看不來一個才十三歲的孩子哭這樣,上前抹掉他的眼淚,輕輕拍著他肩膀,問他,“都知道了?”
十幾年的不是假的,老爺子雖狠心不再認他,但如今看見謝桉,心終究還是了下來。
謝桉就只是倉惶地點頭,淚水卻越發洶涌。
還沒等說上那麼一兩句話,門外謝天齊的嗓音便無往里:“還回來做什麼?”
一旁站著的謝檀被那樣冷漠無的聲音嚇得了腦袋,低頭在手表兩下,給夏晚梔發了條消息。
謝桉一樣被震懾住,那句卡在嗓子眼里的爸爸二字最終又咽了回去。
“你早知他不是你親生都能容他在謝家十幾年,怎麼,現在反倒對他起氣來了?”老爺子繃著一張臉,相比謝桉這個孩子,讓他到不恥的是謝天齊這個兒子。
謝天齊不答,看向謝桉的眼神既冷漠又無:“我記得你不是最喜歡你那位司機叔叔麼,他就是你爸爸,你應該高興才是。”
謝桉被嚇到放聲大哭。
“他就是個無辜孩子,你對他說這些做什麼!”老爺子震怒,將謝桉護在后。
椅上的謝天齊對昨晚的噩夢心有余悸,大中午的又忽然見到謝桉,那不安在心里瘋長,他盯著謝桉這張臉,閉了閉眼試圖平靜自己的呼吸。
他清楚地明白,自己對侯夢秋出軌,對謝桉非自己親生一事滿不在乎,是因為自己從未。
對侯夢秋無,對謝桉無。
而姚琴與謝祁延。
那是他深深過的人和孩子……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03 章

難產夜,付總陪著白月光,我不干了
付南城的新娘在婚禮當天突然消失,他指着池煙,讓她從伴娘變成新娘。 池煙生下雙胎胞當天,他逃跑的新娘回來,他甩給她一份離婚協議。 後來,池煙成了炙手可熱的離婚律師,身邊追求者無數。 他怒砸重金,插隊來到她面前,她已經在婚禮現場要嫁人了,他拉着她的手,怎麼趕也趕不走。 “池小姐,我要打官司。” 她無奈,問他:“付先生,請問你要打什麼官司?” “復婚官司。” “抱歉,我是離婚律師,付先生,另請高明。”...
123.6萬字8 136702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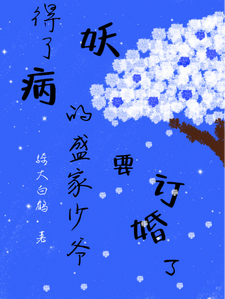
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因為自家公司破產,弟弟生病,阮時音作為所謂未婚妻被送進了盛家。盛家作為老牌家族,底蘊深,財力雄。 而盛祁作為盛家的繼承人,卻極少出現過在大眾眼中,只在私交圈子里偶爾出現。 據傳,是有不治之癥。 有人說他是精神有異,也有人說他是純粹的暴力份子。 而阮時音知道,這些都不對。 未婚妻只是幌子,她真正的作用,是成為盛祁的藥。 剛進盛家第一天,阮時音就被要求抽血。 身邊的傭人也提醒她不要進入“禁地”。 而后,身現詭異綠光的少年頹靡地躺在床上,問她:“怕嗎?” 她回答:“不怕。” 少年卻只是自嘲地笑笑:“遲早會怕的。” “禁地”到底有什麼,阮時音不敢探究,她只想安穩地過自己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不久之后,月圓之夜到來了。 - 【提前排雷】: 女主不是現在流行的叱咤風云大女主,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導致了她性格不會太強勢,但也絕對不是被人隨意拿捏的軟蛋,后面該反擊的會反擊,該勇敢的照樣勇敢。我會基于人物設定的邏輯性去寫,不能接受這些的寶子可以另覓佳作,比心。
2.1萬字8 650 -
完結218 章

宴春
傅遲想把一切好的都給陳落,正大光明的名分,不被桎梏的自由,還有毫無保留的愛。當他看到陳落的眼淚的那一剎那,就知道。 這輩子,他傅遲就徹底栽到陳落的手上了,而且是萬劫不復。
25.8萬字8 1539 -
完結141 章

心尖雀
【復仇+強制愛+算計+相愛相殺+青梅竹馬】 “冷澤林,你放我下來!”秦瑤有些生氣的扯了扯他后背襯衫。 “別亂動,除非你想打一架。” “……”他還真是莫名其妙。 到達酒店房間,冷澤林將她溫柔放下,秦瑤慍怒的看著他,下一秒他將她一把攬入懷中。 冷澤林炙熱的胸膛緊緊擁著她,這一刻他才感覺有了歸屬。 “你回來了,我好想你……” 冷澤林緊了緊胳膊,腦袋埋進她脖頸間,聲線里隱隱多了哭色。 這一刻他等了十八年……
26.3萬字8 166 -
完結198 章

時先生,有興趣和我結個婚麼
【糖分超高的甜寵文!!】【破鏡不重圓,男二(暗戀)上位,閃婚,先婚后愛,雙潔。】 秦書知陪沈奕琛從低谷到東山再起,眼看就要結婚,他的白月光卻回國了。 她怎麼也沒想到—— 沈奕琛會為了周思妍的一個電話就在生日當晚把她一個人拋棄在山頂不管。 他說:“生日而已,年年都有,少過一個怎麼了?” 秦書知心灰意冷,果斷提出分手。 —— 媽媽說:“一個優質的丈夫,第一條就是要溫柔體貼……” 所以,當她看到那個行為舉止體貼又溫柔的男人時,忍不住問他: “時先生,有興趣和我結個婚麼?” 忽然被求婚的時遠行努力維持著面上的矜持,謹慎地確認:“秦小姐,你,確定酒醒了?” 秦書知,“我很清醒。” 就這樣—— 本來是奔著去請人家吃頓飯的秦小姐,就這麼水靈靈地領了一個帥氣多金的老公回家。
36.6萬字8.18 194 -
完結122 章

顧總你別太過分,我們已經離婚了
【不是開局大爽文,不是開局離婚文,前期略憋屈,越往后越暢快】【追妻火葬場,雙潔,甜虐交織,情有獨鐘,婚姻拉扯,撕心裂肺,HE】 【先發瘋后清醒同傳 vs 嘴硬作死貴公子】 深夜,他闖進她房間,吻到她潰不成軍。 她拼命掙扎,卻還是被他抱進懷里,一次次淪陷。 她以為他千里迢迢飛來美國,是來哄她回家的。 結果,他只是來接“妹妹”和外甥,順便把她睡了。 * 三年前,陸語婳成為顧瑾衡的妻子。 顧家是東城頂級豪門,而她,那時已是落魄千金。 她以為自己會一生幸福,卻發現這場婚姻是她最錯誤的選擇。 他說愛她,卻從未給過她應有的尊重。 他那個所謂的“妹妹”,仗著是他救命恩人的女兒,總是挑撥他們的關系。 一句“你就是我退而求其次的選擇”,擊碎了她所有的驕傲。 她決定結束這段婚姻。 * 離婚后,他卻拼了命想把她追回來。 人情債,苦肉計,死纏爛打,卑微乞求…… “我不跪,你就要吃苦頭了,我舍不得。”他為了她在仇人面前下跪。 “我是個正常男人,心愛的女人對我投懷送抱,我有反應很正常吧?”他開始沒臉沒皮。 清冷禁欲的貴公子使出渾身解數,命和尊嚴都可以拋棄,只求她能回頭。 結果因為她一句話,他真的差點連命都沒了。
22.5萬字8 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