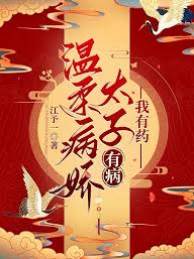《頂級偏愛!陛下輕點寵》 第1卷 第3章 崔寶珠還是那塊甩不掉的狗皮膏藥
晉國公府,書房。
趙文靖正臨窗練著大字,筆走龍蛇間,神卻有幾分不屬。
仆從丁二輕手輕腳地走進來,垂手立在一旁。
趙文靖擱下筆,頭也未抬,似是隨口問道:“今日崔家那位,可有送什麼東西過來?”
丁二恭聲回道:“回小公爺,不曾。”
丁二心里納罕,小公爺昨日便問過一回了,今日怎麼又問?
他到底是盼著崔大姑娘送東西來呢,還是不盼著?
平日里,小公爺不是最煩這位崔大姑娘,嫌糾纏不休麼?
說起來,這位崔大姑娘也真是執著。
自打三年前小公爺順手救了一次,這三年來,真是風雨無阻,日日都遣人送東西過來,不是時興的筆墨紙硯,便是些致吃食,還有各種小玩意兒。
也就是崔大姑娘那位早逝的母親是商家出,嫁妝厚得嚇人,才經得起這般年復一年地送。
旁人家的姑娘,哪有這般手筆。
趙文靖把筆放筆洗,抬起眼眸,向窗外看去。
今日的天格外好,碧空如洗,云淡風輕。
可不知為何,他心中總有一莫名的煩悶。
“小公爺,要不,小的去打聽打聽?”丁二小心翼翼地問道。
趙文靖聞言,手指微微一頓,臉上卻不半分波瀾。
“的事,與我何干?”
“是是是,小的多了。”丁二連忙低頭認錯。
趙文靖確實一整天都有些心不在焉。
午飯送上來,也只是略了幾筷子便撤了下去。
他坐在書房里,手里的書沒翻兩頁,又走到窗邊,看著庭院里被風吹的樹影出神,連丁二幾次出都沒察覺。
到了傍晚,丁二照例進來布菜。
見小公爺依舊是那副若有所思的模樣,丁二猶豫了一下,還是低聲稟報道:“小公爺,下午小的出去辦差,順道聽了一耳朵……說是崔家大姑娘,昨日在崔家祠堂跪了一宿,夜里了涼,今兒就病倒了,聽說還發著熱。”
Advertisement
正拿起筷子的趙文靖作一頓,皺了一天的眉頭總算松懈下去,接著又深深蹙起,他將筷子放下,沉片刻,吩咐道:“我們府里不是有些上好的傷寒藥麼?明早你挑些好的,給崔府送過去。”
話音剛落,他又立刻改口:“別等明早了,現在就派人送去,就說……就說是我母親聽聞,略表關懷。”
“是。”丁二應了一聲,不敢多問,連忙轉出去安排。
等丁二再回來伺候時,驚訝地發現,可能是中午沒吃,壞了,小公爺今晚的胃口竟出奇地好,不僅多添了一碗飯,桌上的幾樣菜也幾乎都吃了。
/
如善堂,檀香裊裊。
崔老夫人捻著佛珠,半闔著眼,呷了口茶,才緩緩開口問道:“寶珠那丫頭,這都幾日了,可好些了?”
劉湘君坐在下首,聞言忙放下手中的茶盞,臉上出恰到好的憂:“回老夫人,還沒好利索呢,整日懨懨的,藥也喝不進去多。唉,說來也怪,這病氣竟還過了人,前天雪兒也有些著涼不適,把我擔心壞了。”
頓了頓,話鋒一轉,帶上幾分慶幸和激:“不過還好,國公夫人聽聞后,當天就遣人送來了上好的傷寒藥,雪兒吃了兩劑,昨日便大好了,估計過兩日又能來給老夫人你請安了。”
崔老夫人聽了這話,臉上明顯出滿意之:“哦?國公夫人命人送了藥來?”點了點頭,“看來,不僅小公爺看重咱們雪兒,連國公夫人也對雪兒十分滿意。這倒是樁好事。”
看向劉湘君,吩咐道:“既如此,你仔細挑些像樣的東西,備一份厚禮,送去國公府上,就說是我們崔家的一點心意,謝國公夫人的關懷。咱們禮數上可不能差了,免得讓人家說我們不懂規矩。”
Advertisement
“是,媳婦記下了。”劉湘君溫順應下,隨即又嘆了口氣,面帶愁容,“只是,寶珠院子里的幾個使丫鬟,這幾日也接二連三地病倒了,躺在床上起不來。大夫來看過,也說是了風寒,但這病來勢洶洶,瞧著傳染還厲害的,媳婦這心里,實在是有些不安……”
崔老夫人聽得眉頭又皺了起來,臉上閃過一不耐和嫌惡:“既是如此厲害的病癥,又容易過了人,還留在府里做什麼?平白讓旁人也跟著擔驚怕。”
當機立斷道:“這樣吧,打發人把挪到城外莊子上去靜養,那里清凈,也免得再傳染了旁人。等病徹底好了,再接回來就是。”
劉湘君眼中飛快地掠過得意之,面上卻依舊是那副恭謹憂慮的模樣,低聲應道:“老夫人思慮周全,媳婦這就去安排。”
/
丁二捧著一個不算小的梨花木匣子進來,恭敬地放到趙文靖書案一角。
“小公爺,這是方才崔府派人送來的回禮,說是謝國公夫人前幾日送藥的關懷。”
趙文靖正對著一幅剛畫了一半的山水圖出神,聞言并未立刻回頭,只淡淡“嗯”了一聲。
丁二見狀,便自顧自打開匣子,將里頭的東西一一取出,里還輕聲念叨著:“這崔家出手倒還算大方,瞧瞧這端硯,極好,還有這玉蟬紙,手溫潤,是上等貨,配著這塊羊脂玉的紙鎮,倒也相得益彰……”
他一邊擺放著這些文房雅,一邊覷著自家主子的神,忍不住又加了一句:“小的就說嘛,崔大姑娘對小公爺慕得。前些日子沒靜,估著是病著難,這病一好,不就又地送東西來了?”
Advertisement
聽到這話,趙文靖終于轉過來,角噙著笑意地看著那些致的禮品。
他拿起那方羊脂玉紙鎮,手溫涼,面上卻出幾分嫌棄與不耐:“我還當真轉了子,知道什麼分寸了。沒想,還是那塊甩不掉的狗皮膏藥。”
話是說得難聽,可他眉宇間這幾日揮之不去的霾,卻似乎被窗外進來的驅散了不,連帶著看那匣中之的眼神,也和了許多。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91 章
農門貴妻相公掌上寵
一場戰火她從秦芷變成秦青芷,一冊兵書送出,她從秦青芷變成周萱兒,經曆讓她明白,她要想安穩過日子,這輩子就老實當好村姑周萱兒。爹孃一對,年紀不小,繼兄窮秀才一個,‘親’哥哥一,二,三個,嫂子三個,侄子侄女若乾,一家子麵色青黃,衣服補丁摞補丁,能不能長大都懸,有心改變,可現實教會她出頭的鳥會被打,她隻能小心翼翼裝傻賣萌提點潑辣娘,老實哥哥,哎,她實在是太難了。他是村裡人嘴裡的小公子,五年前他們母子帶著忠仆來到這裡落戶,家有百來畝地,小地主一枚,村裡人窮,地少人多,為餬口佃租了他家的地,因他年紀小,人稱小公子。周萱兒第一次見這小公子被嚇,第二次見覺得這人有故事,自己也算有故事的一類,兩個有故事的人還是不要離得太近,可村裡就這麼大,三次,四次之後,不知何時閒言碎語飄飛,她氣得頭頂冒煙要找人算賬,卻發現罪魁禍首就在自己身邊。娘啊..你這是要你閨女的命呀。什麼,媒婆已經上門了,你已經答應了。周小萱隻覺得眼前一黑,腦海裡隻一句話,我命休矣!
60.6萬字8 25676 -
完結801 章
穿越后,我被竹馬拖累成了皇后
顧靜瑤很倒霉,遇到車禍穿越,成了武安侯府的四小姐上官靜。 穿越也就算了,穿成個傻子算怎麼回事啊?! 更加倒霉的是,還沒等她反應過來呢,她已經被自己無良的父母「嫁」 進了淮陽王府,夫君是淮陽王有名的呆兒子。 傻子配獃子,天設地造的一對兒。 新婚第一天,蕭景珩發現,媳婦兒不傻啊! 而上官靜則發現,這個小相公,分明機靈得很啊……
147.3萬字8 12394 -
完結616 章

攝政醫妃不好寵
大婚當前被親妹妹一刀捅進心窩,摯愛扭頭就娶了殺她的兇手。一夜之間,她失去了親人、愛人,和家。 逆天崛起記憶恢復,才發現爹不是親爹娘不是親娘,自己十多年居然認賊作父! 好,很好! 忍無可忍無需再忍,作為23世紀的戰區指揮官兼戰地軍醫,她左手醫毒雙絕右手機槍大炮,虐渣絕不手軟,還混成了當朝攝政大公主! 嫁給逍王了不起?信不信我叫他永遠也當不了皇帝? 娶了白蓮花了不起?反手就讓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逍王殿下:“阿辭,要怎樣你才能原諒我?” 楚辭:“跪下叫爸爸!” 奶奶糯糯的小團子:“父王,螞蟻已經準備好,不能壓死也不能跑掉,父王請!”
106.5萬字8.18 36798 -
完結23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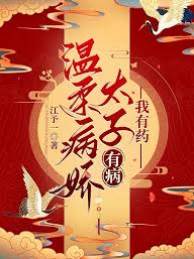
溫柔病嬌太子有病,我有藥
【古言甜寵 究極戀愛腦深情男主 雙潔初戀 歡快甜文 圓滿結局】 謝昶宸,大乾朝皇太子殿下,郎豔獨絕,十五歲在千乘戰役名揚天下,奈何他病體虛弱,動輒咳血,國師曾斷言活不過25歲。 “兒控”的帝後遍尋京中名醫,太子還是日益病重。 無人知曉,這清心寡欲的太子殿下夜夜都會夢到一名女子,直到瀕死之際,夢中倩影竟化作真實,更成了救命恩人。 帝後看著日益好起來,卻三句不離“阿寧”的兒子,無奈抹淚。 兒大不中留啊。 …… 作為大名鼎鼎的雲神醫,陸遇寧是個倒黴鬼,睡覺會塌床,走路常遇馬蜂窩砸頭。 這一切在她替師還恩救太子時有了轉機…… 她陡然發現,隻要靠近太子,她的黴運就會緩緩消弭。 “有此等好事?不信,試試看!” 這一試就栽了個大跟頭,陸遇寧掰著手指頭細數三悔。 一不該心疼男人。 二不該貪圖男色。 三不該招惹上未經情愛的病嬌戀愛腦太子。 她本來好好治著病,卻稀裏糊塗被某病嬌騙到了手。 大婚後,整天都沒能從床上爬起來的陸遇寧發現,某人表麵是個病弱的美男子,內裏卻是一頭披著羊皮的色中餓狼。 陸遇寧靠在謝昶宸的寬闊胸膛上,嘴角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真是追悔莫及啊~
42.5萬字8.18 79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