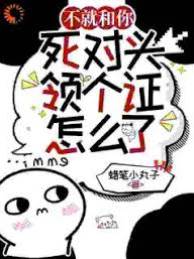《惡吻》 第345章 沉婪59.
藍婪剛走沒一會兒,許輕宜就回來了。
沒想到沒趕上見面,許輕宜問了沈硯舟跟藍婪聊了些什麼。
好一會兒,又問了他一個問題:“如果讓你選,一個是你的人,可以轟轟烈烈的那種。一個是適合結婚過日子的人,你最后會選誰?”
沈硯舟都不用想,“日子怎麼可能跟誰過都一樣?我當然是選能轟轟烈烈一起相的人,否則活一世多沒意思?”
選一個適合過日子的人,或許短時間相敬如賓,一切都覺很好,不用磨合,不用爭吵。
但缺了一份激,日子看似天朗氣清,卻寡淡無味,過一天就能看到將來一輩子是什麼樣子,多無趣?
許輕宜輕輕嘆了口氣,“如果是以前的我,我肯定會選適合過日子的男人。”
因為那時候沒有選擇的余地和權利。
但現在的話,日子要什麼有什麼,再沒有一個能夠得徹骨的人,那好像確實沒什麼意思?
藍婪從小含著金湯匙長大,備挑三揀四的資格,但說實話,許輕宜不知道會怎麼選。
因為戴放過分優秀,日久生也不是不可能?
“你的意思,如果藍婪最后選的是戴放,我們就不用管了?”沈硯舟很認真的征求意見。
畢竟,藍婪選擇戴放,跟他們就沒什麼親戚關系了。
許輕宜嗔他一眼,“我哪有這麼說?不管藍婪選誰,那孩子反正我很喜歡,怎麼都喊我一聲姑姑的。”
藍婪要是哪天被許沉得落魄了,孩子不也得跟著苦嗎?
所以,還是得勸勸許沉不要太過分。
沈硯舟明白了,“聽老婆的,改天我替藍婪打個招呼,專利或者項目,至有一個讓落袋為安。”
沈硯舟也找了個時間跟許沉聊了幾句的。
Advertisement
現在的許沉不像過去了,開始完全釋放他骨子里的強和倔,只是反問他:“讓你眼睜睜看著七七帶著孩子跟別的男人生活一輩子,你能放手?”
沈硯舟噎了噎,“……咱倆這況可不一樣,我沒跟輕輕吵得不可開,咱倆也不存在商業競爭。”
許沉冷冷丟了一句:“那你還來問什麼。”
完全沒有可比,當然就沒有共。
沈硯舟還真是啞口無言。
最后只能勸他悠著點,反正不管藍婪苦還是孩子苦,許沉自己不也得跟著心疼麼?
。
藍婪一直在維系電網那邊的人,專利局那邊也跑了兩趟,該講的道理都跟他們講了。
但看起來沒有多大的作用。
戴放知道發愁什麼,第一次提出來幫,“陸危回來了,有些人脈還是能借一借的,改天我替你去走一趟。”
藍婪一聽立馬拒絕。
嚴防死守的一條,就是絕對不讓戴放為了生意上的事做任何利用職務之便的事。
尤其現在很敏,許沉也不知道會干什麼,萬一揪住戴放的辮子就很麻煩很麻煩。
戴放只是微笑,“我現在是你丈夫,孩子的爸爸,總不能看著你眉頭一天比一天,什麼都不做?”
藍婪很嚴肅,“總之不行,我能解決。”
甚至都覺許沉就等著戴放手呢,他這麼,然后戴放一手,他那邊反手一個舉報。
戴放靜靜看了一會兒,“怎麼解決,找許沉?”
藍婪抿了抿,“只要能解決,各種辦法肯定要試一試。”
然后笑笑,讓他寬心,“到不得已的時候,再找你幫忙。”
為了不讓戴放牽扯進來,藍婪只能第一時間去找了許沉,生怕戴放作比快。
許沉上次說過他住在白云青苑,沒記錯的話,那是在離婚協議的給他的一套房子。
Advertisement
藍婪本來不想來他住的房子里,但是想來想去,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方便談事,也容易被人捕風捉影。
但沒有要進去的意思,就在樓下的車里等著。
許沉的電話一直沒人接。
等了快半小時,那邊終于接通了,“我在白云苑樓下,談談。”
許沉言簡意賅,“十分鐘。”
十分鐘后。
藍婪看著許沉那輛軍綠的越野從小區外面回來的,原來他不在家。
沒有要下車的意思,只是把車窗降下來。
許沉的車走到跟前排平齊的位置停下,也降了車窗,就一句:“到我車上,或者我去你車上,要麼上樓,你自己選。”
藍婪本來想就這麼談的,不想跟他共一個仄閉的空間。
“就這麼聊,耽誤不了你幾分鐘。”表很淡。
剛說完,許沉卻突然升起了車窗。
藍婪皺起眉,就看著他打開車門下來,徑直走過來敲車窗。
警惕的看著他,“我不會讓你上車,就這麼聊也好。”
“開門。”他目落在臉上。
藍婪選擇無視。
許沉不知道不是詭的笑了一下,“你是想試試我能不能抬手砸爛這扇車窗麼?”
聽著這種流氓的發言,藍婪臉都變了,很想罵人。
因為也想起了他們離婚之后某一天去開一個車的時候,發現那個車玻璃被砸爛了。
當時不知道怎麼回事,現在這麼看,應該是破案了。
許沉看似了無意味的勾,卻每一寸氣息都著霸道,“我就是流氓,你不用懷疑,你和李振民最初看上我不就因為這個。”
第一次聽到他說這種話,藍婪是下意識的皺眉。
就算舅舅是那麼個意思,就算只是想借種,但從頭到尾從來沒有要貶低他的意思,可他現在說這話更像是用自貶來諷刺的居心不良。
Advertisement
藍婪不得不把后座的車門鎖給他打開。
可許沉似笑非笑的看著,“就這麼怕我坐副駕。”
藍婪不耐煩了,“你差不多行了,趁我還有心思跟你談。”
許沉挑眉,“你也可以走。”
他真的折回去拉開了自己的車門。
藍婪眉頭皺得更了,這人現在是越來越讓人討厭了。
還好,在覺得自己拉不下面子把他回來的時候,許沉自己又過來了。
只不過這次手里多了一個牛皮袋。
許沉拉了一下副駕駛的車門,開了,隨即彎腰坐進去。
那會兒,藍婪才看了他手里那個袋子。
但是外皮什麼都沒寫,只看得出來已經拆開過了。
許沉坐好后側首看向,“要看看麼?”
藍婪把視線撇了過去,“沒興趣。”
許沉也沒強迫,只是自己重新把里面的紙張了出來,看得出作之間比較小心。
“那就我替你多看兩遍,好好看看你的孩子,為什麼會跟我的DNA比對相似值高達百分之九十九……”
藍婪驟然扭頭看過去,一把將他手里的東西扯了過來。
許沉在一旁不疾不徐的提醒:“輕點,就一份,別跟我弄壞了。”
藍婪這會兒一腔往上涌,瞳孔都忍不住張大,瞪著他,“你從哪來聲聲的生標本?”
藍婪當然也一眼就看到了最后的鑒定結果。
第一反應就是想直接撕了!
這樣的東西,如果被有心人看到,依舊是個大麻煩。
許沉也不著急,只是淡淡看著,“你可以撕,但是我不保證你撕完,我對你做點什麼。”
藍婪現在看他總覺得他瘋了,不像許沉。
又或者,可能是一直都沒有了解真正的許沉。
他側過,沉默的盯著。
“我說晚幾年要孩子,是你一意孤行。現在孩子出來了,你竟然還想讓我不知嗎?幾個意思。”
Advertisement
藍婪諷刺,“不想要孩子的是你。”
他理直氣壯,“我的不想要,針對于現況,而不是針對孩子。”
藍婪平時跟人對峙永遠都不會輸,但對著許沉總是覺得百口莫辯。
然后反應過來,今天不是來吵架的,差點被他這一紙鑒定完全轉移注意力。
“生他那天在下雪是麼。”許沉問。
他知道孩子藍雪聲。
藍婪不想跟他說話。
兀自扭頭往窗外看了一會兒,平復后提起正事,“我知道你目前本就沒有新材料研發,既然你如愿以償知道孩子世了,別站著茅坑不拉屎?”
許沉扯了扯,“今天如果是你告訴我的這件事,我肯定雙手把專利給你奉上。”
“這專利本來就是我研究室的!”藍婪真是氣得無語。
“你不就是仗著自己上有點功績,暗中控別人卡著我嗎?”
許沉也沒有要否認的意思。
突然看了,“戴放不是很厲害嗎?讓他也仗著自己的地位,幫你控一下不行麼。”
果然,他就沒安好心。
“你不用打戴放的主意,我絕對不可能讓他因為我及紅線。”
許沉笑了笑。
“是因為怕他及紅線,還是怕你欠了他的沒什麼可以還?因為,你給不了他……”
“我跟他是夫妻!”藍婪氣得都不知不覺拔高了聲音,“你不用在這里挑撥離間。”
許沉點點頭,“知道,不用強調。”
他的手忽然過來的時候,藍婪幾乎下意識就屏住了呼吸,眼神都是警惕的,“你干什麼!?”
那種警惕到幾乎炸的表讓許沉然而眼神興味。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12 章

虐死夫人后沈少他瘋了
五年前,一場荒唐的婚姻,將他們捆在一起。十年暗戀,她終于鼓足勇氣,對他說:“我喜歡你,你就不能試試,也喜歡我嗎?”他卻冷言冷語說:“我瘋了才會喜歡你。”可后來,她離開的第一年,他守著她的墳墓,酒醉道:“女人多的是,我不是非你不可。” 第二年:林小冉,我沒有對不起你,你回來好不好 ?第三年:我不信,我不信你不在了,只要你醒來,我們試試。 ...林小冉消失的第五年,沈懷瑾瘋了......
61.8萬字8 562746 -
完結2545 章

帝少蜜寵令:嬌妻,休想逃!
「厲嘯北,給我滾下床……」 「床玩膩了,你想解鎖新技能?」 「厲嘯北,別不要臉……」 「寶貝,只要你現在朝我撲過來,這臉……爺就不要了」 深夜,他悄悄潛入臥室…… 「想想,我發燒了,渾身都腫了,不信你摸」 「王八蛋,你把我的手往哪兒放」 世人都傳厲嘯北心狠手辣,無心無情,卻不曾知道。 四年前她消失,他為了一個人差點毀了一座城。 對厲嘯北而言,白想是毒,無葯可解!
223萬字8.18 91953 -
完結303 章

前妻有喜,陸總請排隊恭喜
【男主追妻火葬場、男二橫刀奪愛(雄競雙潔)】【雙向暗戀,誤以為雙向有白月光】 【假無能真大佬女主×毒舌腹黑太子爺】 去阿勒泰滑雪那年,才十歲的江映月被家人遺棄在雪山凍得瑟瑟發抖,是陸承影把沒人要的她撿回去。 穿著一身滑雪服的少年脫下外套裹在她身上:“哥哥送你回家。” 從那時候起,她的目光都在少年身上,直到十八歲訂婚,二十歲步入婚姻殿堂,二十三歲離婚。 她知道他的心從未在她這里,他一直有一個白月光,當初在雪山,他也是為了找白月光江微微,順帶找到了自己。 * 聽到她被遺棄在雪山,陸承影第一時間去找到。 聽到她被父親安排相親,他第一時間找母親去要她。 聽到她說要離婚,他手足無措,只覺得要想盡辦法抓住她。 看到她靠在別人懷里,知道她有喜歡了十年的別人,他心癢難耐,護了這麼多年,怎可拱手相讓。 情急之下,將她抵在墻角,輕咬她的耳垂,低聲威脅:“不想讓你的心上人聽見,就別出聲。”
58萬字8 190 -
連載51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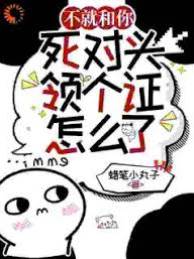
不就和你死對頭領個證,怎麼了?
第三次領證,沈嶠南又一次因為白月光失了約;民政局外,江晚撥通了一個電話:“我同意和你結婚!” 既然抓不住沈嶠南,江晚也不想委屈自己繼續等下去; 她答應了沈嶠南死對頭結婚的要求; 江晚用了一個禮拜,徹底斬斷了沈嶠南的所有; 第一天,她將所有合照燒掉; 第二天,她把名下共有的房子賣掉; 第三天,她為沈嶠南白月光騰出了位置; 第四天,她撤出了沈嶠南共有的工作室; 第五天,她剪掉了沈嶠南為自己定制的婚紗; 第六天,她不再隱忍,怒打了沈嶠南和白月光; 第七天,她終于和顧君堯領了證,從此消失在沈嶠南的眼中; 看著被死對頭擁在懷里溫柔呵護的江晚,口口聲聲嚷著江晚下賤的男人卻紅了眼眶,瘋了似的跪求原諒; 沈嶠南知道錯了,終于意識到自己愛的人是江晚; 可一切已經來不及! 江晚已經不需要他!
92.8萬字8 96 -
連載405 章

抵不住京圈大佬深情引誘
【京圈大佬+先婚后愛+甜寵+蓄謀已久+雙潔】【高冷禁欲假浪子 vs 溫柔嬌軟女教授】 京北名流圈皆知,傅氏集團掌舵人傅凜舟是出了名的風流客。 為了拿到四億投資款,梁知微被迫和他結婚。 領證那天,男人對她說:“跟我結婚,沒你想的那麼壞。” 她賭氣:“跟我結婚,比你想的壞。” 三年后,她留學歸來,搬進傅家。 大家都以為,要不了多久,她就會從傅家滾出來。 包括她自己也這樣想。 …… 可沒想到,在一次貴族私宴上,有人看見傅凜舟將她抵在墻角,溫聲軟語地對她說:“今晚要兩次?” 梁知微揚起嘴角,輕輕一笑,露出一對淺淺的梨渦:“不行!” 男人輕笑,攬腰將人揉進懷里,吻到她氣息凌亂,修長的指節在衣擺處試探:“不同意?我便繼續!” 從此,京北有了另一種說法:浪子在梨渦里翻了船。 女主視角:先婚后愛 男主視角:蓄謀已久 PS:純甜文,越往后越甜。
75.9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