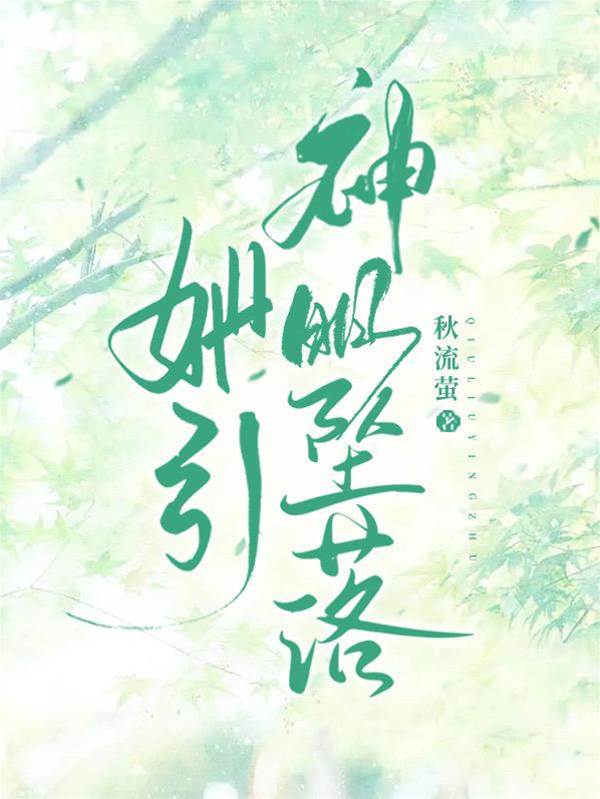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引狼入室》 第90章
林廖遠被接連拋出來的話堵得噎住,不可置信:“搞死我們?我們是一家人啊!”
“你現在覺得我們是一家人了?”林瑯意眉尾上挑,譏諷道,“一家人這種話是在上說說的嗎?每一次涉及到真正的利益,你捫心自問,你真的有把我公平公正地當一個家庭員看嗎?”
“如果早知道應山湖有今天,它會得到我手裏嗎?”
的語氣太兇,林廖遠用手臂攀著桌沿,眼睛裏泛起淚花,說話時帶了音:“你在怪爸爸媽媽,珠珠,你確實是最適合經營公司的人,爸媽都心知肚明,可是,可是我們有兩個孩子啊,我們不能——”
“不。”林瑯意其實已經不失了,平靜地陳述,“你們心裏,其實一直只有一個孩子。”
“不是這樣的。”他直起子往前傾,手臂上有點點的褐曬斑,“珠珠,分給你們的時候我跟你媽媽是仔細考慮過的,你看,應山湖與你大學在同一個城市,G市則是你未來嫂子的住所。而且你一個孩子,我們也不想讓你一個人太辛苦,要飛到這麽遠的地方一點點打拼起來,所以家裏先幫著將G市的公司打好地基了,以後全盤扔給你哥哥讓他後半輩子自己鬥,然後我們可以再舉全家之力一起建設應山湖,一起幫你,我們是為你好。”
他將兩只手掌往上攤開,像是左右托舉著天平一樣比較:“因為G市發展得早,這才看起來這兩家公司更好一點,但你看……應山湖後來居上了。”
“嗯,我現在也是這麽做的。”林瑯意很平靜,“爸,你一個五十好幾的人了,我也不想你這麽大年紀還那麽辛苦,所以我先好好發展公司,然後再孝順您,您就不必再在公司裏早出晚歸,反正你們有兩個孩子,我跟我哥兩個人養的起你,你就早早規劃好退休生活,以後我哥要是有了孩子,你還可以在家帶帶孩子,早晚接送,買菜做飯,去公園帶著孫子孫曬曬太。”
Advertisement
林廖遠擡起來的兩條胳膊垂下去,張了張,一時間不知道說什麽。
林瑯意看著他,把那些從他口中說出來的話一一奉還給他:“我是為您好,不想您那麽辛苦地打拼。”
“至于先發展和後發展。”笑了笑,往後仰的老板椅發出“吱呀”的搖晃聲,“上行下效,我也是這麽做的,我打算把早發展的淡水珠條線給哥哥做,現在再‘舉全家之力’一起發展海珠線。”
林廖遠張口結舌,G市這兩個公司原本去拉投資就是為了大面積鋪開拿應山湖做測試後功的清水化養技,結果錢拿到了,卻大方向一變,去發展海珠線了,到手的答案作廢,答題卡本是另一張,并且剩下的淡水珠條線本就不再是公司的主營業務了。
現在林向朔再去經營淡水珠,這跟把人塞到犄角旮旯的流放崗位有什麽區別。
“珠珠,爸爸只想說一點,”林廖遠無力道,“我跟媽媽都是你的。”
“我也你們。”林瑯意凝視著他,一字一句道,“爸爸,我像你們我一樣,你們。”
“我用你們我的方式,來你們。”
“這是你們教會我的家庭相模式,我也只會這樣依樣學樣。”
“我有時候恨你們對我太絕,有時候又恨你們對我還不夠絕,就好像一只帶絨外套的熱水袋一樣,其實裏面的水已經冷了,但針織外套還留有餘溫,所以總覺得它還是可用的,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如果你認為這樣的家庭關系是正確的,那我現在對你,對哥哥的人事安排就是在做正確的事,如果你認為這樣是不對的,”林瑯意歪了下腦袋,笑容很淡,“你會認為這是不對的嗎?可能這輩子都不會了。”
Advertisement
林廖遠當著的面徹底紅了眼眶,他的眼窩其實一直很深,睡不好的時候眼皮垂下來,顯得眼袋有些重。
他臉上也有曬斑,經年累月,像是沒有陳舊牆壁上泛黃剝落的牆灰。
他一直在吞咽緒,閉,兩頰偶爾一下,沒有洩出半點聲音,實在難忍時才會擡起手,用虎口抹去眼角的淚花。
林瑯意撇過頭,向窗外,同樣保持了沉默。
“其實現在再說這些也沒用了,我來這裏就沒想過讓你再吐出來,”他再說話時嚨裏像是卡了一口痰,沙啞道,“爸爸知道你會把公司經營得很好的,我們都知道,我來找你之前,在你的會客室坐了一個小時,腦子裏都是你從小到大拿的獎狀,說出口的那些妙語連珠的機靈話,你一直是我們的驕傲。”
“我聽了你剛才說的那些話,我知道了,我聽進去了,珠珠,我們不是仇人。”他在說到“仇人”時實在沒忍住,大口頻繁了幾口氣,最後用手掌橫著捂住眼睛,張開無聲地著瓣。
好半天,他才移開手,放下手之前又用手背了眼睛:“爸爸,是爸爸的錯。”
林瑯意屈起手指,用指節抵住山閉了眼,頓了頓,將椅子完全轉過去,面向窗外。
“二十萬個蚌下水了,海珠培育時間更長,等待的時間也更久,”說,“但沒關系,我有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我會一直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我吃得起苦,摔得起跤。”
“人不能完全離原生家庭的影響,你如果真的覺得虧欠了我,那就在以後的日子裏好好讓我改觀,我才能學著你的方式,一點點反哺給你們。”
“你要教我,那就言傳教。”
門外周敲門提醒時間,林瑯意隔著門應了一聲,低頭整理面前的東西。
Advertisement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跟家庭的關系就好像是一只等待的蚌,我也不知道自己一直浸在水裏最後會養出來一顆什麽東西,是爛珠,是畸形的,是有黴點的,還是你們告訴我的,是圓潤漂亮的一顆珍珠。”
那些資料被拿在手裏“篤篤”理齊,看著林廖遠,說:
“從注一粒沙子的時候開始,我們之間的關系就再也切不斷了,孕育環節中,將蚌打開,蚌就死了,把珍珠拿出來,珍珠也型了再也不會變大了,我們誰都離不開誰,要說痛苦,沒有一只蚌是不痛苦的。”
“你今天流的眼淚,可能,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經流過了。”背對著人往外走去,頭也不回,“很公平。”
*
走出會議室,周照例抓住這點時間提醒林瑯意接下來的日程。
在此之間,提醒:“林董,您看日程需不需要再調整下?我剛才確認了下明日的航班信息,如果按照現有安排,您可能趕不上葬禮。”
林瑯意在心裏默念了一遍日程,實在沒看出哪裏能調,將視線轉到周臉上時,也為難地搖了搖頭:“所以我也拿不定主意,還是看您安排。”
“那就按這個計劃吧。”林瑯意拍板,“結束後我立刻飛過去,應該能在結束前趕上。”
“但是您哥哥昨天就去了。”周低聲音說,“您晚到會不會不好?”
說:“我剛打聽過了,他好像包了棒球公開賽的前排座位,請了不人去觀看比賽。”
林瑯意一言難盡地擡起臉:“啥?”
周瞅著看,點頭。
“我現在知道為什麽林向朔天那麽努力在維護關系,關鍵時刻拿到的資金卻才那麽點……”林瑯意緩慢點頭,“人家家人去世了,他包球賽給人散心。”
Advertisement
“原楚聿腦子有病才會去。”
“原總好像會去。”
林瑯意震撼全家,再一次:“啥?”
震驚完後,馬上反應過來:“請的都是誰?”
周業務能力非常出,一連串名字報下來,連個停頓都沒有。
林瑯意皺著的眉舒展開,幾乎都是原楚聿生日宴會上的選嘉賓,大概是大家都在看風向,楚關遷去世後所有的目都停在原楚聿上了,所以他去,其他人也都會去。
“您也在名單裏。”周提醒,“另外,您看這樣的話,我們要不要做點什麽?”
“人晚到,東西當然要先到。”林瑯意出筆,在紙上“刷刷”寫下一串話,“你幫我訂束花。”
這聽起來太平平無奇了,周猶豫地想著有沒有更好的建議能說給林瑯意聽,畢竟葬禮上最不缺的就是花。
林瑯意察覺到了的躊躇,笑了下,安:“其實我還蠻擅長送禮的。”
“以前有個客戶特別寵的兒,兒是一位籃球球星的狂熱,我砸了高價轉了好幾個人才拿到球星的簽名版護腕,現在那客戶還是應山湖的長期合作方。”
“還有個,是單親家庭長大的,我去他家拜訪是送了一個實心金桃給老人家……嗯,就了,合作的價格非常香,那阿姨每次都念叨著讓我去家裏吃便飯。”
周定下心來,心想那花肯定只是其中一項,一定有更別出心裁的東西。
可等了好一會兒,也沒見林瑯意再補充,沒忍住問了句:“林董,那這次去……只有花嗎?”
林瑯意點頭:“是啊。”
這算什麽?
周有些發愁。
“花的卡片上能代寫吧,寫這個。”林瑯意用下劃線勾出,“然後寄到這裏。”
“放心,送禮,肯定要送到人心裏。”
林瑯意拍拍膛,豎起大拇指,自信道:“我擅長!”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4114 章
罪妻來襲:總裁很偏執
易瑾離的未婚妻車禍身亡,淩依然被判刑三年,熬過了三年最痛苦的時光,她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生活比在監獄中更加難捱,易瑾離沒想放過她,他用自己的方式折磨著她,在恨意的驅使下,兩個人糾纏不清,漸漸的產生了愛意,在她放下戒備,想要接受這份愛的時候,當年車禍的真相浮出水麵,殘酷的現實摧毀了她所有的愛。
361.9萬字8 2360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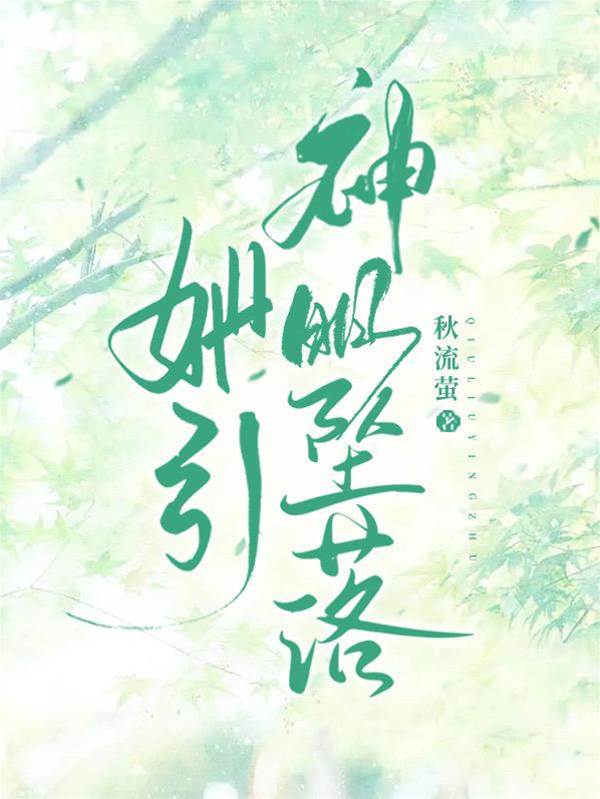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311 章

昨夜燈暖
三年前,蕭叢南被迫娶了傅燼如。人人都道,那一夜是傅燼如的手段。 於是他一氣之下遠走他鄉。傅燼如就那樣當了三年有名無實的蕭太太。 一夕鉅變,家道中落。揹負一身債務的傅燼如卻突然清醒。一廂情願的愛,低賤如野草。 在蕭叢南迴國之後。在人人都等着看她要如何巴結蕭叢南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 她卻乾脆利索的遞上了離婚協議書。
51.4萬字8 115868 -
完結120 章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小說簡介:宋家那個土里土氣又蠢又笨的真千金,忽然轉性了。變得嬌軟明艷惹人憐,回眸一笑百媚生。眾人酸溜溜:空有皮囊有啥用,不過是山里長大,
22.5萬字8.46 5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