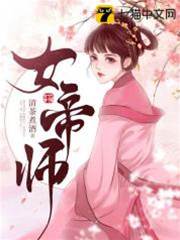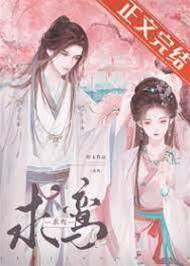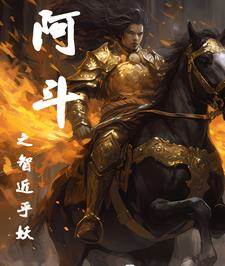《我與太子舉案齊眉》 第38章 第 38 章 “我們回家。”
明蘊之拍著柏夫人的背,柏夫人終于從即將昏厥的狀態中清醒過來,坐在木椅上,連連著氣。
含之跪在地上一個勁兒地哭,說得斷斷續續。
起因是柏夫人見韓世子亡故後,京中許多名門不願再與一個有喪夫名頭的含之定親。這也罷了,柏夫人也改了主意,并不一定要嫁在京中,決定日後回益州再商議親事。
“可這都是阿娘的想法,阿娘從未問過我願不願意……”含之拉著姐姐的角:“阿姐可知,韓家世子生前,是個什麽樣的人?”
也是前一陣才意外得知,那韓世子瞧著人模人樣,其實也是個花天酒地的紈绔,他們定親早,哪裏知曉年讀書知禮的兒郎也會變這般模樣。
“他狎飲酒,賭馬鬥蛐蛐,甚至還多次與旁人說人是非,毀人清名。阿姐,此等兒郎,妹妹不願再嫁!”
“冤孽!阿娘怎會讓你委屈第二次,往後再議親,阿娘定會與你阿爹亮眼睛好好瞧,不會再有這般……”
“含之不願!”
明含之松開手,梗著脖子道:“兒從前生活在阿娘的羽翼下,從未睜眼看過世間,如今親眼看過,只覺人間污穢,不想再以人妻人母之勞碌一生。外祖父已與兒回了信,允兒往後在柳園生活,只有阿娘不願罷了!”
堂中寂靜,柏夫人只會垂淚,呼吸急促。
明蘊之終于明白,含之此番了傷,又見京中男兒一個兩個俱是花架子,便沒了再議親之心。去信益州,與外祖父外祖母說過此事,外祖自是應下,允往後在柳園度日。
“此事你從未與爹娘商議過,是不是?”
明蘊之看著含之,問道。
“阿姐也要勸我嗎?”
明含之垂下頭,語氣頹喪。
Advertisement
是明家最小的孩子,自便千萬寵,有不順心之事。十六年來,遇到的唯一一個挫折,便是這婚事。
“不聲不響便將自己的未來定下,就不怕日後後悔?”
明蘊之看著,輕聲問。
“我不會後悔。”
含之聲音篤定:“阿姐從前與我講過,書院裏有子潛心求學,學以後,回到家鄉教人讀書明理。那時我便想,有朝一日,是否能親眼見見這樣的人。”
比明蘊之要矮上幾分,如今跪著,更是將頭擡得高高的:“阿姐從前不是也說,極敬佩這樣的人嗎?”
明蘊之看著的臉,不知何時,那個總是躲在柏夫人和後,有言語的小娘子竟長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
“我不勸你。”
明蘊之了的腦袋:“你能有自己的想法,這很好。人各有所求,你小小年紀,能想明白自己想要什麽,阿姐反而欣賞你。”
含之怔怔看一眼,忽然笑開:“阿姐!”
“只是含之仍舊有錯。”
明蘊之板著臉:“就算不與爹娘說,也該與阿姐提前商議一番,而非有此偏激之行,是也不是?”
含之收了笑,眼角含淚,低下頭:“……阿姐教訓得是。”
只是想到從前自己甚至為了韓世子哭了許多回,就打心底裏覺得惡心。
阿娘近來多次為打探世家男兒,也聽過幾句。一個兩個,不是文不武不就,只能靠爹娘謀得一半職,便是私德有虧,難以為婿的。
那些想法只在腦海中一轉,便再也忘不掉。
給益州寫了信,言辭懇切,雖不似姐姐在柳園長大,卻知曉外祖母是個慈的子,定不會見委屈還不要……明含之沒想那麽多,收到回信便與阿娘直言,誰知柏夫人反應過激,竟將關了起來。
Advertisement
也是沒了法子,只怕越到益州,越沒逃之機。只能悄悄點了火燭,趁跑走。
“如今天下雖太平,但仍有流寇匪賊作祟,你獨自一人夜裏出逃,可想清了路線,帶夠了銀兩?”
明蘊之沉著聲音:“可想過遇到賊人,該如何?若是路上累了了,在何歇腳?你甚至不知馬車該在何租賃,是不是?”
含之張了張口,徹底了子。
“我……沒想過。”
明蘊之:“與阿娘認個錯,先隨我回宮。過幾日,我派人送你去柳園。”
“二娘!”
柏夫人氣得面通紅:“你這是什麽意思,要隨著你妹妹造反不?!”
起初聽了幾句,以為是真心實意在勸含之,誰知越聽越不對,到了最後,竟說出了這種話。
“母親莫要太激。”
明蘊之使了個眼,青蕪青竹一人一邊,給夫人順著氣:
“含之去意已決,阿娘攔的後果,如今也看到了。主意大,有第一回便會有第二回,堵不如疏。”
“且讓含之與我住幾日,我再聽聽的想法,若是下定了決心,那便先送去柳園也并無不可。如今年紀小,還有後悔的餘地。”
明蘊之倒也沒一下子認定含之就這麽想好了,如含之這麽大的時候,也常常覺得當時做下的決定便是一輩子的。
若日後後悔了,有的是名頭為再尋親事。
含之跪正,給柏夫人規規矩矩磕頭認錯:“阿娘,兒知錯了,兒……”
“……都怪你!”
柏夫人忽然高聲起來,死死看著明蘊之:“若不是你當初和說什麽師師,怎會生出這麽忤逆爹娘的念頭,含之自來乖巧,都是你給灌輸的念頭!”
“不怪阿姐!”含之一驚,抱住的:“阿娘息怒——”
Advertisement
“先前你不願給商議親事,如今又攛掇著離家。二娘,你實話實說,是不是心中仍舊記恨阿娘,當初將你送去柳園?”
柏夫人哭得真意切:“所以你現在,要將你妹妹也送去,是不是?”
含之搖著頭:“這與阿姐無關,阿娘莫要……”
“母親。”
明蘊之站定,閉了閉眼,半晌,竟覺得荒謬到好笑。
“母親還不明白嗎,兒不可能依照著阿娘的想法過一輩子,兒是,含之也是。”
明蘊之看著:“母親有今日之言,想必心中對兒不滿已久,那今日,又何必送信來東宮?”
柏夫人想借的勢含之,卻沒料到會反抗這個當娘的。
做太子妃或許有許多不由己之,卻明明白白地讓到了權勢的好——早就不是任由母親做什麽都可以的明家二娘了。
柏夫人扯著帕子,淚眼汪汪地看:“含之不能走,你是太子妃,你什麽都有了,為何不能幫你妹妹一把,讓也安安穩穩地過個好日子呢?”
“母親或許以為嫁為人婦便什麽都好,”明蘊之將含之拉起來:“但不是所有人都這樣以為。”
從前因為柏夫人傷心時,曾怨過母親為何總是這樣偏心,看不見的好。
如今回憶,只覺得的有些話語可笑又可悲。
從前爹娘尚好,可時間過去,阿娘與阿爹越來越淡,子有些偏激,常常會與阿爹爭論起來。明蘊之嫁人離家前,就知道阿爹其實已經不怎麽回家了。
柏夫人年便與爹娘不親,去柳園。或許正是因此,將含之看得越來越重,一刻也離不得。
“母親先在府中靜一靜。若想通了,過幾日便與含之一道回益州,若實在想不通,兒總歸在京中,有的是功夫聽母親哭。”
Advertisement
聲音沉冷:“我或許無能,但這麽些年過去,滿足親妹一個小小心願的本事還是有的。母親若實在不滿,自可狀告我這個太子妃不孝,去世人面前評說。”
“蘊之,蘊之,二娘!”
柏夫人站起意追上,卻被青蕪攔住:“夫人冷靜冷靜,莫要再傷神了。”
“兒不孝,請阿娘珍重子。”
含之磕了個頭,站起,隨著阿姐一道出去。
明蘊之拉過的手,似年時牽著一樣。
稍行幾步,院中出現了個意料之外的凜然影。
男人長鶴立,披著個玄黑的雲紋披風。霞落在他的袍上,仿若落塵間的玉面神將。只是面依舊冷峻,看不出究竟想了什麽。
風裏帶來些沁骨的寒氣,了十月,天一日比一日涼了下來,明府門前的燈籠也被風吹得搖擺。含之站在後,拉著的手無意識了幾分。
明蘊之拍了拍的手背,安著。看向裴彧,問道:
“殿下怎麽來了?”
裴彧取下肩頭的披風,為披上。
“孤來接你回家。”
明蘊之眸了,手按著那披風,周驀地到了另一個人上的暖意,將那寒邪驅散。
“二娘!二娘別走,你再勸勸你妹妹,含之……”
他攬著明蘊之的肩頭,隨意掃過一眼追出來的柏夫人,淡聲道:“岳母大人,孤要帶蘊之回宮,也不麽?”
柏夫人的哭音忽然止住,不想太子殿下竟然會在,子晃了晃,像要暈過去。
徐公公馬上笑瞇瞇地扶著,道:“夫人累了,且先回屋休息休息,過會兒奴才讓宮中太醫來為夫人瞧瞧,開一劑安神的湯藥。”
含之掉了眼淚,用袖胡幹,沒有回頭。
裴彧張開手,將那微涼的掌心全然包裹住,拉著妻子。
“我們回家。”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1965 章
相公,說好的合離呢
一朝穿越,醒來就被塞入花轎,送去給個身中奇毒命不久矣的病秧子沖喜。蘇棠隻想既來之則安之,奈何找茬的太多,逼得她不得不擼起衣袖把夫護。解毒、虐渣、鬥奇葩!還有嫡妹想吃回頭草,虎視眈眈覬覦她相公?請有多遠滾多遠......到頭髮現,最腹黑的還是她相公,扮豬吃虎,她殺人他遞刀,她放火他扇風,明明說好的和離,怎麼就有孩子了?
183萬字8 165337 -
完結5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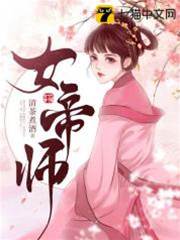
女帝師
顧清韻帶著殘破不全的記憶醒來,成了一個小宮女。 作為宮女,她知道:在宮中求生,不管閒事少說話,再找條粗大腿抱好,熬到出宮就算逃出生天。 可是,夏天棄這個落魄皇子,混得實在太差,她一時惻隱之心……
105.9萬字8 9897 -
完結1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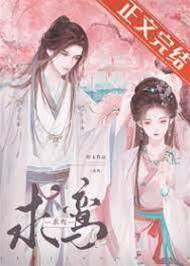
清冷駙馬竟是白切黑
少帝登基,權臣當道,靖陽公主元妤儀打算嫁入陳郡謝氏做助力。 但匆忙設計只成功了一半。 計劃中與她春風一度的,從謝氏嫡長子變成了名不見經傳的二公子,謝洵。 兩相權衡,公主最終選擇同謝二公子拜堂成親。 在元妤儀心裏,駙馬疏離有禮,是個孱弱而淡漠的正人君子,因爲老實,就算旁人欺侮到面前來也不會有絲毫波瀾。 她心軟又愧疚,對郎君便多了幾分照拂。 幾經生死,二人都動了真情。 然而成婚內情暴露後,往日真心變成了交織的利益,恩愛夫妻最終反目成仇; 面對這場本就不該開始的姻緣,元妤儀選擇簽下和離書,前塵往事一筆勾銷。 直到那夜暴雨如瀑,她險些死在刺客劍下時,曾經冷漠和離的駙馬裹挾滿身風雨而來。 元妤儀輕聲問他,“你曾讓我放你自由。” 青年垂眸,將人抱在懷裏,輕輕拂掉她眼睫微顫的淚珠,“從始至終,我只有你,也只要你。” * 謝洵是宣寧侯府見不得人的庶子。 因宮宴上誤飲了嫡兄的酒,陰差陽錯同靖陽公主共處一室。 利用心起,謝洵將錯就錯,主動請求尚公主,以便日後借皇族勢,登閣拜相。 謝二公子活的艱難,自覺是這浮華人世的一抔碎雪,從不相信真情實意。 可婚後同惡名昭彰的公主日夜相伴,昔日成見卻慢慢消失。 謝洵恍然明白,愛至濃處似火燒身,是何滋味。
29.7萬字8 3739 -
完結81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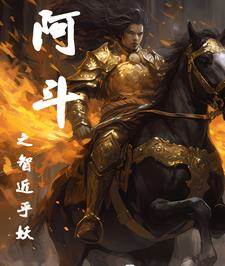
阿鬥之智近乎妖
【搞笑 爭霸 係統 種田 平推流 蜀漢中興】 親信:皇上,孫權手下的全部謀士要同您舌戰阿鬥:去確認一下,是孫權的全部謀士?親信:回陛下,全部!阿鬥一個戰術後仰:讓他們一起上吧,朕還要去養雞場視察母雞下蛋!……親信:皇上,曹操手下的全部武將要同您單挑!阿鬥:確認一下,是曹操的全部武將?親信:回陛下,全部!阿鬥一個戰術後仰:讓他們一起上吧,朕趕時間去兵工廠畫圖紙!……將軍:皇上,咱們造了50艘戰艦了,還繼續造嗎?阿鬥:造戰艦種事,就像問鼎中原一樣,要麼就別造,造了就別停。別忘了,西邊還有個羅馬等著朕呢!……丞相:皇上,這個木牛流馬是您發明的?阿鬥:不僅木牛流馬,你看那邊,還有諸葛連……啊……不對……大漢連弩!
142.9萬字8.18 61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