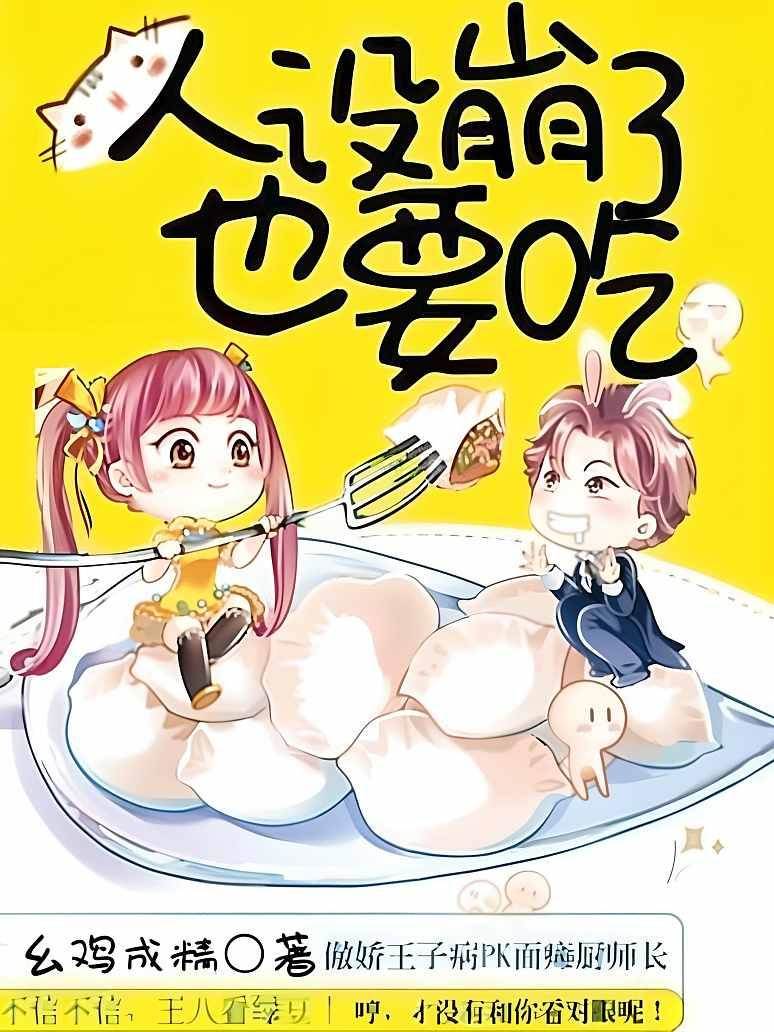《偏執小舅,不許掐我桃花!》 第55章 車震
姜酒住院期間,白天陪著,晚上姜澤言守著。
陳洋的事鬧得很大,警察把姜酒列為首要嫌疑人,臥室里到都是的指紋,也包括陳洋脖子上的那把匕首。
而姜酒的供詞一點力度都沒有,就連正當防衛也立不了。
安靜得反常,不是不想罪,而是想看看這個每天晚上都抱著睡覺的男人到底會有什麼舉。
也不知道哪來的底氣,就是想賭,在所有證據都不利的況下,賭姜澤言會不會幫。
好在,這一次姜酒沒有輸。
在醫院檢尿檢都沒檢出任何問題,姜澤言帶著自己的私人醫生,劍走偏鋒,在姜酒的胃酸里檢測到致人昏迷的藥。
對方用藥非常謹慎,尋常檢測本檢測不出來。
有了這個證據,姜酒功洗嫌疑,出院后,直接搬進了云璽府邸。
“為什麼不住梧桐閣了?”姜澤言從后圈住,細細吻稚肩。
“住久了,所以想換個地方。”
掙出,去翻包里的安眠藥,這幾夜每晚都失眠,全靠安眠藥才能合上眼皮。
姜澤言握住手腕,“別吃藥了。”
Advertisement
“不吃我睡不著。”嗓音細細的,人也清瘦了許多。
姜澤言圈住,抱上床,姜酒下意識撐起,現在對床,尤其是紅的床單都有影。
躺在床上時總覺得有雙死人眼睛在盯著。
“別怕,我們已經回家了。”
他俯溫吻額發,鼻尖,再到角,一點點試圖讓姜酒放松下來。
在醫院那幾晚,他只抱著,什麼都沒做,現在回來了,姜澤言有自己的方法讓姜酒忘記恐懼。
“小舅舅…”
在他下,小小一團,眉眼含淚俏,勾得人心,是另類的催劑。
他掌心姜酒發間包裹住后腦勺,不似以往那麼霸道,而是好耐心地吻著子。
;從前到后脊,腰線至腳踝骨,一寸寸咬開的束縛。
咬著指尖,開始微微抖,他掌心托住部,像嬰兒一樣雪白,顯得他掌紋開闊糙。
然后低頭,吻胎記。
“姜澤言。”
姜酒小聲喊了出來,面紅,呼吸全了。
“我在。”
不愿意,長勾住男人的脖子,仰起頭輕咬他結,滲出薄汗,一寸都不想跟他分離。
Advertisement
“怕什麼,嗯?”他纏進十指間,想進,姜酒突然攏住,頂著他。
男人悶笑,氣息噴在脖頸間,,有力,“故意使壞?”
姜酒他耳垂,喊了聲,“阿言。”
就像失控的那個晚上,這句阿言,讓姜澤言控制不住,發了瘋。
一夜纏綿,姜酒忘了究竟小死了幾回,也同樣忘了,那腥恐怖的畫面……
看著懷里睡的面容,姜澤言吻了吻微腫的瓣,給姜酒掖好被子,然后輕手輕腳下了床。
他穿上睡袍,徑直到書房,陸一鳴已經等他等的睡著了。
姜澤言從煙盒出煙,然后將煙盒直接拋過去,將人砸醒。
“還是什麼都沒查到?”
陸一鳴了個懶腰,一臉幽怨,“陳家勾搭的那條販毒鏈昨晚已經被搗毀,但沒人知道他到底怎麼死的。”
“姜酒家完全沒有被外力破壞過的痕跡,監控也沒有被纂改刪除過。”
“所以要麼對方是個極有經驗的高手,要麼,陳洋人指使,自愿到姜酒家自盡,并且偽裝他殺。”
“不正常。”
“哪不正常?”
Advertisement
姜澤言吐出煙圈,霧靄之下,他神凝重,“前者,姜酒沒有仇家,的生活圈子里也沒有這樣的高手。”
“后者,以陳洋的劣,死之前不可能不。”
侵犯,毀容,甚至跟同歸于盡都有可能,可陳洋卻什麼都沒做,這明顯不符合邏輯。
陸一鳴沉思了會,“有沒有可能背后的人只是想給姜酒制造一場危機,沒想過要真正傷害?”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93 章

甜心玩火:誤惹霸情闊少爺
訂婚宴當天,她竟然被綁架了! 一場綁架,本以為能解除以商業共贏為前提的無愛聯姻,她卻不知自己惹了更大號人物。 他…… 那個綁架她的大BOSS,為什麼看起來那麼眼熟,不會是那晚不小心放縱的對象吧? 完了完了,真是他! 男人逼近,令她無所遁逃,“強上我,這筆賬你要怎麼算?”
90.4萬字8 37776 -
完結155 章
她不乖!要哄
【爆甜輕松 雙潔治愈 野性甜寵 校園】【嬌縱隨性大小姐x邪妄傲嬌野少爺】“疼!你別碰我了……”季書怡微紅的眼圈濕霧霧的瞪著頭頂的‘大狼狗’,幽怨的吸了吸鼻子:“你就會欺負我!”都說京大法學系的江丞,眼高于頂邪妄毒舌,從不屑與任何人打交道,只有季書怡知道背地里他是怎樣誘哄著把她藏在少年寬大的外套下吻的難舍難分。開學第一天,季書怡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惹了江丞不爽。所有人都以為她要完。可后來眾人看到的是,大魔王為愛低頭的輕哄:“小祖宗,哪又惹你不高興了?”季書怡永遠記得那個夜晚,尋遍了世界來哄她的江丞跪在滿地荊棘玫瑰的雪夜里,放下一身傲骨眉眼間染盡了卑微,望著站在燈光下的她小心翼翼的開口:“美麗的仙女請求讓我這愚蠢的凡人許個愿吧。”她仰著下巴,高高在上:“仙女準你先說說看。”他說:“想哄你……一輩子。”那個雪夜,江丞背著她走了很遠很遠,在他背上嬌怨:“你以后不許欺負我。”“好,不欺負。”——————如果可以預見未來,當初一定不欺負你,從此只為你一人時刻破例。你如星辰落入人間,是我猝不及防的心動。
24.2萬字8 17171 -
完結1206 章

相親當天,閃婚了個億萬富翁
【甜寵+先婚后愛+傲嬌男主】 相親當天就鬧了個大烏龍,安淺嫁錯人了。 不過,錯有錯著,本以為一場誤會的閃婚會讓兩人相敬如賓到離婚,安淺卻驚訝地發現婚后生活別有洞天。 她遇到刁難,他出面擺平。 她遇到不公對待,他出面維護。 安淺天真的以為自己嫁了個錦鯉老公,讓她轉運,卻萬萬沒想到,自己嫁的竟然是億萬富翁!
192萬字8.18 17167 -
完結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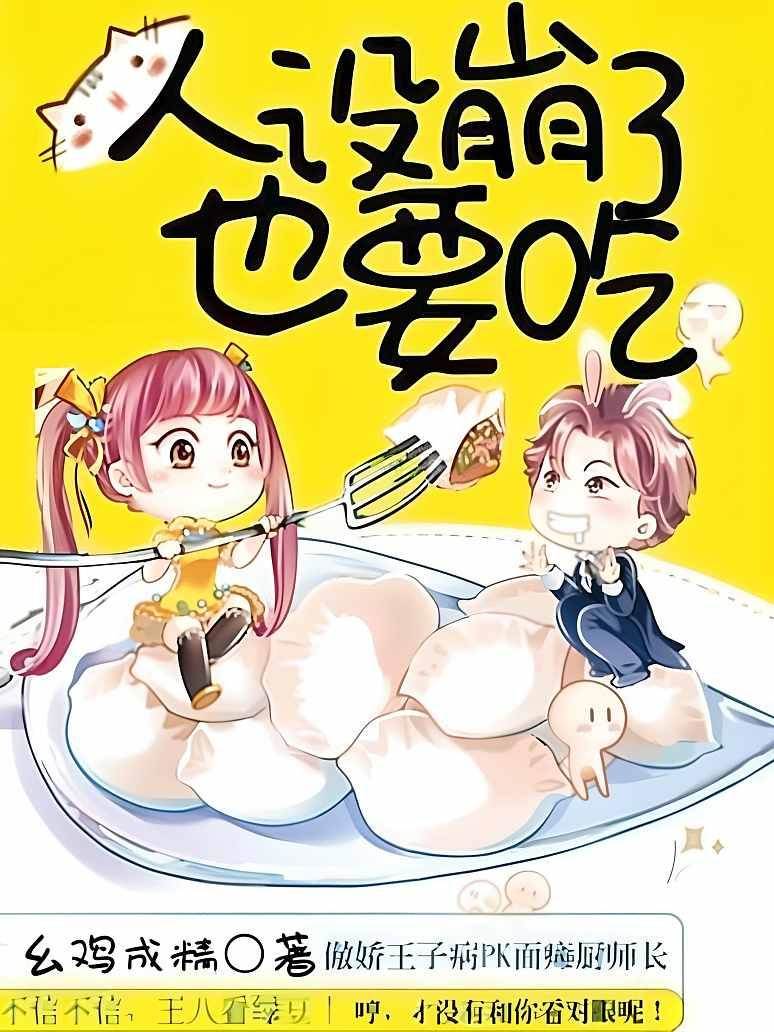
人設崩了也要吃
【那個傲嬌又挑剔的王子病和他面癱很社會的廚師長】 當紅明星封人盛,人稱王子殿下,不僅指在粉絲心中的地位高,更指他非常難搞。直到有一天,粉絲們發現,她們難搞的王子殿下被一個做菜網紅用盤紅燒肉給搞定了…… 粉絲們痛心疾首:“不信不信,王八看綠豆!” 季寧思:“喂,她們說你是王八。” 封人盛:“哼,才沒有和你看對眼呢!” 季寧思:“哦。” 封人盛:“哼,才沒想吃你做的綠豆糕!” 季寧思:“滾。”
17.1萬字8 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