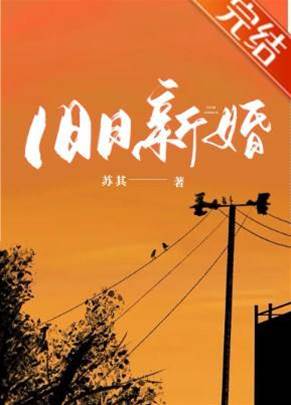《兔子不吃窩邊草,可盛總是狼啊!》 第176章 他差點都瘋了
直到大天亮,這場風雪才停下。
祝鳶是在中午才醒來的。
睜開眼睛,猝不及防對上一雙布滿紅的眼,嚇得一哆嗦,害怕地抬起手遮住眼睛。
這才發現兩只手纏滿了紗布,而且一就疼,渾上下哪兒都疼。
“我就這麼可怕?”男人低沉干啞的嗓音傳來。
祝鳶一怔,恍惚間看見盛聿那張冷峻的臉,眼神復雜地盯著看,那雙深邃的眼睛布滿了紅。
像是一直守在病床邊從未離開。
盛聿看見一副呆愣的樣子,扯了一下角,“凍傻了?”
失去意識前的畫面祝鳶約記得一點。
原來不是幻覺,真的是盛聿找到了。
“你……”盯著盛聿的臉,一開口,嗓子又疼又干,一翻,手不小心撞到床邊疼得直氣。
盛聿皺眉,作輕地抓住的手腕,將抬起的兩只手抓開,“別,你的兩只手凍傷了。”
想到喬邁說再晚點就要截肢,盛聿的眼底閃過一殺意。
祝鳶看著自己被包粽子的手。
原來是凍傷了,難怪這麼疼,應該是皮破了。
了幾口氣,因為嗓子干,的聲音很沙啞,小聲說:“我想喝點水。”
那個高高在上的男人盯著看了一會兒。
祝鳶不知道為什麼,醒來后覺盛聿看的眼神怪怪的。
氣氛也怪怪的。
說不出的曖昧繾綣。
沒等多想,盛聿起到病房的另一邊倒了一杯溫開水過來。
祝鳶這才看到他那雙大長,穿著一雙登山靴。
靴子了,但應該時間有點長沒有往下滴水,只是那深一看就是了。
這麼長時間,他居然連鞋子都沒換。
盛聿拿著水杯走過來,坐在邊,要將扶起來靠著他口,誰知他剛一祝鳶,祝鳶就疼得直氣。
Advertisement
男人繃著下頜線。
看到他生氣了,祝鳶連忙說:“僵太久,所以很酸痛。”
盛聿拿著杯子的手一僵,破天荒地解釋:“我沒生氣。”
祝鳶的心跳的有點快,不由自主想起他在化妝間抱著,對說“對不起”的畫面。
氣氛悄然變化,又是那種說不出來的曖昧,祝鳶眼神飄忽,“有吸管嗎?我用吸管喝吧。”
不指盛聿這個高高在上的盛家太子爺會照顧人。
當盛聿拿來吸管,像哄傻子一樣地說:“進去,再拿到我邊。”
男人這會兒臉沉下來,是真生氣了,“我不懂得嗎?”
他將吸管的一端放在祝鳶的邊,看著喝完水之后嘆了一口氣,聲線低下來,“舒服了嗎?”
宋瓷剛推開病房門就聽見里面傳來祝鳶和盛聿的對話,什麼“進去”“舒服了嗎”聽得面紅耳赤。
齊競和原風野清了清嗓子。
這才驚病房里的人。
“我們待會兒再進去。”齊競對宋瓷說,“比起我們,應該更需要你。”
盛聿看見他們,卻沒有要走的意思。
但現在祝鳶很想上洗手間,雖然和盛聿“那麼”了,但這個樣子肯定連子都不會,要當著盛聿的面上洗手間,做不到。
好聲好氣地說:“你的鞋子都了,去換一雙吧,別冒了。”
因為渾無力,說話的聲音的,的,聽起來比的夾子音還更好聽。
盛聿的眼神眼可見地下來,他面無表地嗯了聲,轉出去。
病房門關上。
祝鳶趕朝宋瓷求救,“尿急!”
宋瓷將攙扶起來,看著疼得齜牙咧的樣子,解釋說:“原本護士要給你尿管的,我沒讓。”
Advertisement
祝鳶疼得面目猙獰,“你做得對,尿管旁邊再放個尿袋,太丟臉了。”
“包袱這麼重?”宋瓷揶揄。
祝鳶一副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的表。
坐在馬桶上,宋瓷雙手抱靠著洗手臺,“剛才在門口我聽你說什麼“進來”還以為你這麼急不可耐,還沒恢復,就在病房干起來了。”
祝鳶一時沒反應過來,等意識到宋瓷在說什麼,無語翻了個白眼,“你真是前途一片輝“黃”,我是讓盛聿吸管,我想喝水。”
宋瓷似笑非笑地哦了聲。
忽然說了一句:“你昏迷的時候跟盛聿表白了,他差點都瘋了,你知道嗎?”
祝鳶腦子里嗡的一下。
上廁所到一半,生生憋回去。
臉漲紅,聲音磕磕:“你說什麼?”
宋瓷挑眉,一副你沒聽錯的表。
祝鳶的臉火燒火燎的,就說怎麼醒來之后盛聿看的眼神怪怪的。
不過也沒什麼,喜歡就是喜歡了。
不知道是哪個時刻,盛聿悄然刻進心里。
也許是除夕夜廣場上的遇見,他戴著狐貍面,在新年鐘聲敲響的瞬間低頭吻。
也許是差點以為要被董家的人害死,在和裴凌逃亡的路上,在郊外,他擁抱住。
也許是更早以前……
等意識到那個男人在心里有多重要,徹底慌了。
可昨晚當猜測那些人是想抓了威脅盛聿的時候,卻義無反顧選擇逃進雪山里,不給任何人牽制盛聿的機會。
宋瓷給穿好子,攙扶著回病床休息,“臉紅這個樣子,還強裝淡定。”
祝鳶忽然停下腳步,“等等。”
“怎麼了?又想拉?”宋瓷問。
祝鳶嘖了聲,被宋瓷攙扶著緩緩轉過,難以置信地看著衛生間的鏡子。
Advertisement
當看清脖子上的那張臉,表木然地看著宋瓷,啞然道:“不是,我的臉這樣了,你沒告訴我?”
又紅又腫,因為凍傷起了水皰,涂了藥,一張臉紅的青的黃的三種拼接在一起,跟一塊調盤似的。
所以剛才就是頂著這張臉面對盛聿的?
宋瓷一副理所當然的口吻:“我以為你知道。”
祝鳶:“……地球毀滅吧。”
兩分鐘后,宋瓷打開病房門。
換了服和鞋子的盛聿握住門把就要進去,宋瓷攔了他一下,“現在不想見人,尤其是你,盛總。”
“為什麼?”盛聿沉聲。
宋瓷嘆了口氣,“嫌自己丑。”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82 章

退無可退:霍少我嫁求放過
他是霍氏集團的總裁,身價上千億,從不近女色,一場意外,他和她發生了關係,從此食髓知味,念念不忘。 霍司銘霸道強勢,步步緊逼。 陸暖一退再退,逼得無路可退,終於忍不住抓狂了,「霍司銘! 你到底要怎樣才能放過我?」 霍司銘勾唇一笑,「當我的霍太太,我就放過你……」
105.7萬字8 274524 -
完結923 章

渣爹做夢都想搶媽咪
三年婚姻如同枷鎖,楊千語終于脫離牢籠,卻不想懷上了三胞胎。不得已將早產病危的女兒留給前夫,她帶著倆兒子遠走高飛。數年后,她潛回國本想偷偷看看女兒,卻被前夫發現驚天秘密!“楊千語,這倆熊孩子你怎麼解釋?”“你的種,難道不該問你?”男人咬牙切齒,作勢要搶走兒子。楊千語一把攔住,“封墨言,你忘了當初怎麼虐我的?你憑什麼搶我兒子?”男人盯著她冷笑,繼而彎腰將她一把扛起:“老子不搶兒子,搶你!”
221.1萬字8 116868 -
完結134 章

我與玫瑰,隨時為公主待命!
【1v1甜寵蘇撩、寵溺無底線】刑偵支隊隊長周燼,桀驁不羈,野性十足,平素最討厭被人糾纏,也最沒耐心哄人。某次任務結束後,卻破天荒的收留了一個小姑娘到家裏。隔天隊裏都在傳,小姑娘會不會被周爺給兇哭?哭倒是真哭了。不過是那個女孩紅著眼把他們隊長給逼到牆角,語氣委屈,“不追幹嘛要招惹我?”說完,便氣的直接踮起腳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外人眼裏的周燼是熱烈的酒,是燎原的焰,但再野也是裙下臣。許久後的某天,事情真相浮出水麵。沈黎霧把自己鎖在昏暗的房間內,直到身邊傳來了熟悉的氣息,她怔怔抬起頭,眸中染上了層水光。沈黎霧身形微顫,語氣哽咽著說,“周燼,我沒有家了……”周燼眼眶泛紅,將她抱在懷裏,輕吻了下她的額頭,啞聲道:“我給霧霧一個家。”**——大霧四起,我們在無人之處愛你。——我不信神佛,不信童話,隻信周燼。**閱讀指南:短篇小甜餅,治愈救贖向,感情線為主,男女主結局He。親情線有意難平,番外會彌補遺憾。劇情線相關內容請勿較真考究噢,謝謝閱讀^^
26.6萬字8 13146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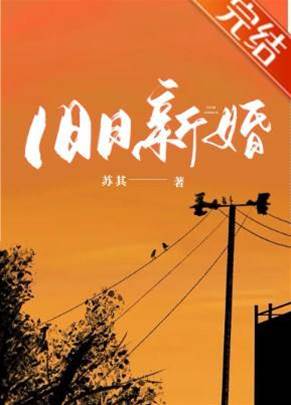
限定婚約/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943 -
完結123 章

偏吻荊棘
段西珩17歲時,曾在阮家借住。 阮蘇茉見他的第一眼,少女心思便如野草瘋長。 可惜少年寄人籬下,清冷寡言,不大愛理人。 阮蘇茉總鬧他,欺負他,來惹他注意,像鞋帶散了這樣的小事,都要喊他。 而每每這種時候,身着校服高挺如松柏的少年,總會一言不發,彎身蹲下,替嬌縱的女孩系上鞋帶。 他很聽話,卻好像不怎麽喜歡她。 阮蘇茉的暗戀随着段西珩畢業出國戛然而止。 沒想到幾年後再見,是被長輩安排結婚。 少年已經長大成人,西服熨帖,斯文清貴。面對她時,仍如從前般沉默。 婚後,阮蘇茉與段西珩的關系屬于白天冷淡偶爾夜晚熱烈,感情一直不溫不火,直到她高中沒送出去的情書被段西珩看到。 阮蘇茉本以為他會奚落嘲笑自己一番,高高在上的她也曾有過卑微的暗戀。 卻沒想到,他只是沉默地将沒拆開的信封還給她,什麽都沒說。 而那個夜晚,段西珩第一次埋首在她肩窩,呼吸不定: “幸好他瞎。” 阮蘇茉:? 你為什麽罵自己?
17.6萬字8.18 53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