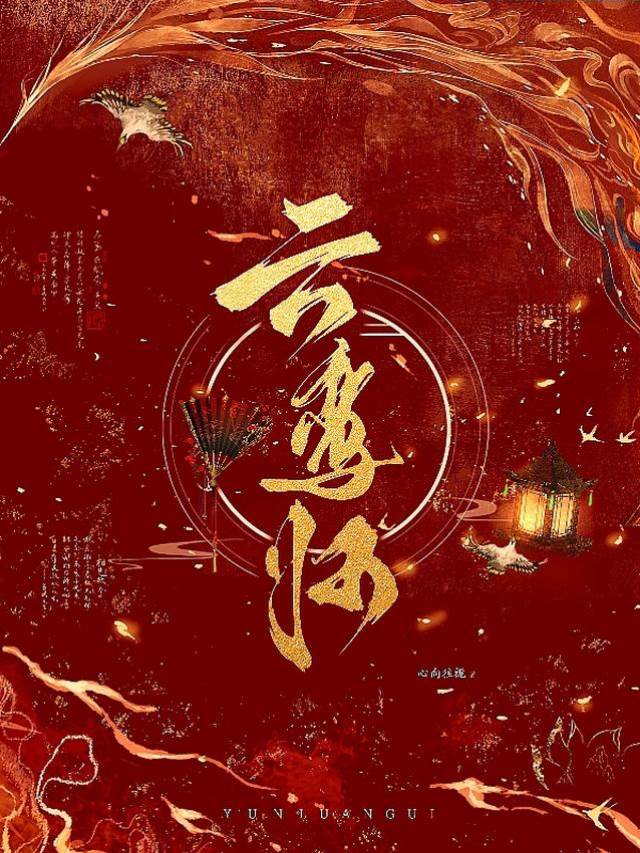《不辭春山》 謀娶
謀娶
祁老將軍披星戴月,一路疾馳趕回瑕城,手上的馬鞭還沒來得及放下,就看到了眼前這一幕。
礙于衛蓁還在,他只得轉過去。
祁老將軍冷聲道:“今日我回來,是有急事與你商議,卻沒想到撞見這一出。”
祁宴道:“父親,我與方才在談事。”
祁老將軍回,擡起馬鞭道:“你當我蠢還是當我傻,你都跑人家兒家床上了,還說談事?”
他一回府上,就來找祁宴,卻從仆從口中得知,將軍在那和親的公主的屋裏。
外面就一個仆從看風,夜已過三更,那屋裏頭不燃蠟燭,一團漆黑,孤男寡共一室,能做些什麽?
所以他也是害怕事態糟糕,才會不等仆從敲門,就敲門而。
“祁宴,你先出來,我有話與你細說。”
老將軍話語充斥著寒意,不想驚府上其他人,先退了出去。
他大步流星往外走去,殿外燭傾瀉進來,將屋照得燈火通明。
衛蓁在祁宴懷中,聽到背後逐漸離去的腳步聲,指尖攥祁宴的袍。
剛剛祁老將軍闖進來,衛蓁下意識要往床裏鑽,那一刻真覺得像是被人捉。
如若知道今夜祁老將軍會回來,絕對不會放祁宴進屋。
那老將軍看的眼神,如芒在背,猶如在淩遲一般。
“衛蓁。”頭頂響起他低啞的聲音。
衛蓁在他懷中,睫抖,到他心口劇烈地跳,愧得幾乎擡不起頭來。
離他的懷抱,搶在年開口前搶先道:“今夜之事是我之錯,是我冒犯唐突了,實在是對不住將軍……”
面酡紅,愧地擡不起頭來。
祁宴傾道:“衛蓁。”
他拉靠近,掌心在衛蓁腕骨一側引起灼燒之。
衛蓁側過臉,避開他的視線:“大將軍還在外面等著你,你先出去與他說話。”
Advertisement
殿外仆從也來催促:“主,大將軍喚您。”
衛蓁道:“將軍先讓我一個人靜一會可以嗎?”
祁宴一定,隨即搭在手腕上的手慢慢下,道:“好。”
腳步聲離去,關門聲響起,衛蓁抱膝坐在昏暗,將臉頰埋在膝蓋之間。
回想方才發生的一切,都猶如在夢中一般。像是被下了蠱一般,整個人不屬于自己,不控制地與他靠近。
剛剛為何會吻他?是第一次遇上對如此好的郎君,激湧上心頭;是口覺酸酸漲漲,出于本能地想要與他湊得近一些,更近一點……
衛蓁的指尖輕輕覆上了紅,與他親吻時那麻浮上心頭,指尖如過電般發。
兒家生敏,心腸,心中有一條涓涓的溪流,如今泛濫災。
從未與男子這般親過,今夜的經歷讓仿徨且不安,且難堪。
床幔上掛著的那顆夜明珠,發出瑩潤和的亮,隨著清風搖曳。
衛蓁眼前浮起了他離去時的樣子。年面容清俊,臉頰微紅,若著一層胭脂,更襯得其人如玉。
那麽他呢,對今夜之事是何想,眼下又是何心?
衛蓁不知道,郎在黑夜中輾轉反側,一顆心躁難安。
祁宴被喚了出去,走進隔壁屋子。
窗戶敞開,江面上晚風呼呼灌,吹得燈架上蠟燭搖曳。
祁老將軍祁徹,背手立在窗邊,高大的背影猶如一座沉默的山。
聽到腳步聲,祁徹開口道:“終于舍得出來了?”
祁宴道:“父親深夜前來,是有何事?”
祁徹轉過來,燭火映照出一張冷峻且棱角分明的面龐。掌管楚國邊境二十萬軍馬的大將軍,歲月沉澱之下,是一如淵的氣場,穩如泰山,往那裏一站,便是不怒自威。
Advertisement
祁徹冷眼看著他:“我若今夜不回府上,怕還發現不了你做了何好事。”
祁宴走到桌邊,給自己倒了一盞茶,倒也不急著回答。
祁徹道:“軍營之中都傳開了,道是祁家主昨日在酒樓之中一擲千金,只為換一顆夜明珠,我原想不通你為何這般,直到剛剛在那郎的帳子中看見那顆珠子,你將它送給了?”
祁宴懶倦地坐著,挑眉道:“父親不是都看到了,還來問兒子?”
這般漫不經心的態度,令祁徹冷笑連連。
祁宴給祁徹也倒了杯熱茶,問道:“父親深夜回來,是有何要事與我商量?”
“莫要岔開話。”祁徹打斷道,“祁宴,我不信你不清楚,是何份,你是何份。你既護送和親公主北上,又與公主如此糾纏不清,這究竟意味著什麽,你當真不知?”
祁宴擡起濃長的睫,與他對視。
他的容貌十十繼承了姬琴公主,尤其那雙眼睛,連眼尾的弧度都如出一轍。
祁徹凝他的眸子,半晌道:“阿宴,你若執意與糾纏,于你于,都不是好事”
祁徹道:“祁家在楚國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那日離宮事發之後,我與太後商議,讓你晉國去見晉王,唯有投奔晉王,祁家方能有一線活路。”
“祁宴,你不是半大孩,不至于不明白這個道理,你不能只考慮你自己,還應當考慮整個祁家。”
這一回,年終于慢慢收起了臉上懶倦的神,“孩兒知曉的,孩兒一日都不曾忘過。”
“若你與和親公主的事傳到晉王耳中,晉王會如何看你?晉王本就對你不喜……”
“晉王喜不喜歡我是一回事,”年擡起頭打斷道,“而我于他有沒有用,那又是另一回事。”
Advertisement
“他最不缺的便是王孫,我若只當他的外孫,和其他孩子并無區別。但我知道他想要什麽,他想要一把能劍指中原的寶劍,想要除去列國,為天下真正的主人,而我可以幫他完。”
黑暗之中,祁宴眸子明亮灼然,仿佛有烈焰從其中升起。
晚風將蠟燭吹得搖晃,連帶著牆壁上的影子也隨之搖。
“外祖他已經很老了。”祁宴輕聲道。
越是年老之人,越是雄心壯志之人,越是想在最後的歲月,抓住一切機會,實現沒能完的夙願。
而他祁宴,可以為晉王最鋒利一把劍。
他面平靜,聲音鏗然,骨子裏帶著一種偏執的執拗。
“我會在晉國走出一條我自己的路。”
祁徹看著他的雙目,這一刻,他又想到了姬琴。
那一夜,從晉宮之中義無反顧地奔出,登上他的馬,眼中也是這樣人覺得滾燙的眼神。
心中直覺告訴他,晉王會喜歡這個孩子。
祁徹回過神來:“你外祖能爭霸天下,手下不缺能領兵打仗的將士,他厭恨一切踩著他底線做事之人,所以不管你何時與和親公主有了首尾,你最好在到達晉國前,與斷得幹幹淨淨。”
“祁宴,你與本沒有未來可言。”
夏雷一震,電劃破烏雲布的天際。
冷風將這句話吹散開,桌案上竹簡嘩嘩作響。
祁宴不出一聲,靜靜著他。
祁徹手上祁宴的肩膀:“你向來懂事明事理,這一次,父親也相信你能做出正確的決斷。”
祁徹往門邊走去,在要推門離開時,聽到了後人靜靜的一句:“我會的。”
他定住,回首看到年坐于燈下,形清瘦而幽寂。
他不知祁宴心中是何想,但年之人要與過往做個了斷,必然是萬分苦的。
Advertisement
祁徹收回目,離開了屋子。
祁宴在寂靜中久坐,修長指尖有一搭沒一搭敲著桌案,叩出清脆之聲。
幢幢燈影,照著他俊的面龐。他另一只手捧著下,瞇了瞇眼,看向濃雲翻滾的天邊。
父親的話提醒了他。
衛蓁份不一般,畢竟是晉楚兩國的公主,背後牽扯的利益衆多。
這些日子來,他與每每相,幾乎都在逾矩的邊緣。
起初他想要躲離,可事實證明,他本躲不了,反而忍不住想與靠近。
若是他當斷不斷,不清不楚地與糾纏,與玩弄無異。
他得做一個決斷,決定好了便不能更改。
他想,以衛蓁這般姿,哪怕不是和親公主,晉國後,也必定不會籍籍無名,引起那些王孫公室為其相爭。
而與晉國公室和親,到時候自然是,王室中誰最得晉王歡心,便能求娶到。
晉王膝下一共十七個孫子,除去已經娶妻的,剩下適齡的便有十人,更不論外孫又或是侄孫。
若過去,最可能嫁的便是七殿下姬淵,聽聞他與魏國公主的婚期已到,卻遲遲未履行婚約,晉王若為拂魏國的臉面,直接將衛蓁嫁給他,也不是不可能。
剩下的一衆兒郎,不乏能人之輩,這麽多男子在,他若想要謀娶到……
似乎頗為棘手啊。
他確實得好好地想一想,謀劃一番,想出一個萬無一失的辦法,將求娶到手。
兩側高高的書架,投下濃重的影子,落在殿中年的上。年指尖依舊輕敲桌面。
一夜暴雨敲窗。
次日一早,風雨漸停,卻是個晴朗的好天氣。
衛蓁起後梳妝,著銅鏡中的自己。
面玉白,瓣如櫻,因清晨才用過一盞茶,雙顯出潤亮的澤。
看著自己的瓣,昨夜發生種種,便從腦海中閃過。
實在不知該怎麽面對祁宴,索打算一整日都不出屋去。
午後時分,侍來給衛蓁傳話,道衛侯與楚太子城了。
衛蓁聽罷更,準備出門迎接。
換了一淡青的羅,佩戴好首飾玉佩,回頭看到帳上掛著的那串夜明珠玉墜,猶豫了一刻,還是走到床邊,解下繩子,將其系到了上。
出了門,到了府邸門口,不可避免遇上祁宴。
四目相對,側過子。
片刻之後,又覺自己這一舉太過生,簡直將有意躲他寫在了臉上。
也是此時,護衛隊到了。
衛淩在士兵的護送下城,後還跟著幾匹寶馬,上頭坐著正是姬沃與晉國的使臣。
衛淩翻下馬,走到階前,將衛蓁深深摟住:“阿姊。”
他松開:“阿姊放心,我無事,只了一點小傷。那夜遇到水匪後,我便立馬棄了船,躲在岸邊林中,不多時就等到了祁家的援兵。”
姬沃與使臣也拱手,表示自己并無大礙。
衛淩嘆息道:“水匪劫了主船後,上船燒殺搶奪,姬沃殿下與使臣躲在甲板下面,并未被水匪發現,至于太子殿下,倒是了不小的傷……”
衛蓁這才注意到,他們後的隊伍裏還有一輛馬車。
那裏頭坐著何人,也不用猜了。
衛淩松開,看向一旁的祁宴,上前擁住他道:“這幾日辛苦你照顧我阿姊了。”
祁宴勾笑道:“應該的。”
衛淩道:“我們說。”
衆人進屋商議,送親的隊伍因為遇上水匪,計劃被全盤打,那夜遇襲的結果慘烈,祁家士兵趕去時,送親的船隊已損失大半,士兵也折損了不。
而送親的行程因此耽擱,招惹晉國不滿,太子回去必然要被楚王問責的。
而人決定在瑕城停留一段時間,養傷的養傷,修整的修整,待隊伍整齊後,再重新啓程。
這期間,衛蓁與祁宴基本上沒見過面。
一則是因為自那夜之後,祁老將軍便日日宿在公主府,未曾離開過,二則是,祁宴忙著集結軍隊,有在府上的時間。
到了啓程那日,出了一道消息,衛蓁震驚不已。
祁老將軍說,要隨軍一同護送。
衛蓁不免多想,老將軍是不是怕與祁宴在路上往過,才決定一同北上?
車廂搖晃間,衛蓁過竹簾,約看見外頭晃的人影。
衛蓁對涼蟬道:“快到午後了,你等會去阿弟上車來歇息,他上還有傷。”
涼蟬恭敬道:“喏。”
衛蓁手無意間輕腰間的夜明珠串。
涼蟬垂眸于珠串,前幾日在公主上發覺多了此,一直沒有多問,直到今日,看公主上路後還在不停輕它,才生出好奇之心。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64 章
在女尊做大佬妻主
蘇靈喬重生了,回到了自己剛開始為一個男人死心塌地付出時。前世一根筋,最後隻落得個至親慘死、不得好死的下場。再來一遭,仇要報,但男人什麼是不存在的。隻不過……有人黑了臉。「妻主莫不是忘了,一日為妻主終身為妻主?」蘇靈喬隻好一臉認真勸退,「我欺師滅祖、大逆不道……」「為師讓你欺讓你滅。」蘇靈喬:……
81.6萬字8 14765 -
完結536 章
王爺,娘娘又有喜了!
童婉這一世決定當一個貨真價實的廢柴。哪裡有靈寶?不去不去。哪裡有神獸?不抓不抓。什麼千百年難得一見的神器現世?快躲快躲,神器要倒貼上來了。她堅持把廢柴進行到底,冇想到卻被自家一對腹黑娃娃給出賣了。“爹爹,一條七星五毒蛇,孃親就是你的了。”“爹爹,乖乖要七彩羽翼哦。不給就不告訴你孃親在哪裡呀。”兩個粉雕玉琢的奶娃娃賣親孃賣的毫無壓力,某王爺一手一個拎起來,全部打屁股。“賣我媳婦兒?找打!”
91.8萬字8 63712 -
完結520 章
重生后我養了五個權臣
秦灼死在了出嫁的那一天。她跟晏傾退過婚,插過刀,動過劍,相愛相殺十幾年,最后穿上嫁衣死在了他家大門前。重生后秦灼決定再也不跟姓晏的糾纏了,談情傷命,有那閑工夫不如搞事業!她要做第一女侯,權傾朝野!從此她一路打臉虐渣走上巔峰,卻發現自己是是流落在外的長公主。皇帝渣爹多年前為了坐穩龍椅殺妻棄女,現在要殺她掩蓋真相。她絕地反殺,既然渣爹為了天下要殺她,她就奪了這天下!假皇子對她極盡溫柔“阿灼想做的事,我都會幫你做到。”紈绔闊少往她身上拼命砸錢“不就是錢嗎?盡管拿去花!”毒舌神醫幾次三番救她性命“都說救命之恩當以身相許,你自己算算,該許我幾輩子?”忠犬型少年將軍傾心守護她“姐姐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前未婚夫跪下,哭著求原諒“心給你,命也給你!只求你回頭再看我一眼!”
138.8萬字8 18191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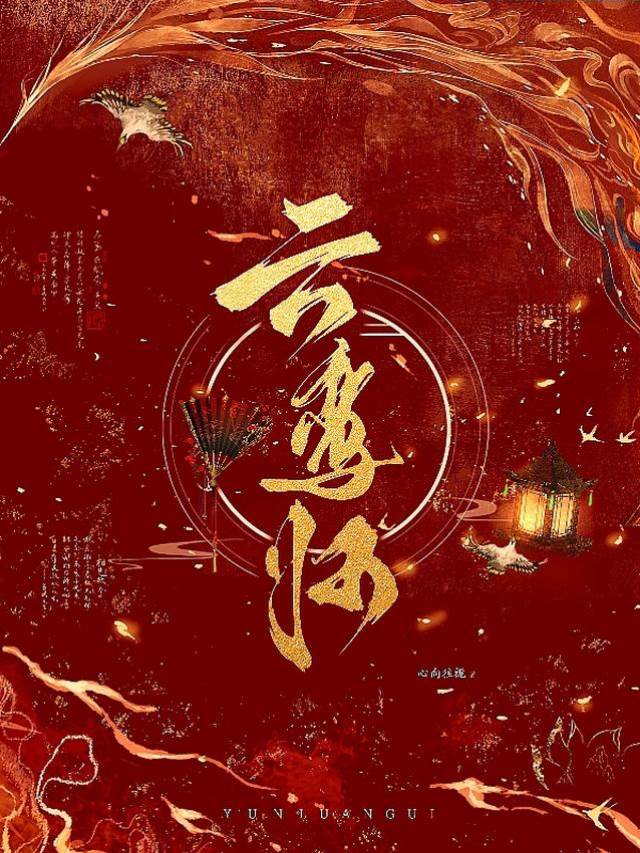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