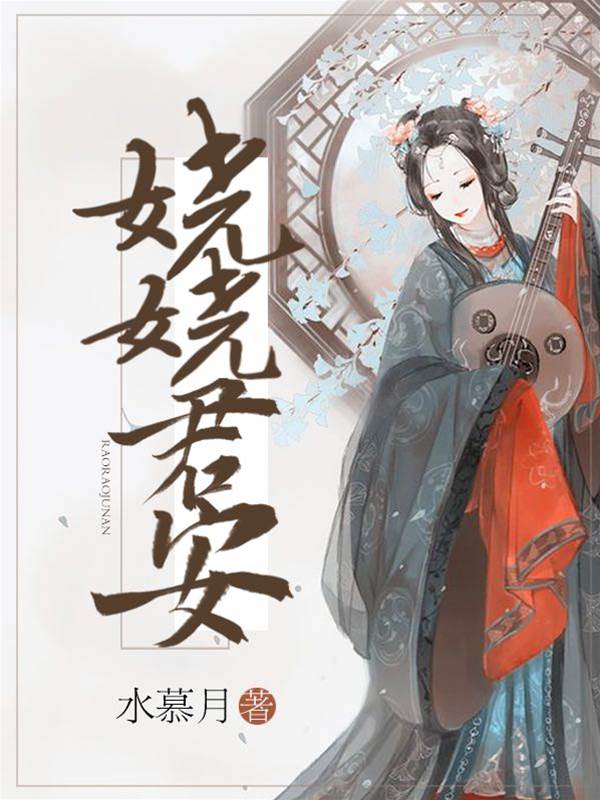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被渣后和前夫破鏡重圓了》 第 57 章
第 57 章
陸嶼然的霎時有些僵。
從前有段時間, 溫禾安在半睡半醒,不太想管事的時候,也會有這樣無意識的態, 但和現在還是不太一樣, 現在更親昵一點。
一種人心尖發發甜,無從拒絕的親昵。
面對那雙眼睛,陸嶼然頓了頓,眼睫低垂,隨後微蹲下, 先將滿捧沁著梔子香的氅攏起來,攏在掌心中, 堆在的椅邊,又將這人系得松的系帶收, 將的肩骨和中都嚴遮住。
“嗯?”他聲音有點天生的清, 稍低:“回去睡?”
兩人離得近,溫禾安定定看了看他, 腦袋一偏, 下頜歪在他的肩頭上,跟前驟然凝住的軀和放緩的呼吸, 擡眼與後目瞪口呆的商淮對視,順著他的節奏,也眨了眨眼, 好似在問他怎麽了。
再給商淮活上一百年,他想破腦袋,也想不到這兩位在外手段雷霆, 人聞風喪膽的主談起來,會是這樣的畫面。
看看陸嶼然這彎腰, 低聲的作,儼然不是一次兩次了。
商淮不由默默合攏了。
這可真是萬萬沒想到。
陸嶼然半擁著沒骨頭一樣要懶懶尋個支撐的人,覺的氣息親地在自己頸後,發披散,落在他的肩與手背上,質像順的綢緞。
他的懷裏,面頰上,耳邊和裳上因此沾惹上無邊際的花木香,像攏著一捧才摘下的新花枝。
他為此低頭,覺手背上的青筋中恍如注另一種不控的跳,從來清冷的人不住虛虛握了握掌,好半晌,冰涼手指緩緩了的發,結微:“……先去樓上?”
溫禾安不說話,他將這人的臉頰撈出來一看,發現杏眼含笑,兩腮微熱,著一點懶懶的勁,沒吭聲,也不拒絕,又是那種,好像都可以聽他的,天真爛漫至極,半懂不懂的樣子。
Advertisement
實際上,就是壞心眼。
之前就是非要他先將話說得明白,將妥協列得清楚,就是要他先來找,先彎腰,先哄人,看似他掌控了所有的主權,實則占盡上風,眉眼彎彎的無辜,看他在給出的親近中無措,看他迷失。
然而他確實,拒絕不了。
陸嶼然忍耐地吸了口氣,回頭看若有所思看戲還假裝無事的商淮,神又凜又寒,商淮頓時撇撇,不不願地轉進廚房,心中憤懣:裝什麽,剛才對溫禾安你可不是這樣的!
陸嶼然牽著溫禾安的手腕,亦步亦趨地起,一階階踩著樓梯,直到關上房門,被他倏的半抵在壁櫃上,清冷的氣息近。
他過幾近燃盡的燭,去看的眼睛,發現是真困,漂亮眼睛裏還藏著不住的。
他靜了靜,聲稍啞:“真困?”
溫禾安輕輕地嗯,嘆息,低聲說:“我明日還要去一趟徐家看看,那邊大概出事了。”
徐遠思的求救都懟到臉上了。
跟相關,他可能會是個關鍵的突破口,確實要去一趟。
陸嶼然閉了下眼,睜開眼時,中指指節無可忍耐地挑開的面,了角,以為能稍稍遏制心中湧的念,卻不想仍被那種驚人的度得難以自抑。
他自己跟自己較勁,半晌,倏的手抵著的臉頰,黑長睫低垂,帶著冰霜般氣息落下來。
很輕,又涼,沒有更近一步,力道起先輕,後變重,像上落下了一片雪花,他的氣息偏又無比灼熱。
溫禾安呼吸微滯住。
一即離,陸嶼然有些狼狽地撇了下視線,指了指裏邊的床榻,說:“去睡吧。”
他手了左臉上的裂隙,眼中稍減:“……明天讓羅青山看看。”
Advertisement
溫禾安點了點頭,怔了會,在他的視線下,用指尖了才被他親過的瓣,又擡頭去看他,眼裏有點懵,又有點不知死活的縱容神采,陸嶼然看得瞳微深,指骨輕攏。
只得告訴自己,
還在毒發期。
溫禾安開純的帳子,往裏一躺,半趴著,看他,每次到他帶點警告的眼神,就若無其事地轉頭去看別的地方,隔一會,視線又落在他上。
跟妖骸打道,向來死守原則的一個人,卻能容忍臉上這個東西,這讓覺自己待在他邊,跟待在沒有邊際的空間裏一樣,不會有壁的時候,放肆舒服得沒有限度。
再看看他,看他滿清冷散去,沾上一些七八糟的難耐,再一想他竟完全偏向,完全屬于,又覺得很是新奇,很是……喜歡。
溫禾安睡著了。
陸嶼然在書案前靜了靜,又捧著卷書靠在書櫃後看了會,等回到自己榻上的時候,發現珠簾上,帳子上,還有枕頭上,床褥上,初雪的氣息被毫不講理地住了,取而代之的是春天的花枝,一種看似溫,實則尤其張揚的生命力。
他盯著看了會,覺得還跟以前一樣霸道。
陸嶼然轉去湢室洗漱,出來時用手輕推了推,垂著睫,也不知出于一種怎樣的心理,說了句:“過去一點。”
隔了一會,溫禾安卷著大半邊被子滾到了裏側,留給他一道纖薄後背,他執著被角躺下去,等了很久,也沒有等到從前下意識養的蜷過來的作。
這無疑在闡述一道事實。
他們終于又在一起,但也確確實實,隔了一段不短的時間。
有那麽一霎,陸嶼然不知心中是怎樣的滋味。
他最終靠過去,將人勾過來,起先很不樂意,不滿地掙了掙,但他這時候出乎意料的強,連氣息都不聲放出來了,抵著背脊不清不重地安,半晌,溫禾安被這種完全合的熨帖勾得舒服了,懶得了,臉頰都出嫣紅。
Advertisement
陸嶼然闔了闔眼,覺心中被尖牙狠狠咬過的小終于有止的征兆。
==
子夜時分,隨著樓下小院的廚房裏炸開一道不大不小的靜,淩枝著自己的角,被嗆得咳了一聲,又手抹了抹臉上的灰,迎著風和商淮對視了好幾眼,最終還是如願了。
只用了半個時辰不到的時間,商淮就將烤好的熱乎的餅幹用牛皮紙包著,又很講究地墊著一層手帕遞給。
轉頭一看,這小姑娘蹲在院外的小樹下,手裏拽著青草,左晃晃右晃晃,他沒辦法,沉沉嘆了口氣,覺得自己真的作孽,又轉到水井邊把帕子浸了給手。
吃東西的作優雅,但速度不慢,一邊問商淮:“溫禾安呢?”
商淮了鼻子,點了點樓上,就差翻個白眼:“樓上呢,估計是不會下來吃餅幹了,我勸你也別喊,免得被人記恨上。”“我才不喊。”淩枝朝那邊掃了掃,又了塊餅幹咬得清脆發響,難得還能把話說得字正腔圓:“怎麽這麽快?”
拍了拍手,一會後,又點點頭,瞇起眼睛,自顧自地道:“不過也還好,畢竟是陸嶼然,帶勁,上了不虧。不虧就行。”
商淮被這樣石破天驚的一句話說得愣住,不管再看幾遍,他都想象不到淩枝怎麽能頂著這麽張稚的臉龐說出如此生猛不避諱的話,他咳了咳,尤其不明白為什麽這樣的格能在淩枝的手下做事。
淩枝又咬住一塊餅幹,納悶地道:“我都耗幾年了,怎麽就沒這樣的速度。”
商淮原本想問家主的事,聽到這話,想了想,還是順著問了句:“你耗什麽?”
淩枝與他對視,沒所謂地道:“我師兄啊。”
商淮現在本聽不得師兄二字,一聽,他就忍不住了角,俊俏的臉上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你也有師兄?家所有子難不都有個師兄?”
Advertisement
“那也沒有。”
淩枝慢吞吞地說,齒間都是漫開一種香氣,扭頭看他,有點眼的:“我明天還有點心嘛。”
商淮想說他真的很忙,沒有時間,在陸嶼然手下做事真的不容易,然話才開了個頭,就見淩枝出手指,攏著那袋餅幹,說:“我知道家主的事,很多事,你想知道什麽,我都告訴你。”
商淮將話咽下去,認命地道:“……我盡量。”
==
翌日一早,溫禾安醒來的時候,發現床榻上已經空了,難得有點懵,抓起四方鏡一看,發現陸嶼然發了兩條消息,昨晚也有,不過那會睡著了沒看到。
他問了月流,知道今天沒有下無歸的計劃,但巫山這邊還得再去。
後面跟著句,說他今晚會回來,讓羅青山看看臉上的東西。
知道會擔憂什麽,最後那條消息只有兩個字。
【放心。】
溫禾安回他:【好。我戌時回。】
出門時天氣還不錯,萬裏無雲,空間裂隙直接傳送到徐家,徐家說遠不遠,說近不近,是來回的路程就需要兩個多時辰,而就在踏進裂隙之時,蘿州的天氣就變了。
昨日無歸上整那一出,三條口都被妖群堵住,所有人無功而返,頂多被溫禾安震懾了一遭,又看了一出關于王庭的戲,就都被不管不顧地送上來了。經過一夜的休整,大家都鉚足了勁,想要在無歸發現些什麽。
三大家也不例外。
然而還沒下溺海,最先察覺到不對的也是這三家。
在溺海邊上建起的那三座觀測臺,觀測了幾日沒看到除了海草之外的別的東西,今日人才下去,隔著幾層仙金,卻見到了前所未有,極度駭人的一幕。只見海下五六米,海水狂卷,已經不複之前幽藍的澤,而是和海面一樣純正的漆黑,像傾倒進了天底下所有的墨。
墨下,是躁的妖群,數量極其多,多到視線中好像都快要裝不下那些東西。甚至沒人能分得清那些東西,只知道是手,腳,骸骨,水草,狐貍尾和豹子頭,世間無數種東西沒有秩序的胡湊合。
它們昨日還知道齊心協力一起對付外人,今日就變了樣子,徹底沒了心智,大的吞噬小的,模樣再次發生轉變,又漸漸朝海面上湧,往上浮。
這片海,出了真正吃人的模樣。
負責看管觀測臺的執事們頭皮發麻,瞠目結舌,短短幾息後,他們猛地回神,匆匆一拂手,道:“快,去通知主。”
頃刻之間,蘿州烏雲城,一聲炸響之後,暴雨傾盆。
們察覺到了不對,但別的家族沒有觀測臺,雨簾一落,海面一,對底下的況一無所知,不人都站在溺海邊上,等著說那聲好,他們就開始往下跳。
淩枝半夜沒睡,原本在補覺,猛然間被那種悉至極,煩厭至極的力量攪得心頭巨震,直接在床上捂著心髒的位置坐了起來。再一凝神,就到外面完全變了的天,以及不知道為什麽,突然暴起來的溺海。
臉一時難看至極,連外都沒披一件,徑直往外走。
與此同時,家家主的命令傳到每位在蘿州的耳裏:【所屬,三刻之,遠離溺海。】
家主的意志,任何都生不出任何一點抵抗的意思。
他們開始後退。
許多家族不明所以,但看三家有負責人到了,接著也跟著退了,再看看今日卷得與衆不同的海面和颶風,心頭驚疑不定,自然,懊惱也有,可沒有辦法,不走,自己下溺海,多半只有死路一條。
人群總算散開,然而整個蘿州之,酒樓裏一半的窗子都大開著,大家探頭,又搖頭,想打探消息,發現都不知道準確的消息。
淩枝攜著滿寒氣徑直闖了巫山的酒樓,陸嶼然正在書房中,看著負責觀測臺的執事一邊汗一邊連說帶比劃地形容海裏的,看不出外放的緒,倒是商淮站在一邊,眉心蹙,吊兒郎當的姿態已經完全不見了蹤影。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042 章
農家小少奶
穿越成小村姑?好吧,可以重新活一次。 吃不飽穿不暖?沒事,姐兒帶你們發家致富奔小康。 可是,那個比她大七歲的未婚夫怎麼破?本寶寶才八歲,前不凸後不翹的,爲毛就被看上了? 退婚,他不肯;想用銀子砸他,悲催的發現,她的銀子還沒有他的零頭;想揭秘身份以勢壓他,那曾想他隱藏的身份比她牛叉一百倍!婚沒退成,反被他壓… 本文一V一 求收藏求抱養 已有完結文(親孃不
96.7萬字8 235303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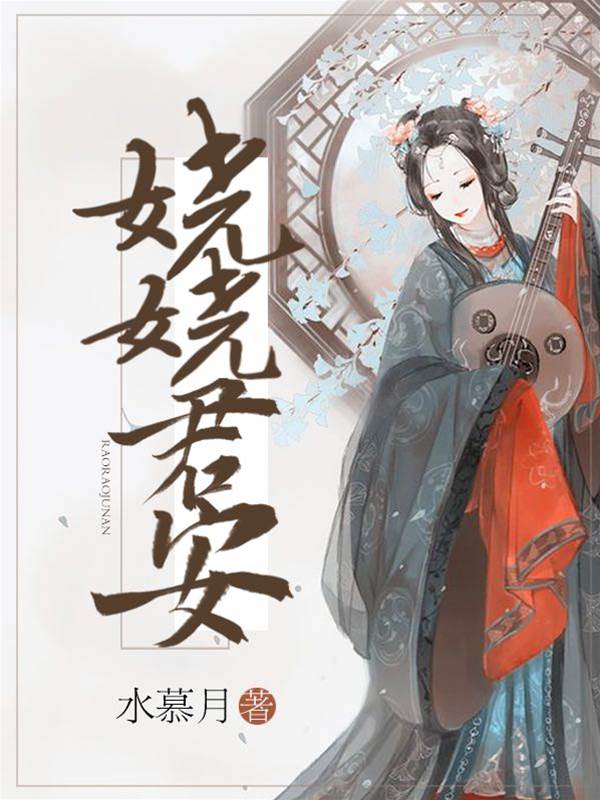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152 章

本王在此/與鳳行
身為魔界銜珠而生的碧蒼王,沈璃的一生是璀璨而奪目的但在她千歲誕辰之際,政治聯姻的魔爪劈頭蓋臉的撓過來九十九重天上的帝君一紙天書頒下著碧蒼王與帝君第三十三孫拂容君定親拂容君早年便因花心而聞名天外她堂堂魔界一霸,一桿銀槍平四海戰八荒,豈能嫁給那種花心草包!這婚必須逃!沈璃不想,這一跑還真碰上了那個不屬于三界五行的男子那男子,當真……奇葩
25.2萬字8 2610 -
完結137 章

乖!嬌嬌別逃!瘋批暴君低啞纏哄
【又名《嬌鳳歸鸞》】【雙重生+雙穿越+病嬌+雙強+團寵+甜寵爽文】 前世慘死穿越去現代后,云梨竟又穿回來了,睜眼便是洞房花燭夜! “阿梨……你為什麼不能試著愛我?” 病嬌攝政王掐著她的腰,眼尾泛紅,發誓這一世也要用命寵他的小嬌嬌! - 世人皆知,暴戾攝政王娶了個草包。 卻沒料到,夜夜在王爺榻上撒嬌耍賴的禍國妖妃,對外卻是明艷驕矜的打臉狂魔! 翻手為醫,覆手為毒…… 不僅前世害她滿門覆滅的人要血債血償,天下英才更是對她甘拜下風! 就連小皇帝也抱緊她的大腿,“嬸嬸如此厲害,不如將那攝政王丟了吧。” 某攝政王:? 他不悅地將小王妃摟入懷,“聽聞我家小阿梨想造反,從此妻為夫綱?” 云梨摟著病嬌夫君的脖頸,“有何不可?畢竟我家夫君的小字比阿梨還要可愛,對吧……容嬌嬌?” - #夫君總把我當小嬌嬌,怎料嬌嬌竟是他自己# - 封面底圖已獲授權:十里長歡-瑞斯、儲秀云心-蟬火。
23.5萬字8.17 113 -
完結107 章

困春鶯
溫幸妤打小就性子呆,脾氣軟。 唯一幸運的,是幼時蒙定國公府的老太君所救,成了貼身婢女。 老太君慈和,經常說:“等幸妤滿十八,就許個好人家。” 溫幸妤乖乖應着,可目光卻不由看向了窗外那道神姿高徹,瑤林玉樹的身影。 那是定國公府的世子爺,京城裏最矜貴多才的郎君,祝無執。 也是她註定靠不近、撈不着的寒潭月影。 —— 溫幸妤出府不久,榮華百年的國公府,一夜傾頹,唯剩祝無執被關押在大牢。 爲報老太君恩情,她千方百計將祝無執救了出來,頂了將死未婚夫的身份。 二人不得不拜堂成親,做了對假夫妻。 她陪他復仇雪恨、位極人臣,成了人人欽羨的攝政王夫人。 可只有溫幸妤自己知道,祝無執一直對她頗爲嫌棄。 她雖委屈,卻也知道假夫妻成不了真,於是放下和離書,遠走高飛。 —— 祝無執自出生起就享受最精細的侍奉,非白玉地不踏,非織金錦不着。 他是目下無塵的世子爺,是孤高自許的貴公子。 直到家族傾頹,被踩入泥塵後,救他的卻是平日裏頗爲嫌棄的呆笨婢女。 爲了掩人耳目,他成了溫幸妤的假夫君。 祝無執看着她掰着指頭算還有幾天口糧,看着她面對欺凌忍氣吞聲,唯唯諾諾。 一副沒出息的模樣。 他嫌棄她粗鄙,嫌棄她呆笨,嫌棄她因爲一捧野花就歡欣雀躍。 後來他做探花,斬奸佞。先帝駕崩後,挾幼帝以令諸侯,成了萬萬人之上的攝政王。 世人都說,他該娶個高門貴女。 可祝無執想,溫幸妤雖呆板無趣,卻勝在乖巧,他願意同她相敬如賓,白頭到老。 可等他收復失地回府,看到的卻是一封和離書。 —— 小劇場: 在外漂泊的第二年,溫幸妤累了,決定在雪城定居。 那夜大雪紛飛,寒風肆虐,她縮在被窩裏怎麼也睡不着。 忽而聽得屋門被人敲響,她恐懼之下提了刀,眼睜睜看着劍尖入縫挑開門閂,門倏地被風吹開。 冷風夾着細雪灌進門內,她用手擋了擋,擡眼看去。 只見那人一身與雪同色的狐裘,提燈立在門外,眉睫結霜,滿目偏執瘋狂。 “敢跑?很好。”
39.7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