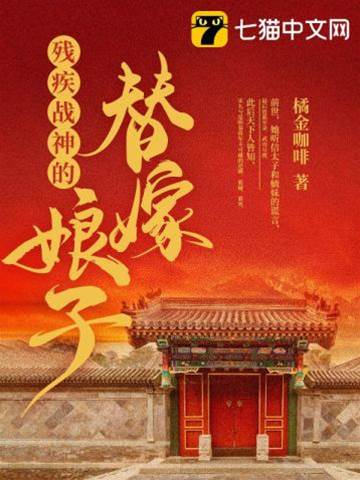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被渣后和前夫破鏡重圓了》 第 2 章
第 2 章
溫禾安來到歸墟多久,有關與天都的傳言便傳了多久。嚴格來說,除了一些極盡誇大離譜的,其餘言論,并不全是空來風。
姓溫,家中排行第二。
而今四極荒廢,九州分裂,部落氏族,宗教門派分布各地,各自為王,黎明疾苦,戰不休。然這些都是小打小鬧,凡提起真正的龐然大,衆人心中皆有數,無非是以溺海縱橫兩線為分割的那三家。
位于溺海東南的北冥巫山,西北的東州王庭,以及東北方的天都溫家。
溫禾安的溫,便是天都溫家的“溫”。
流放歸墟之前,溫禾安也是九州之令人津津樂道的人,出頂級世家,顯赫已極,卻并不是庸庸碌碌,靠家族蔭蔽那類。
大名鼎鼎的“天都雙姝”,便是其中之一。
這不僅只是個名號,相反,溫禾安在溫家手握實權,出事之前,天都外十五城,全都歸管轄。是修為達到第八以上,自願歸麾下的強者,就多達數百。
更遑論,五年前,天都與巫山突然宣布聯姻,溫禾安與巫山“帝嗣”陸嶼然結為道,同時接管天都城近衛司。這無疑將的聲推至巔峰,在名聲與議論度上,甚至一度超過了溫家那位同樣優秀奪目的三姑娘。
可惜,再如何輝煌耀眼,也是從前的事了。
現在的溫禾安,落魄到靠變賣殺手們的家當過生活,大冬天的修為盡失,冷得在一床木板上全打,悲慘得人難以置信。
這是事實。
來到歸墟之後,溫禾安反思過許多次,自己究竟是怎麽將這樣一手牌打得稀碎的。
凡為世家,莫不野心,親總是淡薄,與溫家互相利用,這麽多年,只要不及底線,關系很是穩定。至于被得罪過的仇敵,倒是不,可既然都能得罪,就證明他們沒有那個本事拉下水。
Advertisement
想來想去,還是怨溫禾安自己,養蛇自噬,竟將江召留在了邊。
現在一閉上眼,眼前就會自轉變景,回到一個半月之前的天都。
溫家家主在九境巔峰停留多年,直至九月下旬,終于找到了踏聖人境的契機。
要知道,整個九州的聖人境才有多,掰著手指頭都數得出來,溫家僅有三位,每多一個聖者,都象征著家族實力又更上一層樓,這件事自然為了整個溫家的重中之重,其他事都要為這件事讓步。
為了這個,天都外城悄無聲息開啓了戒嚴狀態,溫禾安和溫三作為溫家最有前程的後輩,負責此次守衛工作。
按理說,外城的勢力攏于溫禾安手中的較多,該是負責外城守衛,嚴守天都,可這次收到的命令是守衛家主閉關所在的通靈塔。
接收這調令的第一時間就意識到,一旦出了什麽事,這責任就是自己的。
且家主是在一片腥風浪雨的氣氛中閉的關。
彼時,天都外不知怎麽突然傳起了將立家主的言論,且局面愈演愈烈,溫禾安起初不以為意,誰知家主閉關前,竟親口對與溫三說,待他出關,便有意退,將封家主,昭告九州,穩固人心。
說溫禾安與溫三皆是家族的棟梁之材,家主之位不論落到誰上,都希們表姐妹之間關系和睦如初,一個務必寬和待下,一個務必勤勉侍上。
他說寬和待下時,看著溫三,說勤勉侍上時,看著溫禾安,其中意思,已經明顯得不能再明顯。
溫禾安倒是沒有憤怒失落,只是覺得奇怪,非常奇怪。
就算再給一個腦子,也不覺得溫家會在這個時候選家主出來。溫家對帝位思之如狂,這麽多年,因為陸嶼然的“帝嗣”之名慪到要死,他們會甘心就這樣定下家主之位,而不是取得帝位之後,將真正的“帝嗣”之名冠到未來接班人上?
Advertisement
話雖如此,溫禾安還是將手邊能推的事都推了,專心負責這件事,可修士閉關,輒三五年,在這期間,不可能全程守在通靈塔,其餘什麽事都撂下不管。
于是在通靈塔下設下個巨大的陣法,調了數十名八境以上強者和三位九境強者日夜守護,但他們只在外圍待命,一旦預備強行進陣法中心,便會被攔下,同時通知。
被予以特權,能真正出陣法,直達通靈塔的人,只有一位。
江召。
可衆所周知,這位王庭質子修為只有七境,難以突破,是一顆擺在明面上被廢棄的棋子,若不是因為與溫禾安的風月之事,世人都不知道還有這麽一個人存在。
而要突破一個即將踏聖人境強者閉關時産生的屏障,并且做到中途打斷,傷害到本人,至得是八境巔峰的修為。
簡而言之,江召沒這個本事。
但事實就是,在法陣沒有任何破損,被強闖的跡象下,通靈塔仍舊出了意外。有人闖了通靈塔,擾了家主閉關的進程,并且險些造實質的傷害,最後關頭被及時趕來的溫三出手制止了。
稽的是,人沒捉到。
等溫禾安回到天都,只有在堂下審的份。
森嚴的古殿中,有人高聲喊早有預謀,只因家主定下了溫三主溫流為家主,心生嫉妒,于是心籌劃了這一場事件,大家衆說紛紜,跪在堂下,一句也沒為自己辯解。
其實能說的有很多,是有多沒腦子,會在自己負責的事件裏行兇,能從這裏面得到半分好嗎。
更何況。
家主死了,家主之位就到了?
可更知道,事已至此,說什麽都是無用之舉,只會平添自己的狼狽。
因為沒辦法解釋為什麽明明是自己布置的陣法,自己挑選的心腹,自己確認過的每項細節,怎麽還會發生這樣的事。
Advertisement
腦子一片,只知道一條:陣法到現在都是好的,證明從始至終,只有被自己允許的人進去過。
也就是江召。
他到底怎麽做到的,不得而知,可親眼所見,在溫家數百雙眼睛之下,在溫禾安的外祖母親自出面,問及溫禾安可有允許其他人進大陣時,這位明明知曉一切的的“人”臉凜如霜,說了句:“二主究竟應允幾人陣,江召不知。”
這一句,直接判了的死刑。
溫禾安不是傻子,立刻意識到,江召和溫三合夥了。
一切籌謀,就是為了今日。
溫禾安被定罪時,的外祖母,也就是溫流的祖母神矍鑠,雙目炯炯,如是說:“你說自己沒有行事機,可你無法自證清白,即便蓄意謀害,大逆不道是假,可辦事不力是真。”
“去歸墟,好好反省吧。”
溫禾安就是這樣被剪除一切翅羽,押來了歸墟。
多年籌謀,付諸東流。
到現在,能不能活著,都得看在絕境中生存的心態與本事。
溫禾安都能想象那些昔日的舊相識,在聽到這件事後,都是如何在被背後嗤笑與評論的。知的說為智,膽包天,不知的說糊塗短視,自毀前程,最後來句總結,說因果回,活該。
想了想後面不知道還會來幾波的暗殺,以及日漸拮據的日子,靠在冷冰冰的牆面上,無聲崩潰了好一會,半晌,又默默恢複過來,拉過棉被,原樣蓋回自己頭頂。
先睡覺。
明天還有正事要做。
活著就還有希,活著,未來總有機會將今日所一切悉數奉還。
==
翌日清晨,大霧彌天。溫禾安端著竹筒杯,走出自己砌得十分敷衍的土籬笆牆,到那頭小溪的石板子上洗漱,水面結了冰,用竹筒杯底部去敲開,舀一勺水覆在臉上。
Advertisement
人和靈魂一起清醒了。
回去的路上,溫禾安看見鄰居家的出籠了,公圍著繞了一圈,聲音倒是嘹亮,只是尾上掛了霜,還結了淩,走的時候像吊著幾條廉價流蘇。
一邊拉拉笨重的領,把臉藏進去,一邊笑。
好在昨晚上了藥,今天胳膊只是痛,但并沒有發熱,人的神不錯,在出門前往集市變賣那幾樣東西前,給自己又換了次藥,準備賣完東西後再隨意買點東西當早膳。
帶上門準備出去,發現自己的牆底下放著個紙團,打開一看,是個糖餅和豆團,早就冷了,拿在手上邦邦的,像石頭。
溫禾安愣了一下。
有鄰居,而且是個好心鄰居。
溫禾安第一次發現家附近突兀出現小零食,吃食之類的東西時,是不敢留,也不敢吃的——落到這個境地了,還不小心點,怎麽死的都不知道。
後面發現,自己這個鄰居可能就是典型的熱心腸,小膽子。可能是關于的傳言多而離譜,所以他們也不敢面,不敢談,只做些默默無聞的善舉。
溫禾安折回去,把手裏的餅和團放到屋裏,想,今天要是賣得還不錯的話,就帶個糖葫蘆回來。
如果沒記錯的話,那家好像有個小孩。
歸墟東西邊都有集市,離得更近一點的是西市,但溫禾安卻繞道遠行,去了東邊,足足走了一個半時辰。不是第一次在集市上賣貨了,只潦草地將布往地上一鋪,東西擺上,有喜歡的就談價,磨價,整個過程很是簡單速度。
溫禾安自己了個泥面,往臉上一擺,很有故弄玄虛的唬人氣勢,加之歸墟魚龍混雜,衆人都心有顧忌,怕踢到鐵板,所以并沒有人來找事。
裝藥的瓶子很快賣出去了。
比預想的多了半顆靈石。
至于香囊和玉佩,因為價格夠低,也很快被人買走。
早早收攤,溫禾安轉道去吃了碗餅湯,買了糖葫蘆,又去昨日那家醫館提了幾副藥。此時天已經不早了,卻沒著急回家,反而悄悄遁後山,踏著條泥濘小路,到了歸墟邊上。
歸墟臨海的地方四面八方都有結界,那結界只擋海,不擋人。
今天天氣不好,狂風呼嘯,海浪掀天,溫禾安見到黑沉沉的浪一陣接一陣掀上來,越來越高,最後怒卷噬人的漩渦,完全將整個結界包裹住,歸墟也在此時陷渾然的黑暗中。
一種震懾心靈的危險漫然爬上溫禾安的心頭。
在結界,不擔心自己被海水吞沒,此時皺著眉打量結界外的駭人畫面,越看,心裏就越煩悶。
歸墟外是溺海的一道分支,位置十分特別。
溫禾安的諸多仇敵想殺而後快,可都不曾親自前來,才讓利用各種拙劣的陣法和計策,活到今日,也都歸咎于這份特別。
而今九州被溺海以“十”字形狀分為四塊廣袤的地域,歸墟只是其中極小的一塊,居于西南一隅,和四地相比,宛如滄海一粟,可特殊便特殊在,這裏有一道溺海分支,它則被完全包裹進去。
衆所周知,溺海之危機四伏,波瀾湧的海面下,怪陸離之事頻發。它遇強則強,遇弱則弱,一旦闖,十人九亡,甚至不乏許多開啓了第八,乃至九境的強者喪生其中。
總之,只要進了溺海,甭管份貴賤,天賦高低,一切手段都不頂用,這時候能不能活著,只看一樣。
——你的運氣夠不夠。
不到萬不得已,誰敢去賭這個?
唯有一些被追殺纏,退一步便是死路的,被得沒有辦法了,咬咬牙,心一橫,會跳進溺海涉水進歸墟。其中九九都會死在海裏,唯有極數的人,能僥幸覓得生機。
但也從此和外界失去了聯系。
因為歸墟沒有,沒有擺渡,誰也別想安然無恙從溺海出去,除非還想再試一試自己的運氣。
當世許多世家都與姜氏達長期合作,支付巨額擺渡金,以便出溺海,溫禾安當日就是被溫家仙衛和一個小押進歸墟的。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51 章

醫判
【医生+探案】【双C冤家】在山里养病十年的叶四小姐回家了,所有人都在等她的笑话。才子郭允肯定要退婚了,毕竟叶四小姐蠢丑。叶老太爷要撵她父女,因为不养闲人。叶家虎狼们准备“吃”了她,解决分家产的孽障。可怎么着,要退婚的求婚了、撵人的变黏人的、孽障反吃了虎狼了呢?“有不服的?一起上!”叶四小姐道。沈翼打量叶文初:“给我治病的神医,是你吧!”“您有证据吗?没有的话咱们就继续谈生意好吗?”叶文初道。
122.2萬字8 42476 -
連載1915 章

王爺,聽說你要斷袖了!
傳聞,冥王殿下戰功赫赫,殺人如麻,令人聞風喪膽!傳聞,冥王殿下長相絕美,乃是東陵國第一美男子!傳聞,冥王不近女色,有斷袖之癖,看上了蘇家廢材大少爺!都說那蘇九男生女相,卻是個又軟又弱,任打任罵的廢物。只見某人搖身一變,恢復女兒之身,傾國之姿...
196.5萬字8 29382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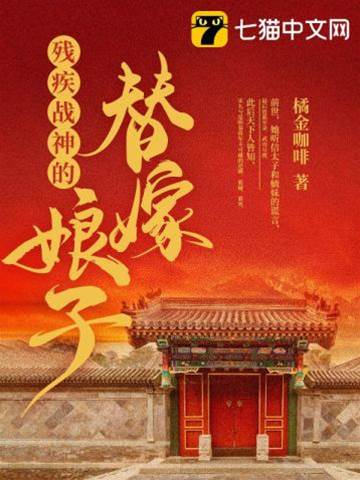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18 35390 -
完結63 章

長燁無月
【和親公主vs偏執太子】【小短文】將軍戰死沙場,公主遠嫁和親。——青梅竹馬的少年郎永遠留在了大漠的戰場,她身為一國公主遠嫁大晉和親。大漠的戰場留下了年輕的周小將軍,明豔張揚的嫡公主凋零於大晉。“周燁,你食言了”“抱歉公主,臣食言了”——“景澤辰,願你我生生世世不複相見”“月月,哪怕是死,你也要跟朕葬在一起”【男主愛的瘋狂又卑微,女主從未愛過男主,一心隻有男二】(男主有後宮但並無宮鬥)(深宮裏一群女孩子的互相救贖)(朝代均為架空)
20.9萬字8.18 17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