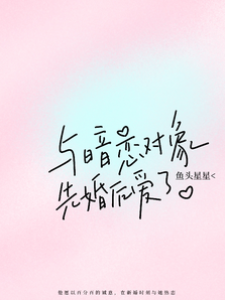《賀總絕嗣?和小啞巴閃婚后真香了》 第十章 你越界了
賀肆的大還帶著寒氣,冷沉木的香氣淡淡縈繞,他將人頂到墻上,俯吻上去。
阮清音隨即到一陣天旋地轉,被人打橫抱到了床上,男人的手掌寬大溫暖,魯急迫地撕開了睡的蝴蝶結,整個人的重量在上。
他一路向下吻,雙手也極其不安分地在上游走著,魯地褪去的所有衫,阮清音起初還試圖反抗,不停地用手推他,用腳踢他。
直到腳踝被人捉住,猛地向下拉扯,下意識屈膝弓,以一種迎合的姿態面對著上的男人。兩人距離極其近,阮清音甚至能數清他有多睫,滾燙的呼吸噴薄在白的頸后,幾乎是一瞬間,不經意到他滾燙的某個部位,瞬間安分了,任由賀肆吻所有的敏點。
狹小溫暖的房間燈昏暗,窗外的雨淅瀝朦朧,雨滴凝水,沿著玻璃一路向下蜿蜒滾落,京北迎來了今年第一場磅礴的秋雨。
賀肆停在了最關鍵的一步,阮清音強掰著他的腕骨覆在了自己的小腹上,對視那雙勾人的眸子,長翹的睫輕,水霧彌漫的眼睛楚楚可憐的著他,祈求的意味深長不語。
他猛地停住了,像是做了場迷離沉醉的夢,戛然而醒。
賀肆一言不發地穿上服離開,他驚醒后才發覺自己剛才有多麼沖,似乎是到深不能自已一般,后悔差點傷到和肚子里的孩子。
司機在樓下等候多時,看見頎長的形從電梯走出連忙撐傘去接,來時天還沉悶,雨未降,秋風一吹,磅礴的雨勢難擋,溫度平白降了好幾度。
賀肆卻抬手擋了傘,任由冰冷的雨珠劈頭蓋臉地砸到上,難耐的燥熱終于褪了大半。
他坐在后座,將結婚證小心揣到大兜,腦子里忍不住回想他們剛才相的點滴。
Advertisement
直到手機振,他狂風驟雨般的思緒才漸漸停歇,歸于平靜。
“四哥,臣琲和蔣丘彥從南城回來了。哥幾個聚一下?再給你補過個接風宴。”陳牧野扯著嗓子喊,他那邊重金屬搖滾音樂吵的賀肆頭疼。
賀肆聲音沙啞,沒好氣地一口回絕“不用。”
“四哥,你怎麼一副求不滿的樣子啊。出來找點樂子去去火。”陳牧野開了外放,在場幾個人不懷好意的哄笑幾聲,賀肆耳尖地聽到臣琲笑的最大聲。
賀肆被人中心窩,直接撂了電話。
他著手機思襯半天,給助理去了個電話,“明天去嵐水灣幫夫人搬家,晚上回家我要看到住過去。門牌號和手機號我發給你了。”
“好的,賀總,還有什麼吩咐嗎?”
“不會說話,別讓不自在。”
助理掛了電話,是自己的錯覺嗎?為什麼他從小賀總低沉冷漠的聲音里聽到了點異樣的緒呢?像是藏匿了忍克制的心疼?
次日清晨,阮清音是被門鈴聲吵醒的,有了昨晚的前車之鑒,特意從貓眼往外看,幾個形壯碩的大漢穿著黑制服來勢洶洶,為首的有些眼。
阮清音仔細回憶了下,頓時想起他們就是昨天醫院那撥人,猶豫著要不要裝作家里沒人,可手機卻不合時宜地響起來。
外面的人顯然聽見了,重新按門鈴。
阮清音胡在上套了件,極其不愿地開了門。
“夫人好,我是賀總的特助宋嘉誠,聽賀總吩咐來幫您搬家。”男人穿著整齊的灰西裝,頭發微短戴著一副黑邊眼鏡,顯得干練而明。
阮清音仍有防備,整個人占據在微開的門,一雙眼睛骨碌地在他們上來回打量。
“夫人,您子不方便干這些重活,您和賀總的婚房在燕京別墅1區,離這得兩個城區呢。”
Advertisement
阮清音稍微有些搖,但這房子才租了沒幾天,一次付了半年的房租,可若是不搬…賀肆鷙的神讓恐懼。
權衡過后,只簡單收拾了幾件服和工作的筆記本電腦,宋嘉誠看著孤零零的行李箱又回頭看了看自己帶過來的五個人高馬大的保鏢,頓時有種殺焉用牛刀的即視。
燕京別墅是京北頂層富人區,一年是業管理費就足以讓普通人在京北郊區買房,綠化植被覆蓋率堪比京北森林地公園,坐在后座,被燕京別墅復雜的地形繞得七葷八素,一陣惡心反胃涌上心頭,臉慘白地靠在車窗上。
直到停在一幢豪華華麗的別墅前,宋嘉誠一路小跑繞到后面,殷勤的替開車門,“夫人,到家了。”
家?還有家嗎?
阮清音懷著忐忑不安的心邁進華麗的別墅,映眼的是挑高六七米的客廳,水晶吊燈如瀑布灑下,真皮黑沙發占據一角,數米面積的純手工羊絨地毯一塵不染,整個別墅裝修富麗,但卻給人一種冷清空曠的覺,沒有半點人住的跡象。
宋嘉誠引著繞過廚房中島臺,徑直走上水晶玻璃的樓梯,鎏金雕花的扶手冰涼,臺階上的燈發出和的,阮清音再次無聲慨賀肆的揮金如土。
這算不算麻雀變凰,嫁豪門了?
“別墅復式兩層,總面積六百平,行李已經放到二樓主臥了。”宋嘉誠為介紹著屋結構,像是專業售樓房屋中介,“二樓書房是賀總平時辦公的地方,二樓有三間客房均配有獨立衛浴,您和賀總住在朝的主臥,玄關是男主人的帽間,這是別墅門卡您拿好。”
阮清音接過信封,順手拆開里面還有張黑金卡。
Advertisement
“賀總給您準備的信用卡,碼是您生日。”
【他不會在這住吧?】阮清音打著手語問。
宋嘉誠看不懂,但是想起賀總那句別讓到不自在,心里暗暗下定決心,出門就去報個手語機構,為總裁特助,怎麼能看不懂夫人的指令呢。
是他無能!
阮清音像是想起什麼,在手機上敲著字——
這房子只有我一個人住對嗎?他不會來吧?
宋嘉誠頓時松了口氣,連連搖頭,義正嚴詞道,“這就是賀總的住,他回國以來一直在這住。”他抬起腕表看了眼時間,拋出致命一擊,“賀總今晚沒有工作安排,大約半小時后到家。”
阮清音微微張著,瞬間一個頭兩個大。
宋嘉誠轉接了通電話,面沉重猶豫道,“您今晚似乎得和賀總一起回老宅,賀總在回來接您的路上了。”
阮清音突然希這是一場夢,起碼不用被賀肆那個閻王帶去地獄赴死。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88 章

戰爺的掌心寵又甜又嬌
前世,慕若晴眼瞎心盲,不顧父母的勸阻,拒嫁戰爺,非要嫁給唐千浩,結果落得個母女倆慘死的下場。重生歸來,她撕爛戰爺的衣衫,咬他一口,囂張地道:“你身上已經有我的烙印,我對你負責任!要麼你娶,我嫁,要麼,我娶,你嫁!”
121.1萬字8 401708 -
完結199 章

寶寶乖老公抱!病嬌大佬低聲誘哄
【超甜!甜就完了,團寵笨蛋小哭包×偏執病嬌自戀狂】司臨淵家族聯姻娶了一個公主,面對一個連飯都不會吃的女人,他能退貨嗎?凌洛洛一臉委屈,“洛洛會乖乖的”司臨淵一臉嫌棄,“能先把你的淚收一收嗎?”倒了八輩子大霉,碰到這麼一個祖宗。最后,司爺真香了……“寶寶,過來,老公抱抱。” ...
34萬字8.18 16980 -
完結212 章

乖,別咬
【甜寵 雙潔】薑未是個軟包子,對上傅晏又愛又怕。她扶著腰,怯生生問:“今天能休息嗎?”男人看向她。“去床上。”
35.6萬字8.18 9637 -
完結591 章

縛月
阮檸戀愛腦舔了厲城淵三年,最後卻落得遍體鱗傷,遠走他鄉的下場。五年後的重逢,她卻爲他的女孩做孕檢,看着報告單上的名字,阮檸陷入沉思。曾經他說自己是他的月光,如今沒想到月亮已經在他身邊。而她只是曾經那一抹被束縛的月色。也就是這一刻她總算明白,和厲城淵的三年成了笑話。直到,她毅然轉身,即將嫁爲人婦。他卻跪在她面前,捧出一顆真心,哭成了當年的那個少年。厲城淵說,“檸檸,別走,求你。”她卻說,“陷落的明月,如何追?”
86.2萬字8 6080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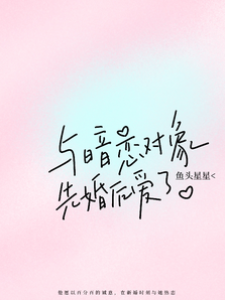
與暗戀對象先婚后愛了
【清冷美人×桀驁貴公子】江疏月性子寡淡,不喜歡與人打交道,就連父母也對她的淡漠感到無奈,時常指責。 對此她一直清楚,父母指責只是單純不喜歡她,喜歡的是那個在江家長大的養女,而不是她這個半路被接回來的親生女兒。 二十五歲那年,她和父母做了場交易——答應聯姻,條件是:永遠不要對她的生活指手畫腳。 _ 聯姻對象是圈內赫赫有名的貴公子商寂,傳聞他性子桀驁,眼高于頂,是個看我不服就滾的主兒。 他與她是兩個世界的人,江疏月知道自己的性子不討喜,這段婚姻,她接受相敬如賓。 兩人一拍即合,只談婚姻,不談感情。 要求只有一個:以后吵架再怎麼生氣,也不能提離婚。 _ 本以為是互不干擾領過證的同居床友。 只是后來一次吵架,素來冷淡的江疏月被氣得眼眶通紅,忍住情緒沒提離婚,只是一晚上沒理他。 深夜,江疏月背對著,離他遠遠的。 商寂主動湊過去,抱著她柔聲輕哄,給她抹眼淚,嗓音帶著懊悔:“別哭了,祖宗。” _ 他一直以為自己與妻子是家族聯姻的幸運兒,直到有一天在她的書中找到一封情書,字跡娟秀,赫然寫著—— 【致不可能的你,今年是決定不喜歡你的第五年。】 立意:以經營婚姻之名好好相愛 【先婚后愛×雙潔×日久生情】
26.1萬字8 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