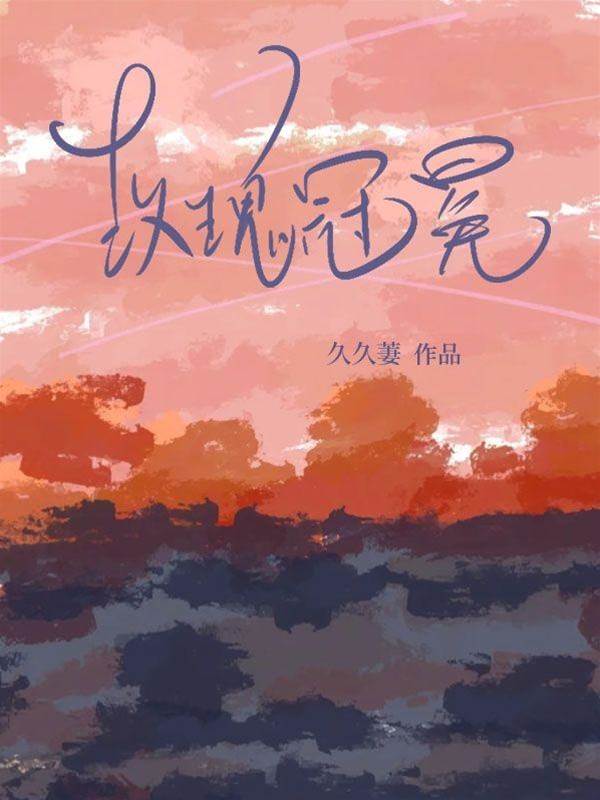《深藏溫柔》 第161章 三年零一個月
尹嬋娟看向吳薇薇,哀求道:“薇薇,你進去勸勸尤瑾吧,他把我兒子的份全都拿走了,讓我怎麼辦?”
吳薇薇低著頭,怯怯道:“他們是正常易。”
“去東南亞開賭場是沒有好下場的,他不可以這樣縱容阿晨,他在害我兒子……你幫我勸勸他吧。”
“我不敢。”吳薇薇咬著下深呼吸,拳頭握。
“我吃飽了。”慌忙起,離開飯桌。
經過客廳時,尤晨拿著支票從書房出來,“薇薇,我哥讓你進書房。”
吳薇薇嚇得一僵,愣住了。
臉逐漸泛白,轉進書房。
在書房的鞋柜里,又換上書房專用一次拖鞋,緩緩走過去,“阿瑾,你找我?”
尤瑾慵懶隨地坐在書桌前,看著手中簽訂的權認購書,淡淡開聲:“明天中午2點的機票,跟我出差大理。”
吳薇薇突然慌了神,急忙搖頭:“我不想去。”
尤瑾抬眸盯著,聲音冷厲如冰:“不想去也得去,這是你作為妻子應盡的責任。”
吳薇薇氣惱道:“我還不是你老婆。”
尤瑾眉眼清冷,角卻噙著笑意:“明天早上去民政局登記完,再出差也來得及。”
吳薇薇臉一陣白一陣青,不安地站著,握著拳頭在發抖。
心慌地發怵。
尤瑾每次出差都會主帶上。
然而卻是咖啡沖了八十多杯也不滿意。
一言不合就把從車上趕下來,把一個人扔在暴風雨的高速上。
需要幫他手洗鞋,親自熨燙服,有一條褶皺都不行。
三更半夜被醒去給他送文件。
跟他出去應酬,被合作商擾,他不但不幫忙,還嫌沒伺候好對方。
因為他的潔癖和強迫癥,不斷重復再重復地去整理和打掃關于他需要用的每一樣東西。
Advertisement
在尤瑾邊這三年,一個豪門千金小姐活了不被的保姆兼狂。
而尤瑾,樂此不疲。
折磨任何一個想親近他的人。
吳薇薇握著發抖的拳頭,咬著牙:“我……不……去。”
尤瑾扔下手中的文件,緩緩起走到吳薇薇面前,瞇著冷眸,修長有力的手指狠狠掐上的后脖子,勾到面前來。
“啊!”吳薇薇痛得驚呼,驚恐地著尤瑾。
尤瑾俊如魔,笑意冷瘆,輕聲輕語低喃:“吳薇薇,你以前不是很我的嗎?為了嫁給我,連死都不怕,怎麼相三年就這麼嫌棄我了?”
吳薇薇嗓音發抖,帶著哭腔:“好痛,阿瑾,你放手。”
尤瑾不但沒松手,反而更加用力,狠狠掐得后面脖頸,低頭在耳邊低喃:“吳薇薇,人生還長著呢,后面幾十年,夠你的了。”
吳薇薇臉上一陣煞白。
尤瑾冷意森森問:“你跟安南那點臟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很多年了吧?”
吳薇薇雙腳一,眼底盡是恐懼不安,吞吞口水,“你……你既然已經發現了……為什麼不生氣,還愿意跟我結婚?”
尤瑾松開的脖子,往后退了一步,從口袋掏出消毒紙巾拭手掌,不不慢道:“臟東西我又不會,娶誰都一樣。”
吳薇薇瞳孔地震,咬著牙低吼:“我要退婚。”
尤瑾輕笑,把手的紙巾狠狠扔到臉上,每個字都帶著兇狠的殺氣,“不退,這婚如你所愿,必須結。”
吳薇薇的淚,一滴滴流淌在慘白的臉頰上。
——
大理的秋天,蒼山洱海間層林盡染。
古城的銀杏葉灑落毯,將千年風韻進每一縷清涼的晨里。
“媽媽,我不想上兒園。”稚的聲音靈好聽,帶著一調皮的可。
Advertisement
宋晚夕低頭看著三歲的兒,圓嘟嘟的小臉蛋,在齊短發的襯托之下,像極一個的小包子,大眼睛水汪汪的,清澈亮,小嘟嘟的,讓人忍不住想一下。
“小芽,媽媽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活要參加,你必須要去兒園。”
“媽媽,帶上小芽好嗎?”小芽嘟著紅嘟嘟的小,“好不好嘛?”
“不好。”宋晚夕蹲下,握住小芽的雙臂,“小芽聽話,媽媽忙完就來兒園接你回家。”
“幾點忙完?”
宋晚夕指著天空,“太公公下山的時候,媽媽就忙完了。”
小芽笑容爛漫:“好,我在兒園等媽媽。”
宋晚夕會心一笑,往臉蛋上親了一口,將抱起來,送兒園。
離開兒園,驅車開往科技會館。
中午時分。
科技會館大廳里坐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科學家、專家、以及政府里最權威的員,各大優秀企業的領導人。
記者把整個大廳得水泄不通,長槍短炮對準舞臺,等待頒獎典禮開始。
這可是國家最權威的最高科學技獎頒發活。
宋晚夕已經提前收到通知,研發的罕見病新藥榮獲了最高專利獎以及最高科學技獎。
今天特意穿得大方得,也化了淡妝,準備好等會上臺領獎的言詞。
此時此刻,心里格外張。
這次的頒獎典禮,是全國聯播的。
心里多有些忐忑。
活開始,新聞也在直播,現場氣氛嚴肅莊重。
主持人在臺上致辭,頒獎開始后,宋晚夕作為第一個被邀請上臺的。
宋晚夕心跳加劇,激又張。
這是多科學家一輩子都無法到達的高度,而只花了三年時間,攻克了某個罕見病領域的大難題。
Advertisement
主持人在一旁介紹的功偉績,宋晚夕看著臺下這麼多人,張到雙手滲汗。
在視線掃過臺下那一瞬,在最前排的中間,看到一個悉的影。
倏然!
宋晚夕整個人都僵住了,頭皮發麻,心臟驟停了數十秒后,突然瘋狂暴跳,覺全世界都安靜了。
的視線里,白茫茫一片,只看到尤瑾坐在臺下。
男人神淡然,眸幽深復雜,冷冷地凝著。
四目對視,眼波流轉之間,盡是陌生與冷淡。
宋晚夕沒想到他也會在這里,心復雜又凌。
隨后,當地員上臺給頒獎,對著話筒,心不在焉地發表言。
這時,看到尤瑾向旁邊的保鏢勾了勾手指。
保鏢低下頭,聽他幾句吩咐之后,離開轉離開會場。
宋晚夕的視線追隨那個匆匆離開的保鏢,心慌意,不好的預涌上心頭。
匆忙完結言,拿著獎項和證書下場,后續的記者采訪和慶功宴會也不參加了,驅車直奔兒園。
接回小芽那一刻,宋晚夕的心才安穩下來。
把小芽放到車后座的兒座椅上,系好安全帶。
“媽媽,太公公還沒下山呢。”小芽笑嘻嘻地問:“你怎麼來得這麼早?”
宋晚夕的小臉蛋,笑容溫,輕聲輕語:“因為媽媽想小芽了。”
“小芽也想媽媽了。”小芽把眼睛瞇兩條彎彎的線,聲音糯糯的。
“咱們回家吧!”宋晚夕出車廂,關上門,繞到車頭的一瞬。
突然沖出兩個西裝革履的保鏢,一個按住的車門,另一個擋在后。
“宋小姐,謝帶路。”
宋晚夕警惕地著他們,“天化日之下,你們想干什麼?”
這時,不遠的豪車車門被保鏢打開。
Advertisement
尤瑾從車下來,徑直走向。
宋晚夕張地著他。
三年不見,即使容貌沒多大變化,但他的眼神是那樣的冰冷陌生。
宋晚夕看著尤瑾從邊走,沒有半句話語。
宋晚夕張不已,要阻止他:“尤瑾,你要干什麼?”
兩名保鏢魯地把按在車門上,彈不得。
尤瑾開門,坐車廂后座。
小芽好奇地著他,“你是誰啊?”
尤瑾凝著可又漂亮的小芽,三年來第一次由衷地出溫的微笑,聲音極其輕盈:“我是你爸爸。”
“爸爸?”小芽眨眨大眼睛,驚訝地張大,的小手捂住,好片刻才冒出一句:“是啊,你跟我爸爸的照片長得一模一樣,你真的是我爸爸!”
尤瑾出手指,輕輕了呼呼的小臉蛋,“你什麼名字?”
“我小芽。”
“小芽,跟爸爸回家好嗎?”
“回哪個家?”
“爸爸的家。”
“那媽媽呢?”小芽略顯不安。
尤瑾解開的安全帶,單手把抱起來,下了車,另一只手擋住的視線,聲細語哄著:“媽媽現在很忙,等忙完就來爸爸家里接小芽。”
宋晚夕被兩名保鏢在車門前,被捂住,掙不了,也喊不出聲音。
眼睜睜看著小芽被尤瑾帶上車。
由始至終,尤瑾也沒看一眼,沒跟說一句話,在眼皮底下強行把小芽給帶走了。
直到尤瑾的豪車消失在馬路上,保鏢才松開,上了另一臺車離開。
宋晚夕氣得全發抖,雖然知道尤瑾不會傷害小芽,但那是十月懷胎,辛辛苦苦養了三年的兒。
他要見兒也不是不可以。
但用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段搶走的孩子,實在太過分了。
宋晚夕六神無主,掏出手機報警。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690 章

重生后,渣總追妻火葬場
雲桑愛夜靖寒,愛的滿城皆知。卻被夜靖寒親手逼的孩子冇了,家破人亡,最終聲名狼藉,慘死在他眼前。直到真相一點點揭開,夜靖寒回過頭才發現,那個總是跟在他身後,笑意嫣然的女子,再也找不回來了。……重生回到18歲,雲桑推開了身旁的夜靖寒。老天爺既給了她重來一次的機會,她絕不能重蹈覆轍。這一世,她不要他了。她手撕賤人,腳踩白蓮花,迎來事業巔峰、各路桃花朵朵開,人生好不愜意。可……渣男怎麼違反了上一世的套路,硬是黏了上來呢……有人說,夜二爺追妻,一定會成功。可雲桑卻淡淡的應:除非……他死。
215.7萬字8 322367 -
完結1890 章

許你情深深似海
為了得到她,他不擇手段,甚至不惜將她拉入他的世界。 他是深城人盡皆知的三惡之首,權勢滔天,惡跡斑斑,初次見面,他問她:「多少錢?」 ,她隨口回答:「你可以追我,但不可以買我」 本以為他是一時興起,誰想到日後走火入魔,寵妻無度。 「西寶……姐姐,大侄女,老婆……」 「閉嘴」 心狠最毒腹黑女VS橫行霸道忠犬男
342.7萬字8 29518 -
完結77 章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408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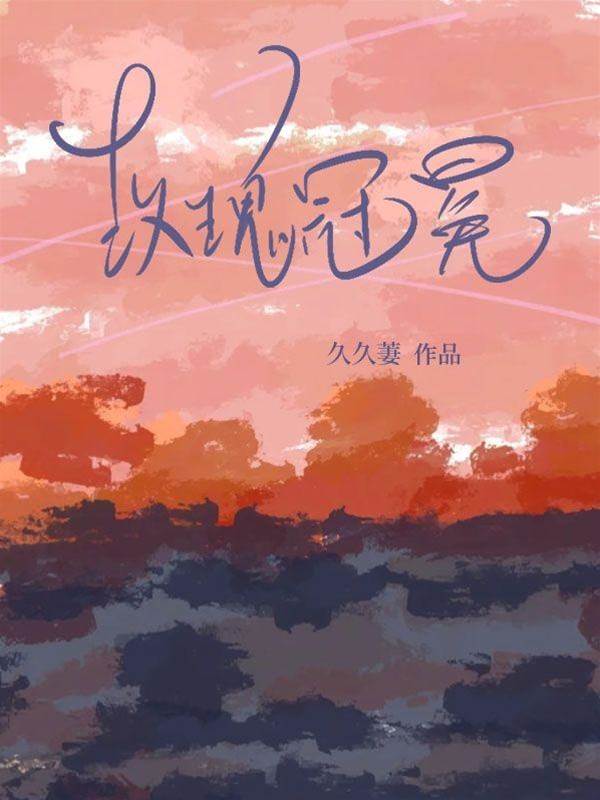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61089 -
完結66 章

思餘如潮
孤冷學霸孤女VS冷漠矜持霸總父母雙亡的孤女(餘若寧),十一歲被姑姑接到了北城生活。後來因為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餘若寧嫁了沈聿衍。有人豔羨,有人妒忌,有人謾罵;當然也有人說她好手段。殊不知,這是她噩夢的開端。
15萬字8.18 2415 -
完結159 章

情疤
【落魄千金VS黑化狗男人】溫家落敗后,溫茉成為了上流圈子茶余飯后的談資。 橫行霸道慣了的千金小姐,一朝落魄成喪家敗犬。 是她應得的。 傳聞圈中新貴周津川手段狠辣,為人低調,有著不為人知的過去。 無人知曉,當年他拿著溫家的資助上學,又淪為溫家千金的裙下臣。 動心被棄,甚至跪下挽留,卻只得來一句“玩玩而已,別像只丟人現眼的狗。” …… 溫茉之于周津川,是他放不下的緋色舊夢,是他心頭情疤灼灼。 既然割不舍,忘不掉,那就以愛為囚,相互撕扯。
28.6萬字8 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