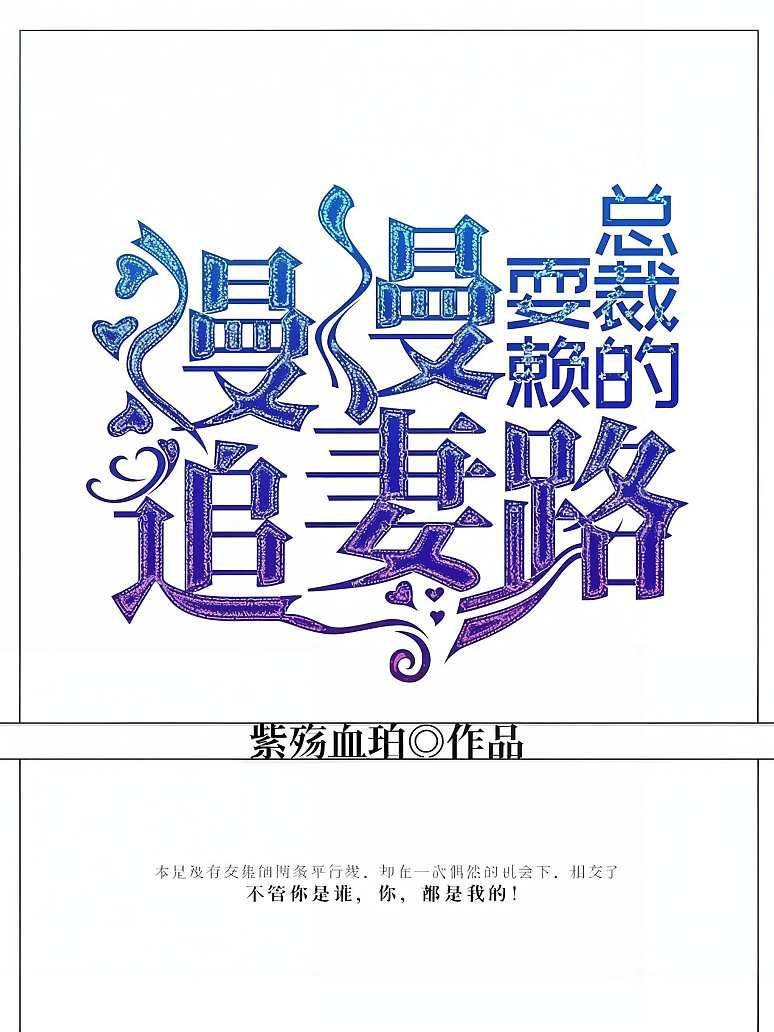《閨蜜才是老公白月光,我選京圈太子當新歡》 117:你們是什麼人?
沈蔓西頭發凌地在角落里,蒼白的臉上印著清晰的指痕,雙手死死握著一塊玻璃碎片,脆弱纖瘦的正在不住發抖。
著氣,破碎的領口出的鎖骨,隨著口一陣劇烈起伏,可見了極大的驚嚇。
胖的男人倒在地上,他上赤,帶也解開了,正捂著脖子痛得不住扭。
他的指都是,蜿蜒到手臂,可見傷得不輕。
休息室里一片狼藉,地上床上都是斑駁的跡。
服務員捂著肚子要去看休息室里的景象,被安慕洲怒吼一聲,嚇得紛紛回脖子。
“滾!”
安慕洲進休息室,一把關上門,不想外面的人看到現在的沈蔓西,隨意揣測在上發生何事?
他下外套,走向沈蔓西。
沈蔓西顯然已經意識模糊,發現有人靠近,揮著手里的碎片就要刺。
“是我!”
安慕洲兀地溫下來的聲音,仿佛絕境黑暗里的一盞明燈,照亮了沈蔓西眼前的景。
緩緩抬起頭,掌大的小臉在凌的發下,那雙水盈盈的眸子,此刻空黯淡,脆弱得好像隨時都會碎掉。
的瓣了,發出低弱的,沙啞的聲音。
“安……安醫生?”
“是我!”
安慕洲蹲下來,用外套包裹住沈蔓西。
他第一次發現,長得好瘦好小,他的外套顯得很大,可以將蜷起來的整個包裹住。
沈蔓西繃的最后一弦徹底斷裂了,一頭扎安慕洲的懷里,啜泣起來。
“你終于來了!嗚嗚……”
安慕洲抱懷里哭得雙肩的人兒,輕的后腦。
“嗯,我來了,不用怕了。”
安慕洲幫沈蔓西把外套裹得更些,等沈蔓西的緒穩定了些,他打了一通電話出去,說了現在的位置。
Advertisement
掛斷電話后,緩緩回頭看向終于從地上爬起來的胖男人。
他的眼神又冷又狠,仿若一頭已經出可怖獠牙的狼。
車制片原本還想質問安慕洲是什麼人,膽敢闖他的房間,雖然責怪,但也慶幸有人闖進來,不然他怕今晚代在這里。
當他及到安慕洲冷酷的目,瞬間慫了,指了指安慕洲,捂著脖子往外走。
“我……我不跟你一般見識!”
他單手撿起地上的服,本想穿上服,發現脖頸還在流,又趕捂住傷口。
不知道是不是割破了脈,怎麼流了這麼多的?
他要去醫院。
立刻馬上。
就在車制片即將打開房門的時候,安慕洲的薄幽幽吐出兩個字。
“站住。”
明明他的聲音不高,卻給人一種無形的威,車制片生生的邁不開了。
整個碩的都僵在原地。
他抖轉過,看著男人冷的背影,哆嗦問。
“你……你還想干什麼?”
安慕洲沒說話,打橫抱歉沈蔓西,對車制片角邪氣一勾,笑了。
“不著急,有點事找你談。”
悉安慕洲的人都會知道,他這一笑,是生死難料的意思。
他抱著沈蔓西走到門口,車制片趕讓路。
怯怕抖的樣子,稽的像個球。
安慕洲抱著沈蔓西出門,沈宛藝趕迎上來,哭著問。
“姐姐沒事吧?”
安慕洲冷冷掃了沈宛藝一眼,那眼神好像刀子在皮上刮過,讓沈宛藝心肝俱。
呆呆著男人俊帥的臉龐,五立,如刀削斧鑿般,一雙黑眸宛若寒潭,高的鼻梁,薄削的瓣,每一線條都似被藝家心打磨的完之作。
沈宛藝有那麼一瞬看呆了。
之前看沈蔓西和安慕洲的緋聞,就覺得安慕洲很帥,沒想到本人比照片更帥,更讓人心。
Advertisement
“滾開!”安慕洲罵了聲。
就在沈宛藝即將讓開的時候,一只纖細的手臂,一把抓住沈宛藝。
那只手很瘦,纖白如玉,力氣卻很大。
沈蔓西吃力從安慕洲的懷里出半張臉,一雙空無的眼眸,死死盯著沈宛藝。
“日記本呢?”
沈宛藝僵在原地。
顯然不想給沈蔓西,事搞砸了,還想留著日記本為日后打算。
安慕洲一眼看穿沈宛藝的心思,低吼一聲,“還不快去拿!”
沈宛藝渾一,連忙小跑向放在沙發上的包,從里面拿出一個深藍的破舊日記本,遞了過來。
沈蔓西一把抓過日記本,死死抱在懷里,慢慢閉上眼,徹底失去意識。
安慕洲抱著沈蔓西走出包廂。
沈宛藝正要跟上去,包廂門在這一刻被關上,從外面鎖住。
沈宛藝慌了,用力敲門,門外卻沒有一點靜。
于導捂著肚子從地上爬起來,“什麼況?”
沈宛藝也不知道,“我們好像被鎖在這里了。”
車制片捂著脖子從休息室出來,整張胖臉因為疼痛扭曲變形。
“開門,我要去醫院!”
他用力敲門,可門外沒有任何回應。
過了大概十五分鐘,門終于開了,來的卻是一群形膘膀的黑保鏢。
氣勢洶洶,陣仗煊赫,給人一種黑云頂的迫。
保鏢們為首的人是魏明。
他抬了抬手,保鏢們當即上前,住于導,車制片,還有沈宛藝。
“你們干什麼!放開我!”于導大聲喊。
車制片怕臉被人拍,這家餐廳可是經常有圈人士顧,急忙用手里的上捂住臉。
“你們知道我們是誰嗎?最好放開我們。”車制片威脅道。
然而沒人理他,著他們往外走。
于導意識到什麼,也急忙捂住臉,含糊不清問,“你們是什麼人,你們要帶我們去哪兒?”
Advertisement
沈宛藝也怕了,但不敢出聲。
到了餐廳外。
于導和車制片被保鏢塞上一輛黑車。
沈宛藝即將被塞上車時,魏明稍作猶豫,讓人把沈宛藝送上他的車,親自送沈宛藝回沈家。
“你們,你們到底是什麼人?”沈宛藝在車上驚懼問。
到了沈家。
魏明帶人按響門鈴。
來開門的傭人見二小姐被一群黑人押著,嚇得趕去沈文學。
沈文學知道沈宛藝今天出去吃飯了,還以為沈宛藝會高高興興回來公布,的角搞定了,沒想到卻是被一群來歷不明的人押回來。
他也被眼前的陣仗嚇到了,茫然問,“你們是?為什麼押著我的兒?”
沈文學不認識魏明,但看魏明的氣度,還有一看就知道是訓練有素的專業保鏢,便知道他們來頭不小。
魏明抬手,保鏢們放人。
沈宛藝趕忙跑向沈文學,躲到他后,委屈又恐懼地吸著鼻子。
魏明緩緩開口,“管好你的兒,下次再帶著親姐姐出去陪客,的演藝之路就是到頭了!”
沈文學的眼睛猛地張大,回頭質問沈宛藝,“什麼?你帶蔓西去做什麼?”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6 章

白蓮花她不干了
1、 紀棠被北城宋家選中,嫁給了繼承人宋嶼墨,成為人人羨慕的豪門貴婦。 作為作為位居名媛榜之首的紀棠時刻保持著溫柔得體,但凡公開場合,她都三句不離秀恩愛,結果夫妻同框次數為零,被號稱是最稱職的花瓶太太。 喪偶式形婚三年,宋嶼墨從未正眼看過自己這位妻子。 空有一張美麗的臉,性格乏味無趣。 直到網傳兩人婚姻關系破裂那日,紀棠早就將已經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放塑料老公面前,哭著等他簽字分財產。 ——“老公……嚶嚶嚶人家離開你就不能活了!” 2、 后來,圈內姐妹忍不住紛紛追問她跟宋家這位艷冠全城的公子離婚感受? 紀棠撩著剛燙好的深棕色大波浪長發,輕輕一笑: 【跟他這種無欲無求的工具人離婚要什麼感受?】 【要不是宋家老爺子要求我結婚三年才能分家產,誰要用盡渾身解數扮演白蓮花哄他玩?】 【幸好能成功離婚,再不提離,老娘就要忍不住綠了他!】 笑話!拿著離婚分到的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整天住豪宅開豪車,被娛樂圈小鮮肉追著獻殷勤,過著醉生夢死的小富婆生活,不香嗎? 誰知剛轉身就看見站在人群外的男人,穿著純黑色西裝的氣度清貴又驕矜,似笑非笑地望著她。 “紀棠”宋嶼墨金絲眼鏡下的眸子斂起,視線盯著這個美艷又明媚的女人,優雅地撕了手上那份巨額離婚協議書,聲音清冷而纏綿:“不是離開我,就不能活了嗎?” “那就好好活。” 紀棠:“…………?” 不,我想死!!! · 演技派白蓮花x偏執狂腹黑霸總。 先婚后愛,狗血俗套故事,男主追妻火葬場的雙倍排面已經在安排了
36.4萬字8.18 29200 -
完結1297 章
替嫁甜婚:爹地,媽咪太撩了
一場陷害,她與陌生男人荒唐一夜,她落荒而逃而他緊追不舍;為給外婆治病,她被迫頂替繼妹嫁入豪門霍家,婚后卻被發現懷孕!霍御琛——她的新婚丈夫,亦是霍家繼承人,手段殘忍冷血無情。對她趕盡殺絕,最終害了肚中孩子。六年后,她攜二寶歸來,技能全開,狠狠虐了曾欺負她的人。前夫卻忽然跪地求饒:“老婆我們復婚吧,當年睡了你的人是我,我要負責!”她不屑拒絕,
137.7萬字8 71757 -
連載336 章

女兒火化時,渣總在為白月光放煙花
女兒腎衰竭,手術前,她最大的心愿就是過生日爸爸能陪她去一次游樂場,她想跟爸爸單獨相處。我跪在傅西城的面前,求他滿足女兒的心愿,他答應了。 可生日當天,女兒在寒風中等他,等到吐血暈厥,他都遲遲沒有出現。 女兒病情加重,搶救失敗。 臨死前,她流著淚問我,“媽媽,爸爸為什麼喜歡程阿姨的女兒卻不喜歡我?是我還不夠乖嗎?” 女兒帶著遺憾離開了! 從她小手滑落的手機里正播放著一條視頻,視頻里,她的爸爸包下最大的游樂場,正陪著他跟白月光的女兒慶祝生日。
67.7萬字8 17878 -
完結707 章

離婚后,厲少追妻路漫漫
五年前,她放棄尊嚴淪為家庭主婦,卻在孕期被小三插足逼宮被迫離婚。 五年后,她帶著兩只萌寶強勢回歸,手撕渣男賤女搶回屬于她的家產。
127.9萬字8 4154 -
完結258 章

沈總別虐了,夫人離家出走了
【倔犟驕傲的前鋼琴公主VS偏執占有欲極強的房地產霸總】 20歲的黎笙: 是被沈硯初捧在心尖上的女友,是最羨煞旁人的“商界天才”和“鋼琴公主”。 25歲的黎笙: 是被沈硯初隨意玩弄的玩具。 沈硯初恨她,恨到骨子里。 因為她哥哥一場綁架策劃害死了他的妹妹。 18歲的沈聽晚不堪受辱從頂樓一躍而下,生命永遠停留在了最美好的年華。 而她跟沈硯初的愛情,也停留在了那一天。 再見。 已是五年后。 沈硯初對她的恨絲毫未減。 他將她拽回那座她痛恨厭倦的城市,將她困在身邊各種折磨。 日復一日的相處,她以為時間會淡忘一切,她跟沈硯初又像是回到曾經最相愛的時候。 直到情人節那晚——— 她被人綁架,男人卻是不屑得嗤之以鼻,“她還不配我拿沈家的錢去救她,撕票吧。” 重拾的愛意被他澆了個透心涼。 或許是報應吧,她跟沈硯初的第二個孩子死在了綁架這天,鮮血染紅了她精心布置的求婚現場。 那一刻,她的夢徹底醒了。 失去了生的希望,當冰冷利刃劃破黎笙的喉嚨,鮮血飛濺那刻,沈知硯才幡然醒悟—— “三條命,沈硯初,我不欠你的了。”
46.5萬字8 184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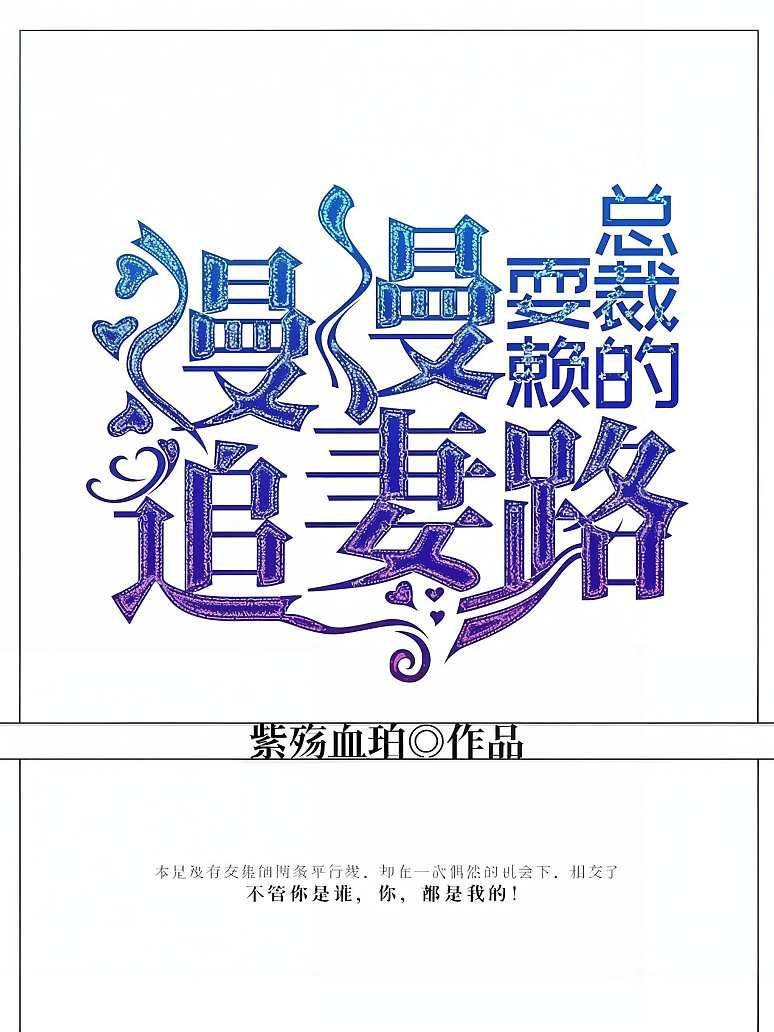
耍賴總裁的漫漫追妻路
本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件一:“醫藥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我覺得,把我自己賠給你就夠了。”事件二:“這是你們的總裁夫人。”底下一陣雷鳴般的鼓掌聲——“胡說什麼呢?我還沒同意呢!”“我同意就行了!”一個無賴總裁的遙遙追妻路~~~~~~不管你是誰,你,都是我的!
27.3萬字8 1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