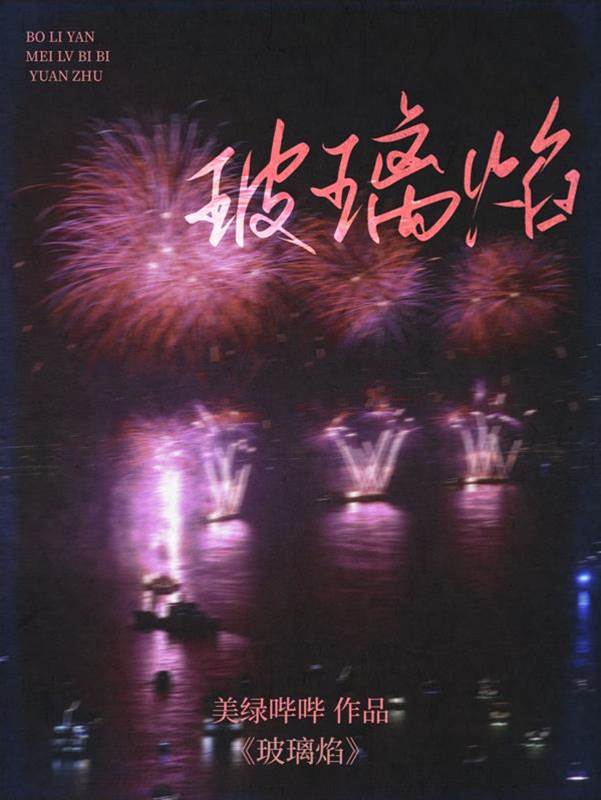《戲夢入君心》 第1卷 第105章 叮鈴——
萬籟俱寂的深夜,整個世界仿佛被一層濃稠的墨淹沒。
窗框外,月過斑駁的樹葉,在地面上灑下一片片破碎的銀白。
屋,一盞孤燈散發著微弱的,燈下,是骨節分明的手握著床單。
玉牌清亮的聲音響起,與之合鳴的還有鈴鐺的脆響。
‘叮鈴——’
“嗚……”
段君彥專注地翻閱著手中的‘書籍’,只有筆尖在紙上挲的沙沙聲,未免太過單調。
大紅的細繩上穿著幾個小鈴鐺,晃一晃就是叮鈴作響。
漂亮的腰鏈襯得裴夢桉本就又細又白的腰肢更加細白。
大紅和白啊。
曖昧極了。
輕輕作間,就是時快時慢的響聲。
段君彥按了按裴夢桉腰間的小痣,著指尖下的抖,只覺得頭皮發麻。
裴夢桉搖頭咬住枕頭的尖尖,又被段君彥手救了下來,低頭吻了上去。
段君彥這人也算是無師自通,自學能力忒快。
遙遙想起兩人第一次時,其實即便是收了力氣,也實在是弄疼了裴夢桉。
只是那會兒,忍著罷了,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講。
但現在段十爺已經爐火純青了,完全帶著節奏,猛烈的時候能將人變海上孤舟,溫的時候更是招架不住。
裴夢桉輕輕息著,湊到段君彥頸側,落下滾燙的吻。
‘叮鈴——’
段君彥扶著他虛的脖頸,吐出的每一個字都引得下之人栗不已:“為什麼,總吻我的頸側?”
裴夢桉嗚咽著,說話斷斷續續,“因為啊,之前要走……想著,想著這樣,等日后……您……總會想起我。”
總會想起,曾經有這麼一個人,為了另一個人拼了命的奔來。
總會想起……
Advertisement
段君彥低了頭,把額頭抵在裴夢桉的鎖骨。
滾燙的水滴打在的皮上,引得裴夢桉微微瑟。
‘叮鈴——’
清脆的聲響伴著段君彥低啞的聲音響起,“裴夢桉,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他聽到了,輕輕轉,進段君彥的懷里,腰間那串帶著鈴鐺的腰鏈便撞出細微聲響,蜿蜒如溪流,致的小鈴鐺在尾端輕輕晃,沒更深的隙,隨著他的作,像是在訴說著的故事。
這下可一點兒也不單調了,有的是好與幸福陪伴著段君彥度過這漫長的夜晚 。
……
客房中,段君堯不老實的把被子踢到一邊,起想開窗戶,卻被攔住。
楚懨之握著段君堯的手腕,如同以往的每一次,“爺,別開窗了,您喝酒會頭痛。”
聲音低低的,幾乎算得上是囈語。
段君堯愣了一下,很慢很慢的轉頭過來,看向楚懨之,仿佛大夢初醒。
屋里沒有開燈,只有月過窗灑進來的輝。
段君堯的眸子暗沉沉的,看不出緒。
恍惚間,楚懨之好像又看到了曾經的那個段君堯……
“楚懨之,你他媽就是老子養的狗,誰允許你管老子的事?”
“這窗戶,老子想開就開,你算個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欠打?嗯?說話?”
記憶里的狠厲聲音讓楚懨之突然有些膽怯。
沒有了溫暖的輝,子好像都冷了下來。
楚懨之握在段君堯腕子上的手,不自覺的就松了下來,眉眼間盡是瑟。
卻在退開前,又被人握進了掌心。
段君堯看著楚懨之,專注極了。
楚懨之又愣了一下,這才注意到,那對漆黑的雙眸中,是月投進去后打碎的溫。
Advertisement
不一樣了。
“楚懨之……”
段君堯把人撈過來抱進懷里,覆在他后背上的手隔著料輕輕挲,“又抱到你了,真好……”
沒有侮辱謾罵,他說,真好。
楚懨之走后,段君堯夢到過他很多次,醉酒,開窗,卻不再有人制止。
夢里看到的影,也會在須臾之間消散殆盡。
那是徒余哀傷的冰冷。
現在好了,懷里滿了,心也滿了。
段君堯抱著人,聲音發,“你不在我邊,我總也不記得,喝多了就想開窗,第二日就要頭疼,疼的厲害了,又想你,想你該有多疼……”
楚懨之安靜的站著,聽著,心里難得厲害。
這麼多年了,沒人在意他疼不疼。
一直到今天……
段君堯解了楚懨之的扣。
他上有許多疤痕,并不好看,但其實段君堯看過無數次,而這些疤痕大多都是因為他。
段君堯的指尖輕輕掠過楚懨之手腕上的傷痕,像羽心尖,“這是你剛來我邊的時候,不小心用刀刮的吧。”
那時楚懨之還握不好刀,劃傷了自己,是段君堯為他包扎的。
再往上是小臂,“這是第一次去平場子的時候,被啤酒瓶碎片蹭的吧。”
鎖骨,“這是跟那群人訓練的時候沒輕重留下的吧。”
脖頸,“這是當時為了讓你到段君彥邊來留下的……”
一,一件件,段君堯全都知道。
最后,他到了楚懨之的手臂,聲音哽咽的幾乎連不句。
“對不起……楚懨之,對不起……”
他們明明相伴多年,他帶給楚懨之的好像只有傷痛。
段君堯喝多了,酒氣縈繞,挖掘著心里對人的悔恨。
楚懨之抬手,了段君堯肩上差不多已經恢復好了的傷口。
Advertisement
聲音輕的如同嘆息,“沒關系。”
散落在的地毯上,段君堯帶著淚水的吻過一個又一個疤痕。
不同了……
不痛了。
前所未有的溫是段君堯給楚懨之的保證,他忍著,任由額角的汗珠滴落下來,卻始終不敢放肆而為。
是清醒的克制。
段君堯現在明白了,還好,還不算晚。
楚懨之抬眸,看著男人手臂上因為忍而突出的青筋,閉了閉眼,偏頭咬了上去。
很重,很痛。
太突然了,段君堯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卻沒制止,任由楚懨之發泄。
腥味在口腔里彌漫,楚懨之終于流下了眼淚。
他總是沉默著,忍著……
段君堯心疼的親吻著楚懨之的發,將他的抱在懷里。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9 章

將軍打臉日常
那年陳國同遼軍交戰,沈煙冉頂替了兄長的名字,作爲沈家大夫前去軍中支援,見到江暉成的第一眼,沈煙冉就紅透了臉。 鼻樑挺拔,人中長而挺立之人是長壽之相,做夫君最合適。對面的江暉成,卻是一臉嫌棄,拽住了她的手腕,質問身旁的臣子,“這細胳膊細腿的,沈家沒人了嗎?”當天夜裏,江暉成做了一場夢,夢裏那張臉哭的梨花帶雨,攪得他一夜都不安寧。第二日江暉成頂着一雙熊貓眼,氣勢洶洶地走到沈煙冉跟前,“不就是抓了你一下手,說了你一句,至於讓你哭上一個晚上?”昨夜睡的極爲舒坦的沈煙冉,一臉懵,“我沒,沒哭啊。”從此兵荒馬亂的戰場後營,沈煙冉如同一條尾巴,跟在江暉成身後,“將軍這樣的身子骨百年難得一遇,唯獨印堂有些發黑,怕是腸胃不適......”江暉成回頭,咬牙道,“本將沒病。”不久後,正在排隊就醫的士兵們,突地見到自己那位嚴己律人的大將軍竟然插隊,走到了小大夫面前,袖子一挽,露出了精壯的手腕,表情彆扭地道,“我有病。” 前世沈煙冉喜歡了江暉成一輩子,不惜將自己活成了一塊望夫石,臨死前才明白,他娶她不過是爲了一個‘恩’字。重活一世,她再無他的半點記憶,他卻一步一步地將她設計捆綁在了身邊。夢境歸來那日,她看着他坐在自己的面前,含着她前世從未見過的笑容同她商議,“嫁衣還是鑲些珠子好。”她擡頭看着他,眸色清淡,決絕地道,“江暉成,我們退婚吧。”他從未想過她會離開自己,直到前世她用着與此時同樣的口吻,說出了那聲“和離”
22萬字8 12194 -
完結1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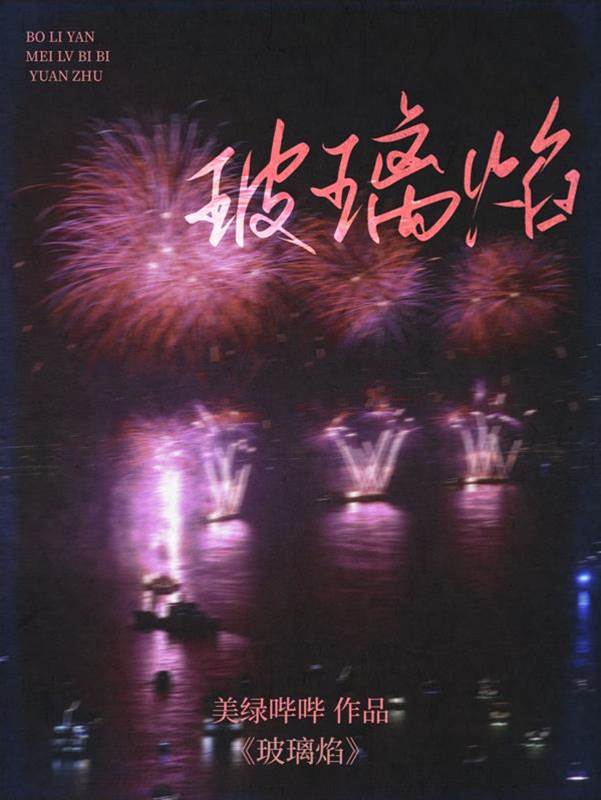
玻璃焰
[已簽約實體待上市]【天生壞種x清冷校花】【大學校園、男追女、協議情侶、強製愛、破鏡重圓】黎幸在整個西京大學都很有名。高考狀元,夠美,夠窮。這樣的人,外貌不是恩賜,是原罪。樓崇,出生即登上金字塔最頂層的存在優越家世,頂級皮囊但卻是個十足十的人渣。——這樣兩個毫無交集的人,某天卻被人撞見樓崇的阿斯頓馬丁車內黎幸被單手抱起跨坐在腿上,後背抵著方向盤車窗光影交錯,男人冷白精致的側臉清晰可見,扣著她的手腕,親自教她怎麼扯開自己的領結。——“協議女友,知道什麼意思嗎?”“意思是牽手,接吻,擁抱,上床。”“以及,愛上我。”“一步不能少。”——“玻璃焰,玻璃高溫產生的火焰,銀藍色,很美。”
25.7萬字8 14204 -
完結946 章

替嫁殘疾老公後,我偷孕三寶
一場陰謀,孟初念被家人從鄉下接回,替嫁給傳聞中權勢滔天、殘廢醜陋的傅家九爺。新婚之夜,他冷酷無情的捏上她下巴:“老實點,否則別怪我粗魯!”她看著坐在輪椅上的殘疾老公,毫不留情的回懟:“就你這樣,能對我幹嘛?”話音剛落,就見殘疾老公忽然站了起來,把她狠狠吻在床上!......婚後,所有人都等著孟初念這個鄉下醜八怪被殘酷暴戾的傅九爺弄死。誰知一場宴會,她摘下偽裝,露出絕色容顏。真實身份更是驚掉眾人眼球國際上最深不可測的神秘黑客是她!享譽全球的神醫跟在她後麵乖乖叫師傅!令全球大佬都聞風喪膽的聯盟組織追著她叫老大!殘忍冷血,不近女色的傅家九爺更是高調官宣:孟初念是我此生唯一摯愛!對付她,就是與我為敵!(1v1,先婚後愛,逆襲虐渣)
176.1萬字8.18 78438 -
完結148 章

沈小姐愛意燃燼,禁欲顧總紅了眼
在顧家做了十年被低看的繼女,沈雨嫣成了商業聯姻的犧牲品。奮不顧身向愛戀十年的男人祈求庇護,得到的只有嘲諷。她終于醒悟,求人不如求己。企圖在一場契約婚姻的掩護下,完成涅槃重生。 可當她成爲非遺大師,名滿世界,轉身離開時,那冷心冷情的男人,卻紅了眼,雙手緊緊纏住她的腰,低聲祈求:“別鬧了,你走了,總裁夫人的位置誰來坐?”
26.6萬字8.18 31899 -
完結581 章

陸總誘她高攀
作為沈家的童養媳,蘇楹孝順沈家長輩,成為沈氏項目部總監,為沈氏嘔心瀝血,最後卻慘遭拋棄,被迫讓位。沒人知道,她是沈氏股東之一,被拋棄後她直接撤資,沈氏幾度陷入危機。自此,她和沈確老死不相往來,各生歡喜。後來,沈確得知真相,淚眼朦朧跪在她麵前,奢求原諒。她還沒開口,身後看戲的男人將她摟住,“寶貝,好馬不吃回頭草,何況你是人。”男人看向沈確,宣示主權,“她是我的人!”
97萬字8.18 33903 -
完結187 章

月光潮汐
席悅在大四這年終於得償所願,和自己從高中就開始暗戀的男生走到一起。 第一次戀愛沒經驗,她以爲在一起半年只到擁抱是正常進度,直到有一天,她看見自己男朋友和他剛認識三個月的舞蹈系花在路燈下接吻。 席悅失戀了,但她並不孤單。 當她抱着一堆東西呆愣在原地時,系花的男朋友就銜着煙站在她旁邊。 明明也是受害者,可許亦潮比她得體許多,像沒事人一樣撣了撣菸灰,還不忘嘲諷她:“你男朋友好像戀愛了哦。” - 跟席悅的默默無聞不同,許亦潮絕對算是濱大的風雲人物。 家境優渥,頂着一副紈絝的渣男臉,明明具備遊戲人間的各類要素,可他玩票般成立的遊戲工作室,只用了兩年時間就在行業內異軍突起。 席悅陰差陽錯進入他的公司,同時被綠之後,她受邀成爲他的現役女朋友。 一開始她以爲許亦潮也是憤懣不平,畢竟他傳聞中的前女友名單那麼長,沒有一個像系花那樣,是給他戴完綠帽子才分手的。 直到有一回,大少爺在酒吧喝多了,給席悅打電話讓她去接。 燈紅酒綠的長街,席悅怒氣衝衝地趕過去,然後看見許亦潮倚在門邊,和酒吧老闆討價還價,非要把人擱在吧檯上用來裝飾的月亮小夜燈買走。 “給個面子。”許亦潮脣角輕掀,笑容散漫帶着幾分薄醉,“我用來哄女朋友的。” 過了許久,席悅後知後覺,自己好像是被騙了。 - 許亦潮有一片璀璨的夜空,席悅本以爲自己只是其中一顆隨時會湮滅的星。 直到後來許亦潮告訴她,她是他處心積慮也想摘入懷中的月亮。
28.3萬字8 57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