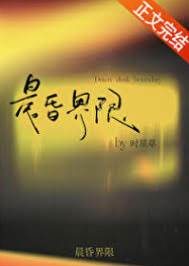《曾將愛意寄山海》 第48頁
復讀班在八月底就提前開了學,阿姨陪我去買了新的書包和文,寓意著換一個心,重新開始。
我在久違的收拾書包的時候,在書架上看到了一沓還沒有用過的本子。
由於我這一年多許久沒有用本子寫過東西,那些本子擺在書架上已經蒙了一層灰塵,就像我已經塵封的記憶。
那年有一個人匆匆跑出去買了厚厚一沓本子回來丟給我,說以後你的本子我都承包了。後來他連哄帶騙問我本子裡寫的是什麼,他明明有無數個機會打開看,也有無數個機會問我,可他一定要等到一個他覺得我能夠接的時候才問。
他看起來那麼自由散漫的人,可他的邊界,比誰都強。
在他的眼睛裡,我永遠看得見自己。
可是那樣熱烈真誠的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他。
時間是一道向前奔涌的洪流,失去聯繫,就會走散。
我進了教室報導,教室里卻不像我想像中那樣鬧哄哄的,所有人都安靜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提前拿著書本複習。
那一刻我才後知後覺到高考的迫。
所有人來到這裡,只是為了再給自己一個機會,而我是其中的一員。
我的位置仍然靠窗,我喜歡靠窗,也許是因為可以看著窗外發呆,也許是兩年前那次自由選座位,周嘉也給我指的位置就是靠窗。
我的同桌是個男同學,他開學第一天就帶了很厚一箱子書,老師還沒來,他已經在飛快刷著試卷。
我還沒有投到這種迫的氣氛中,在一片劍拔弩張的硝煙中,看起來像個呆頭鵝。
Advertisement
沒有繁瑣的自我介紹環節,也沒有活躍氣氛的調侃環節,全班到齊後,直奔主題進到了備戰高考的課業中。
我被的跟上節奏,在長時間沒有融人群的無所適從中,久違的有了一種熱沸騰的覺。
上課很累,因為老師講的東西很多我都不懂。
高二結束那個暑假學校安排的集中複習,我沒能參加,只能聽周嘉也說學得有多累,知識點講得有多深,題有多難,像是高一的那一整年都沒有學似的。
如今隔了一年,我獨自坐在這個陌生的教室里,才會到那時候周嘉也說的心。可是如今我的這種心,卻沒有人可以分。
下課的時候也沒有人打鬧,不是趴在桌子上休息養神就是在看書做題。晚自習也沒有人看小說玩手機,時間仿佛是流逝的金子,每一秒都很珍貴。
新學期剛開始的節奏就很湊,每天都像是打仗一樣,但是我居然沒有覺到疲憊,反而非常喜歡。
我很喜歡那種每個人都在專注於為了自己而拼命的熱,讓我覺到我的生命是波著的,而不是死氣沉沉。
我沒有經歷過正兒八經的高三,這一年才算是我的正式開始。
有時候脖子酸痛,仰頭著脖子時,會走神想著,去年的這個時候,周嘉也是不是也是這樣度過的呢。
他說的等我開學後就告訴我他填的是什麼學校,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高考結束後他去了什麼大學,我也不知道。
其實不是我們走散了,而是我把他弄丟了。他的朋友總是很多很多,也許早就忘了我吧。
Advertisement
那天是周末結束返校,復讀班同班的一個男生給了我一個信封。
他放我桌子上就走,沒跟我說一句話,可是看到信封的一瞬間,我的心臟連同著全的都在翻湧。
我拆開,裡面是一隻折好的千紙鶴。
翅膀上只寫了四個字,得償所願。
那個字跡陌生,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他的字,可是悉到只看一眼,我的眼眶就要不控制的流淚。
被我刻意躲避著的記憶,在一瞬間向我洶湧而來。
我的緒大多數平穩,現在已經能夠做到很失控,因為我在有意識的控制自己去避開能引起我緒波的事,可是有些閥門一旦,就會崩塌。
我飛快的跑過去拉住那個男同學,他回頭看到我滿臉的淚水,嚇了一跳,像見鬼了一樣。
我已經顧不上我這樣緒崩潰的樣子在他的眼裡是不是很像電視劇里的瘋子。
我只是拉著他的袖子,執著問他,「他有跟你說什麼嗎。」
「哦,有。」男同學平靜看著我,「他說如果你不追問就算了,但如果你問就給你帶句話。」
「……什麼?」
「對不起。」
暮夏的蟬鳴斷斷續續的嘲哳,如同拉長的警報,在耳朵里刺耳的放大。
從耳到大腦,每一寸都是刺痛,痛到手心冰涼。可是真正的痛覺,好像是來自心臟。
男同學看著我滿臉的眼淚,覺得莫名其妙,「你沒事吧?」
他一定是跟周嘉也認識,周嘉也的朋友總是很多很多,只要我還在學校,要打聽到我似乎並不難。
Advertisement
可他只托人捎給我的一句話,似乎預示著這個快要結束的暮夏,這次是真的要離開了。
我的眼淚越來越多,沒回答他的疑問,而是執著問他:「他去了哪個大學?」
「樓下的榮榜上有啊,凡是錄取了的名單都在上面。」
我轉就跑出教室,我有的緒失控,但是比這一年養病在家的任何時候都清醒。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晚安,蘇醫生
作為一名醫術精湛的外科醫生,卻被人用威脅用奇葩方式獻血救人?人救好了,卻被誣陷不遵守醫生職業操守,她名聲盡毀,‘病主’霸道的將她依在懷前:“嫁給我,一切醜聞,灰飛煙滅。”
35.7萬字8 19772 -
完結209 章

日日招惹,矜貴男主被勾纏失控了
【極限撩撥 心機撩人小妖精VS假禁欲真斯文敗類】因為一句未被承認的口頭婚約,南殊被安排代替南晴之以假亂真。南殊去了,勾的男人破了一整晚戒。過後,京圈傳出商家欲與南家聯姻,南家一時風光無限。等到南殊再次與男人見麵時,她一身純白衣裙,宛若純白茉莉不染塵埃。“你好。”她揚起唇角,笑容幹淨純粹,眼底卻勾著撩人的暗光。“你好。”盯著眼前柔軟細膩的指尖,商時嶼伸手回握,端方有禮。內心卻悄然升起一股獨占欲,眸色黑沉且壓抑。-商時嶼作為商家繼承人,左腕間常年帶著一串小葉紫檀,清冷淡漠,薄情寡欲。卻被乖巧幹淨的南殊撩動了心弦,但於情於理他都不該動心。於是他日日靜思己過,壓抑暗不見光的心思,然而一次意外卻叫他發現了以假亂真的真相。她騙了他!本以為是自己心思齷鹺,到頭來卻隻是她的一場算計。男人腕間的小葉紫檀頓時斷裂,滾落在地。-南殊做了商家少夫人後,男人腕間的小葉紫檀被套入了纖細的腳踝。男人單膝跪地,虔誠的吻著她。“商太太,今夜星光不及你,我縱你欲撩。”從此,做你心上月。
31.5萬字8.18 15202 -
完結156 章

掌心獨寵:錯撩權勢滔天的大佬
【雙潔 先婚後愛 頂級豪門大佬 男主病嬌 強取豪奪 甜寵 1V1】人倒黴,喝涼水都塞牙去中東出差,沈摘星不僅被男友綠了,還被困軍閥割據的酋拜,回不了國得知自己回敬渣男的那頂「綠帽」,是在酋拜權勢滔天的頂級富豪池驍“能不能幫我一次?”好歹她對他來說不算陌生人“求我?”看著傲睨自若的池驍一副不好招惹的模樣,沈摘星咬牙示弱:“……求你。”聞言,男人突然欺身過來,低頭唇瓣擦過她發絲來到耳邊,語氣冷嘲:“記得嗎?那天你也沒少求我,結果呢……喂、飽、就、跑。”為求庇護,她嫁給了池驍,酋拜允許男人娶四個老婆,沈摘星是他的第四個太太後來,宴會上,周父恭候貴賓,叮囑兒子:“現在隻有你表叔能救爸的公司,他這次是陪你表嬸回國探親,據說他半個身家轉移到中國,全放在你表嬸的名下,有900億美元。”周宇韜暗自腹誹,這個表叔怕不是個傻子,居然把錢全給了女人看著愈發嬌豔美麗的前女友沈摘星,周宇韜一臉呆滯周父嗬斥:“發什麼呆呢?還不叫人!”再後來,池驍舍棄酋拜的一切,準備入回中國籍好友勸他:“你想清楚,你可能會一無所有。”池驍隻是笑笑:“沒辦法,養的貓太霸道,不幹幹淨淨根本不讓碰。”
28.6萬字8 15484 -
完結578 章

億萬寵婚:神秘老公狠兇猛
他是A市帝王,縱橫商界,冷酷無情,卻唯獨寵她!“女人,我們的契約作廢,你得對我負責。”“吃虧的明明是我!”某宮少奸計得逞,將契約書痛快粉碎,“那我對你負責!讓你徹底坐實了宮夫人的頭銜了!”婚後,宮總更是花式寵妻!帶著她一路虐渣渣,揍渣女,把一路欺負她的人都給狠狠反殺回去。從此人人都知道,A市有個寵妻狂魔叫宮易川!
106.2萬字8.18 544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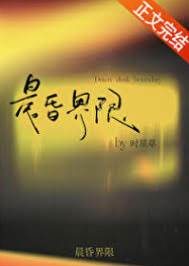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