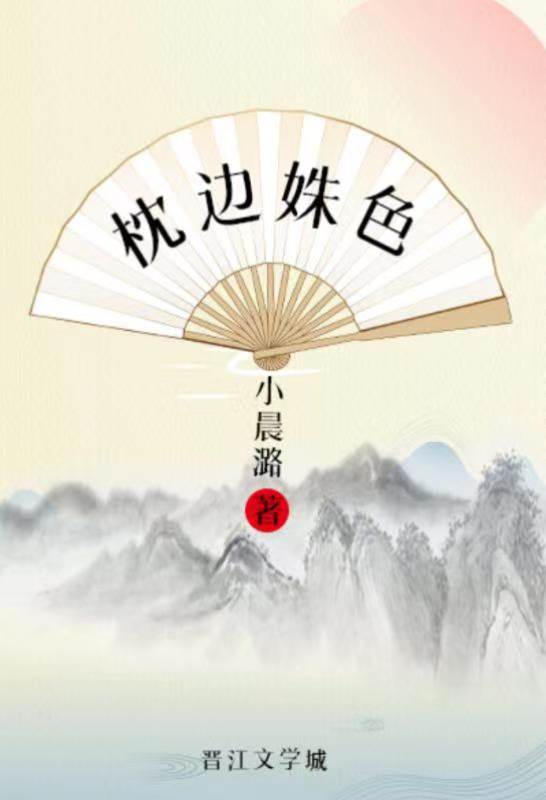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籠中雀她渣了瘋批皇帝》 第9卷 番外八:燕宮
東方既白。
有人抱住了他。
那人上溫,似母親一般將他抱在懷里,溫問道,“阿洐,你為何而哭啊?”
為何而哭?
緣由太多了。
多的數不清了。
這一雙手沾滿了,也染盡了罪惡。
他好似沒有做過什麼值得被人念的事。
他抹了淚笑道,“你怎麼會找到這里,我竟沒有聽見馬蹄的聲音。”
那人好一會兒才輕嘆一聲,“阿洐,你每日究竟在想些什麼?”
“沒什麼,都是些瑣事。”
輕聲勸道,“那便與我說說你心里的瑣事罷。”
他愀然無言,能說什麼呢,誤多年,也過了多年,什麼都開不了口了。
便哄道,“我們回去吧,很快就到燕國了。”
“阿姒啊,就到這里吧,不必再往前走了。”他笑著搖頭,輕輕撥開的手,“你帶著嬋兒和夏侯恭回長安罷。”
姜姒垂淚,“我和嬋兒不會丟下你。”
他凄然淚下,卻是笑言,“多謝你和嬋兒,多謝你們陪我這一程。”
輕輕著他微涼的臉,“過去的事,你該放下了......”
他憮然嘆息,“罪孽太深,放不下了。”
垂下淚來,“阿洐,我不怪你啊!”
總是這麼純良,他也一次次辜負了的純良。
他緩緩拔出劍來,“很多年前我便想,死在你懷里,定是很幸福的事罷。”
姜姒含淚看他,“都過去了。”
“阿姒,就在這里罷。”他將劍柄遞給,聲中含著乞求,“我很累,不想再醒過來了。”
姜姒潸然淚下,跪起來將他的整顆腦袋都攬在懷里,“嬋兒還在等你,跟我回去罷。”
他沒有回答,手里的長劍微微輕。
這日復一日的煎熬要熬得他燈枯油盡了,他累極了。
那人卻說,“我一直都你啊,你不知道嗎?”
Advertisement
他心中一嘆。
數次提過不。
不。
不。
不。
說過許鶴儀,過裴君,過伯嬴,唯獨不曾過他。
便是在建始十一年的張掖都不曾過。
是不的,所以才一次次殺他。
如今又說,怎麼會呢,的是伯嬴,嫁的也是伯嬴。眼下不過是要在他死前哄他罷了。
他做過那麼多錯事,又怎會再,他神思清明,卻又不忍破。
“多謝你。”他笑了起來,將劍柄塞的掌心,“我心里好許多。”
姜姒淚如雨下,“你總不信我,這麼多年了,還是不信......”
他笑,“信,信。”
如今他也不知該信什麼,又不該信什麼了。但也都沒什麼打了,哄哄他也是好的。
嘆了一聲,“誰又沒有錯呢!”
是啊,都有錯,沒有人清清白白。他有錯,也有錯,伯嬴也有錯,正是因了都有錯,才造就了今日的苦痛。
又問,“殿下還要帶我去曬太嗎?”
他信了。
這是抱出永巷地牢時說的話,還記得呢。
“那年仲秋的月真圓啊,我還想再吃一次張掖的辣羊和葡萄酒......”
他信了。
那個喜歡辣羊和葡萄酒的姜姒是過他的。
“建章宮不知還有沒有人守著,那里是我們大婚的地方......”
他信了。
大婚后的姜姒也是過他的。
若當真不,也許早在甘泉宮便將他剝皮揎草了。
他悵然一嘆,低低道,“阿姒,我很累了,想好好睡一覺。”
溫哄道,“那便好好睡一覺,等醒來我們回建章宮,好嗎?”
他應了。
他說,“好。”
有人他,自然好啊。
這一路穿過代國,終是到了燕國的大地。薊州的泥土散著雨后的清香,燕宮還是舊時的模樣。
Advertisement
天子的信使早先一步到了燕宮,要守宮的舊人清掃殿宇,好生侍奉。
許嬋和夏侯恭都是頭一回來燕國,一下馬車便歡笑著往宮中奔去。
姜姒扶他下了王青蓋車,守宮的舊人忙上前跪迎。
他們在燕國住過三年整,那三年啊。
時隔八年重回故都,他卻再不是那個意氣風發的燕王殿下了。
但他步子輕快起來,“阿姒,去建章宮。”
姜姒拉住他的手,笑道,“去建章宮。”
建章宮是他們當年的寢殿,那是他迎娶的地方。他的掌心是溫的荑,他心頭一燙,許多年前,他多想要與牽手走路。從前不能,如今就在邊。
他覺得疾病全消,一直在心頭的巨石被這掌心的荑陡地擊碎齏。
他們同住建章宮,姜姒與萬嬤嬤早晚侍奉著,他的氣一日比一日好起來,便是醫都連連點頭,說只需將養著便沒什麼大礙了。
對于“沒什麼大礙”,他的兒作此解釋,“醫的意思是,父親會長命百歲。”
他便笑,“父親能活到嬋兒出嫁便滿足了。”
許嬋臉一紅,“那嬋兒永遠不嫁,父親便永遠活著。”
他大笑起來,永遠活著豈不是要變妖怪。
姜姒亦是笑,“那要問夏侯小將軍肯不肯。”
許嬋臉愈發紅得似個桃,跺跺腳跑了出去。夏侯恭趕追了上來,“公主去哪兒?”
許嬋氣呼呼地錘了他,“誰要你跟來的!”
“難道公主不愿嫁我?”
“我才不嫁!我要陪著父親母親!”
夏侯恭奇怪,便問,“嫁我就不能陪父親母親了嗎?”
許嬋又錘他,“誰要嫁你!”
“反正公主去哪兒,我便去哪兒。”
“我若將來嫁給別人,你也跟去?”
夏侯恭凝眉咬牙,“跟!”
Advertisement
許嬋這才噗嗤一下笑了,“傻子!”
夏侯恭嘟囔了一句,“不傻就不跟來了。”
許嬋便也嘟囔了一句,“孤就喜歡傻子!”
到秋日,他能帶們去北郊草原了。他的左手雖拉不開弓,但看著宴安與夏侯恭狩獵也是好的。
夏侯恭為許嬋獵來赤狐和黃羊,小小的公主歡天喜地,與那小將軍一同在草原上策馬。
他臥在姜姒上,聽著兒歡笑的聲音,漸漸睡,心中安寧。
他會在晨間為畫眉,也試著為簪發,他笨手拙腳,并不嫌棄。
每日簪著玉梳,也會為他束發,為他寬,會哄他睡。
來年,燕宮的辛夷花開了。夭夭灼灼,狀如傘蓋。
送給他一只帛枕,枕邊繡著“洐”字,里塞滿了晾干的辛夷花。
他不釋手。
他說,“阿姒,我信。”
他沒說信什麼,姜姒也沒有問。
但大約什麼都知道,因為含笑點頭,“等你再好些,飲一杯葡萄酒罷。”
葡萄酒夜杯。
飲一杯酒,不醉不休。
再不必去王陵了,他們還要活好多年。
他,
他的阿姒。
他的嬋兒。
還有他的昭時。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40 章
云鬢亂
智斗皇后、反殺嫡母、懲罰情敵……她于他,是玩物,還是有情人?縱使她素手攪天下。 《焰落吻火》 尹落替嫡姐加入東宮,而太子周焰雙腿患疾,被廢已成定局。 未曾想到等待她的竟是來自自己與太子敵人的明槍暗箭:與愛慕周焰的年輕皇后斗智斗勇、險些被周臨報復、父親與嫡母為保尹家下毒陷害……尹落發現,光靠茍著……好像不行?
84.3萬字8 9901 -
完結316 章

一朵花開百花殺
花焰是個神教圣女,俗稱魔教妖女。 因為諸位前輩的斑斑劣跡,導致她尚未出家門就已經聲名狼藉。 天可憐見,她是個好人! 現在,她正待在號稱正道百年以來最強戰力,魔教聞之色變的“人間殺神”陸承殺陸少俠身邊,分分鐘擔心身份暴露被這個世仇碎尸萬段。
48.3萬字8 1929 -
完結152 章

病嬌瘋寵,暴君掐著她的腰叫乖乖
簡介: (重生,瘋批VS病嬌,互寵互撩)前世被渣男所欺,遲挽月死的淒慘。重活一世,渣男又假意示愛,遲挽月手握彎刀插入他的心髒:“好呀,本郡主挖開你的心來看看是不是真的。”綠茶陷害,遲挽月刀尖抵著她的臉,笑的陰戾:“你猜我能不能在人皮上刻出花來。”眾人瑟瑟發抖,本以為這樣的瘋子沒人治得了。卻瞧見她日日纏著那病嬌王爺,模樣又嬌又軟。“阿昭長得真好看,往後我們的孩子一定像阿昭一樣。”“阿昭若害羞,親親我,我便知道你也喜愛我了。”眾人皆看寧懷昭總一副傲嬌不領情的模樣。轉眼便瞧見他掐著小郡主的腰將人堵在逼仄的小巷子,從她的眼角親到唇角,眼眶發紅:“阿寶怎麽能對別人笑嗯?莫不是真讓本王打造一座金籠將你關起來,才肯乖乖的哄著本王?”
26.6萬字8.18 7365 -
完結3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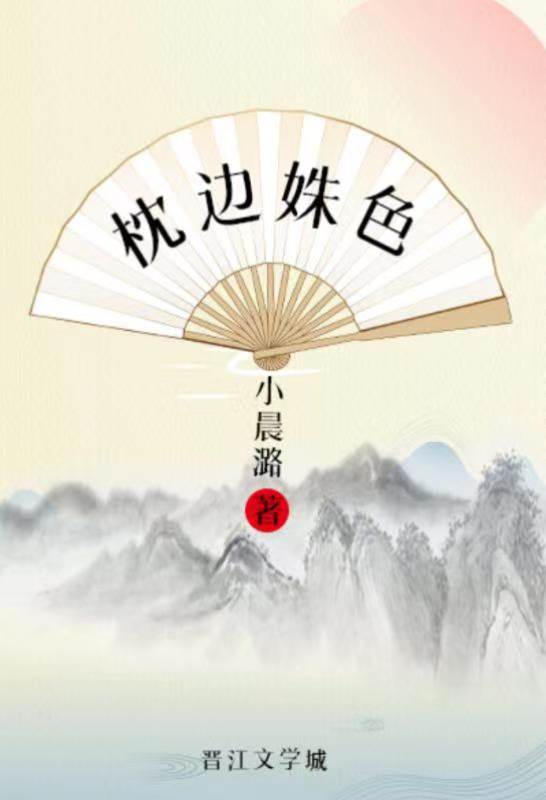
枕邊姝色(重生)
阮清川是蘇姝前世的夫君,疼她寵她,彌留之際還在爲她以後的生活做打算。 而蘇姝在他死後,終於明白這世間的艱辛困苦,體會到了他的真心。 得機遇重生歸來,卻正是她和阮清川相看的一年。她那時還看不上阮清川,嫌棄他悶,嫌棄他體弱多病……曾多次拒絕嫁給他。 再次相見。蘇姝看一眼阮清川,眼圈便紅了。 阮清川不動聲色地握緊垂在身側的右手,“我知你看不上我,亦不會強求……”一早就明白的事實,卻不死心。 蘇姝卻淚盈於睫:“是我要強求你。” 她只要一想到這一世會與阮清川擦肩而過,便什麼都顧不得了,伸手去拉他的衣袖,慌不擇言:“你願意娶我嗎?”又哽咽着保證:“我會學着乖巧懂事,不給你添麻煩……我新學了沏茶,新學了做糕點,以後會每日給你沏茶喝、給你做糕點吃。” 她急切的很,眸子澄澈又真誠。 阮清川的心突然就軟成一團,嗓音有些啞:“願意娶你的。” 娶你回來就是要捧在手心的,乖巧懂事不必,沏茶做糕點更是不必。
58.5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