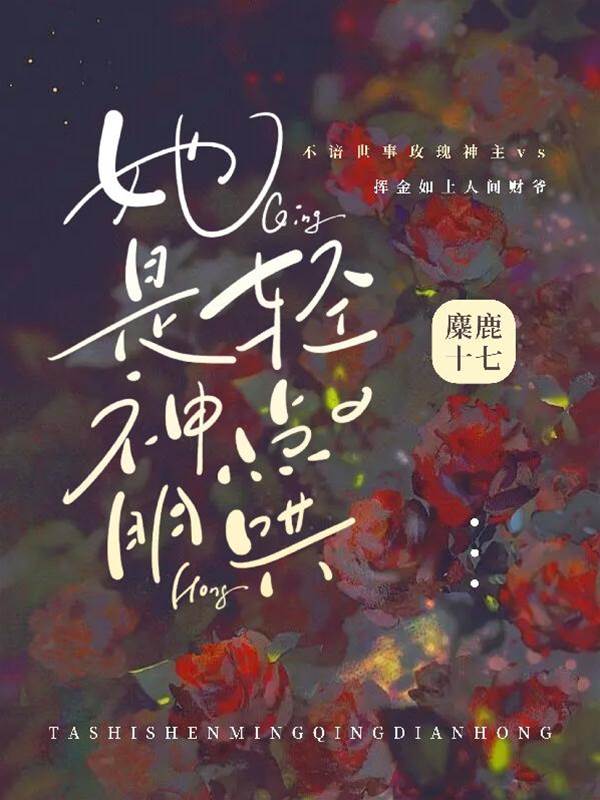《眾神肯為我走下神壇了?不稀罕了》 第1卷 第107章 不論什麼樣,都讓人厭煩
那是一個天朗氣清的午后。
正是午間休息時間,寬敞明亮的萬法宗外門學堂中,輕風微揚,紙張輕舞。
沅忱端坐首桌,漫不經心的翻閱手中書籍。
作為萬法宗宗主,修真界第一人,沅忱是不必到外門講堂傳授道法的。
今日會來,全因最為疼的小弟子祝鳶纏了他大半響,求得他答應來給外門弟子傳授修道之課。
又是一陣微風拂過,走廊的風鈴敲擊出清脆悅耳的樂聲。
一張揚肆意,著紅的,輕快的踏步而來,走到他面前,不經吩咐的便半跪而坐,手支著下頜,角微彎著看他。
“師尊,原來你在這兒啊,弟子終于找到您了。”雙眸清澈明亮,笑意盈盈,眸中溢滿了信任與依賴。
被這樣的目注視著,應是會讓人自在舒心,心放朗。
但沅忱的心緒是皺了皺眉。
他的視線終于從書本上移開了,看向面前容昳麗的司謠。
目不期然的與司謠的對上,眸中的溫與炙熱的清晰的傳遞了過來。
似被這樣毫不掩飾的目灼燒到了般,沅忱的指尖不一,清冷的眸也微微晃了晃,他不自覺移開目。
心中無端生出些許靜不下心的煩躁之意。
沅忱只當這是自己在面對不喜之人時會生出的反應,就沒有去深想。
“本尊平時教你的規矩哪去了?”他沒有理所說的話,只是聲線清冷的責問,語氣略微帶了些不悅。
雖不明顯,但只要是個人就能覺到。
司謠臉上輕快的笑一頓,眼中笑意漸退,變了失意,眼睫也垂了下來,掩飾住了真實緒。
慢慢坐直起,卻是不言不語。
整個人沉寂了下去,上也似布了一層灰。
Advertisement
見這般低落的模樣,沅忱的眉宇卻沒有舒展,心中亦沒有如愿的快意。
反而更令他煩躁了,只覺面前的司謠不論什麼樣,都讓人厭煩。
整個學堂沒有人再說話,氛圍有些低沉與抑。
“……師尊,弟子可以問您一個問題麼?”沉默了許久后,司謠才像是鼓起了勇氣般,重新看向沅忱,語氣認真的問。
沅忱沒有拒絕,也沒有應允,只默然的回看向。
司謠知道,這是默認讓問了,便開口道:“弟子想問,為何同為師尊門下的親傳弟子。”
“凌樾師兄和祝鳶小師妹他們在見您,以及和與您相時,可以親昵的不守規矩,只獨獨讓弟子守規矩?”
“你這是在質問本尊?”沅忱神瞬間轉冷。
“弟子不敢。”司謠斂眉低頭。
沅忱卻似對這低眉順眼的模樣更不滿極了,聲音更冷的道:“司謠,你該認清自己的份。”
“本尊能收你為徒已是仁至義盡,別妄圖得到其他什麼,也別妄圖和他們比。”
“你沒那個資格。”
司謠徹底的沉默下來了。
沒有再說話,只是那麼安靜的微低著頭坐在哪兒,整個人像是被打擊得失了智。
到這時,沅忱才知自己的話似乎說重了,可他不認為自己說錯了,只是往日只有清冷淡漠的眸中劃過一其他緒。
他微微啟了啟,像是想要說些什麼。
意識到自己的反應,他皺了皺眉,張開的重新合上,線抿一條直線。
像是再與誰較勁著什麼般。
“弟子知道了。”只是沒等他較勁出個什麼來,司謠重新開口了,只是聲音怎麼聽怎麼都有些懨懨。
無打采的起,像是被打擊到了般,拖著步子轉離開。
Advertisement
沅忱一頓,張口想住他。
只是不待他開口,司謠已經重新轉過了,姿卻站得筆直,臉上的緒也全部去。
不復方才的神懨懨和無打采的模樣,就好似方才的一切,并未影響到。
但沅忱看得出來,這是在強撐。
“弟子司謠,拜見師尊。”司謠規規矩矩的行禮。
禮數端正周全,挑不出一錯。
可莫名的,本該覺得滿意的沅忱,卻更覺得眼前這一幕越發不順眼起來。
“說吧。”他不耐的吩咐,隨后聲音冷淡的問:“找本尊何事?”
司謠卻像是被問住了般。
先是一頓,隨即愣愣的抬頭看他,眼中是摻雜著一難過的言又止,眼尾不自覺的氤氳出一抹淡紅。
整一副了天大委屈的難過模樣。
沅忱一頓,手指不自覺的捻了捻,像是想要去什麼般。
這抹緒來得快去得也快,快得他都沒法抓住。
心無端的燥,沅忱不耐的皺眉,這幅模樣看在外人眼中,倒像是不厭其擾想趕人的模樣。
“師尊忘了麼?”司謠像是認命般的嘆息,“三日前你說過,只要弟子破了你布下的制,便看一看弟子自創的劍招。”
經司謠這麼一提醒,沅忱這才想起來了。
大概是半月前,司謠就一直纏著他,說自己自創了一道很有用的劍招,想要讓他幫看看。
他一直都推拒了,只是司謠太有毅力了。
直到三日前,他被纏得不耐煩極了,便在周圍布下了數道制,承諾只要能在三日后突破這些制,并且找到他。
他便看上一看。
當時他也只是隨意一說,布下的制亦是沒太留手,以司謠此時的修為,是破不了他布下的制的。
他本以為司謠能看得出來,他是在故意為難,也以為會知難而退。
Advertisement
不想竟真的在三日后的現在,破了制找了過來。
直到這時沅忱才意識到了什麼。
他驀的朝司謠看去。
果然,司謠此時上靈力暴,很是不穩,一看就是了重傷被反噬的結果。
可是卻沒有去在意,反而是生怕錯過了什麼般,在破開制后第一時間找來了。
這人竟然因為想要讓他看一看自創的劍招,因為他的一句話,這般拼……
最終,沅忱終于答應了司謠的請求。
于次日展示給他看。
……
次日,司謠如愿的使出了自創的劍招。
當著莫名而來沈予行的面。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2110 章
豪門寵妻惹不起
實習生薑瓷在一次公司團建中,不小心把總裁陸禹東給睡了。她知道陸禹東心裏有個白月光,這次意外,不過是酒後的意亂情迷。因此她悄悄溜了,想當一切都沒有發生。然而沒想到,兩周後,她卻被陸禹東叫去,結婚。薑瓷嫁入了豪門,得到了陸家人的喜愛,但唯獨陸禹東,沒給過她一天好臉色...... …
204.9萬字8 63645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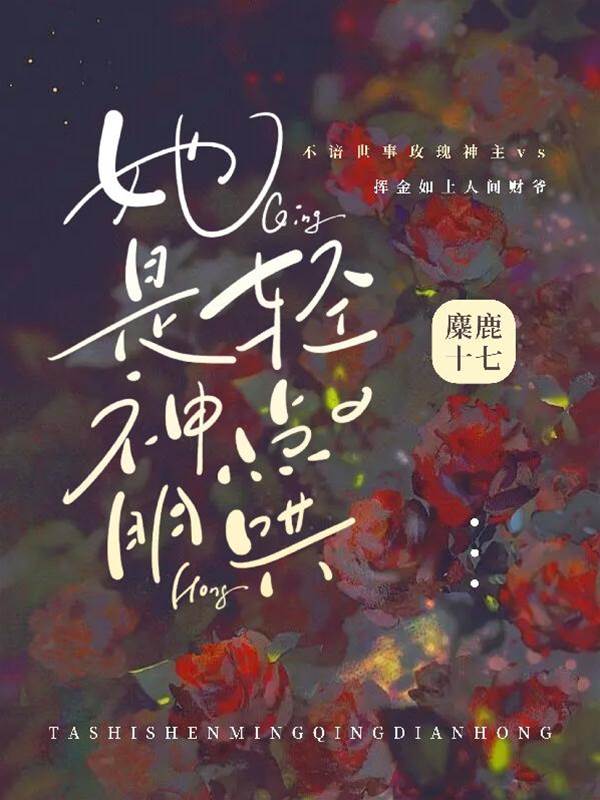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
完結490 章
重生,病嬌總裁哭求乖寶疼疼他
【嬌軟溫情大美人vs忠犬卑微偏執總裁】【雙向救贖+甜寵+男主卑微】 白墨清死后才得知商斯年愛她入骨,卻連接近她都不敢,在她被渣男害死后為她手刃仇人又殉情。 重生歸來,她只想抱好總裁老公大腿,手撕渣男,逆轉人生! 卻不曾想商斯年人前冷漠孤清霸道總裁,人后秒變粘人狂,一言不合就要親親,要抱抱, 白墨清表示還能怎麼辦,自己老公寵著唄! 人人都道,商斯年手段狠戾沒有人情味兒, 可是某一天有人無意間撞見,這個讓人聞風喪膽的大魔頭卻心甘情愿趴在床上挨打,還滿眼寵溺的一遍遍朝她道歉。 商斯年;“老婆,我最近發現了一個跪鍵盤不累的技巧!” 白墨清;“哦?那換氣球吧,不許跪破那種哦。” ...
86.2萬字7.83 11748 -
完結118 章

乖,別怕!病嬌反派致命撩寵女配
病嬌瘋批?甜寵?偏執?反派?女配穿書?雙潔?救贖?校園【不黑原女主】係統存在感低 【主角團全員覺醒,男主純情病嬌戀愛腦,青春熱血小甜餅】 溫柔痞帥病嬌忠犬美強慘X古靈精怪沙雕社牛少女 誰說搞笑女沒有愛情? 甜甜的戀愛這不就來了嗎! 洛冉冉穿進一本瑪麗蘇小說裏成了惡毒女配,還要完成係統崩壞前交代的【拯救虐文】任務,把BE扭轉成HE。 書裏的瘋批大反派少年黎塵,是手持佛珠卻滿手鮮血的小少爺。 洛冉冉努力完成任務,可過程中她居然被這個反派纏上了,大魔頭要親親要抱抱還化身撒嬌精,接吻怪…… 任務結束洛冉冉離開,二次穿書,她被少年抵在牆角,他笑的妖孽,捧起洛冉冉的臉說:“乖,別怕,不聽話要受到懲罰哦。” 我從來不信佛,不信神,我隻是你的信徒。——黎塵 — 黎塵:“冉冉,那你能不能喜歡我一下啊?” 洛冉冉:好吧,誰能拒絕一個又撩又可愛的大帥比呢? 黎塵:“冉冉,你親了我就得負責。” 洛冉冉:“……” 黎塵:“冉冉,鮮血染紅的玫瑰才好看對嗎?” 洛冉冉:“大哥別激動哈,咱們有話好好說!” 【甜寵救贖,曖昧拉扯,明目張膽偏愛寵溺。】 女主直球 男主戀愛腦 作者女主親媽
29.5萬字8.33 4470 -
連載756 章

破產後,上門老公成了我的金主
“想了你很久了......” 夜色裏,男人肆無忌憚的吻着我。 他是我的上門老公。 於是我這個金貴的千金小姐不得不讓他這個落魄小子入贅我們家,成爲我的老公。因爲心裏的不甘,我屢屢羞辱他,作踐他,對他非打即罵。可他從不生氣,儼然一副溫順賢良的模樣。而就在我慢慢喜歡上他時,他卻向我提出了離婚。昔日溫順賢良的男人忽然變得腹黑可怕。一朝變化,我家落魄了,他發達了,昔日被我踩在腳下的賢良老公搖身一變成了我的金主。
143.8萬字8.18 414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