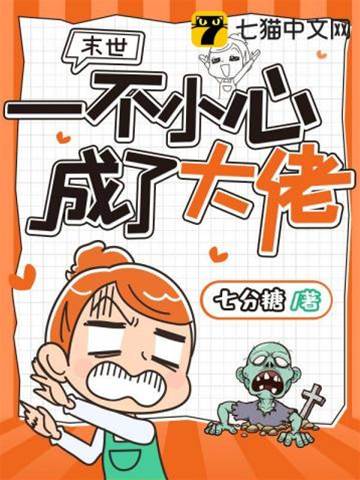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陸太太又鬨離婚了》 159 配不上陸家
午間,明。
一輛黑轎車停在別墅前,司機恭敬的打開車門,車裏的男人下了車,上臺階。
宛如歐式宮廷風格的別墅,豪華奢侈。金碧輝煌的大廳,鎏金拱門隨可見,富麗堂皇的水晶吊燈,巧繁複的銀飾品,以及價值連城的名家壁畫,無不彰顯出主人的品味與實力。
“霍先生。”傭們紛紛低下頭,井然有序站在旁邊。
男人走進客廳,隨手將西裝外套下來。立刻有一名傭上前,彎腰接過西裝,心翼翼掛好。
砰!
咚咚!
樓上突然傳來一陣響,霍名申仿佛沒有聽見,轉坐到沙發裏,將剛剛買回來的袋子打開,拿出裏麵的幾本書。
咚!
樓上又是一陣很大的靜,傭們個個垂著頭,沒人敢話。有人走到茶幾前,輕輕將一杯紅茶放下,然後又退到邊上。
沙發裏的男人雙疊,抬手解開襯衫的最上麵兩顆鈕扣,鎖骨微。
白骨瓷茶杯被男人修長的五指握住,顯得格外秀氣。午後暖下,輕抿口杯中的英式紅茶,整個心都得到極好的籍。
紅茶的濃香縈繞不散,霍名申挑了挑眉,似乎正在愜意的消磨時,直到樓上再度傳來一陣巨響。
砰砰砰—
稀裏嘩啦的鎖裂聲,比起剛剛有過之而無不及。霍名申勾了勾,眼底的神終於有了一波。
“霍先生。”
管家急匆匆跑下來,滿臉無奈的跑來求助,“姐又鬧起來了,誰也勸不住。”
“今鬧了幾次?”男人聲音低沉,狀似不經意的問道。
Advertisement
管家不敢瞞,如實回答:“早上鬧過一次,我這才吩咐人重新換了家飾品,可這麽快又……”
管家心裏雖急,但上也把握分寸,不該的話,絕不多一個字。男人放下茶杯,緩緩站起,抬腳走上樓梯。
見他上樓,管家才鬆口氣。
二樓走廊鋪著白地毯,羊絨地毯腳極佳。男人走到最中間的臥室門前,有兩名傭臉張的守在外麵,不敢進去又不敢離開。
男人站在臥室外,手將房門推開。傭們識相的往後退開,距離更遠些。
打開臥室門,裏麵線過於昏暗。深窗簾遮擋住外麵的,屋子裏沒有開燈,整個房間看起來森黑暗。順著開啟的房門,有走廊的線映,隻見原木的地板上一片狼藉。
床單被罩被丟的滿地都是,花瓶瓷也被摔的碎。梳妝臺自然也沒幸免,瓶瓶罐罐或砸或翻,總之就沒一件完整東西。
暗的窗簾前方,一位穿白長的子,五致。站在最暗的角落,但依舊無法掩蓋那張絕的容。
隻不過,此刻那位人,赤腳站在地板上,右腳已經被地上尖利的碎玻璃渣刺破,滲出鮮紅的跡。
紅跡一簇簇在地板中綻放,如同荊棘之地開出的麗花朵。霍名申看眼子流的右腳,慢慢朝走過去。
有傭人迅速送來醫藥箱,放下後又匆匆出去。
男人上前兩步,不知道手按下哪裏,隻聽‘嘩’一聲,剛還閉的窗簾自往兩邊拉開。昏暗的臥室,瞬間被從落地窗照進來的照亮。
Advertisement
明的太過刺眼,站在窗邊的子不抬起手,在眼前遮擋了下。等的眼睛適應這種亮時,男人也已經走到的麵前。
霍名申彎腰將子抱起來,轉而放到床邊。隨後他拎過醫藥箱,打開後找出一把醫用鑷子,蹲在床邊,抬起子的右腳。
坐在床邊的子沒有掙紮,垂落在臉頰邊的長發烏黑順。甚至都沒有掙紮,隻靜靜的坐著。
霍名申低頭看眼子流的腳,黑眸沉寂而平靜。他拿起鑷子,把刺子腳底的玻璃渣,一點點拔出。
傭人們一字排開,全都站在臥室門外,等待吩咐。
玻璃渣刺稚的,大概因為過分的碾,以至於刺的位置很深。碎玻璃與皮的分隔,帶來一陣鑽心的痛楚。
子閉了閉眼,垂放在床邊的五指驟然收。
“疼嗎?”男人的聲音低沉。
然而,回應他的,隻有空氣。
男人理傷口的作練,好像已經做過很多次。須臾,他把刺子腳底的碎玻璃全部拔出,接著消毒、包紮。
坐在床邊的子,始終一言不發,甚至在剛剛往傷口塗藥時,也沒有任何緒的變化。隻是原本應該完無瑕的,卻印著大大的傷口。
霍名申作不不慢,親手為子包紮好傷口。此時,他才慢慢的抬起臉,將目定格在的臉上。
他看著,漆黑視線如同黑夜中蟄伏的野狼,危險又冷酷,“知道你最大的錯誤是什麽嗎?”
子眉目清冷,安靜的仿佛空氣。
“明明可以離我遠點,偏要招惹我。誰住在城堡裏的公主,隻能和王子在一起?這輩子就算是綁,你也隻能綁在我邊,將來和我葬在一起。”
Advertisement
子蒼白的瓣勾了勾,開口的聲音有些沙啞,“霍名申,沒有人會和你葬在一起,你這樣的人,隻配孤獨終老。”
孤獨終老?
霍名申瞇了瞇眼,仰起頭在子的角輕吻下,繼而低笑聲,“放心,會有很多人來陪葬。不相信的話,你很快就能看到。”
聞言,子臉一變。
……
從午後明的,到夕垂落的晚霞,薑久始終保持一個作,呆呆坐在窗前的沙發裏。
樓一片幽靜,幾乎沒什麽靜。舒虹和薑然早已被趕走,那些聒噪的聲音也早已消失。可這大半過去,薑久整個人好像還沒緩過來,腦袋還是麻木的,無法思考。
孽種?
這兩個字仿佛被誰按了重複鍵,反複不停的在耳邊播放。薑久手捂住耳朵,但那陣刺耳的聲音,依舊無法被清除。
原來是薑萬明外麵的人生下的孩子,難怪舒虹對總是親熱不起來。其實在心裏,隻怕早已恨死薑久的存在。
嗬。
薑久低低笑了聲,眼眶酸酸的難。手了下眼角,沒有眼淚。
這些年父母偏心的理由,終於在這一刻得到答案。原來是個人人嫌棄的存在,不過是外婆心善才把養在邊。
想起外婆,薑久低頭拿出懷裏的照片。黑照片中,外婆慈的眉眼特別真實。好像還在笑,看著薑久道:久久別哭,有外婆疼你。
原來外婆一直都知道。
漸暗時,慈園燈火通明。陸謹行走進主樓,腳步微微有些急促。
“老三,你回來了。”玉坐在沙發裏,臉很難看,見到兒子回來才有好轉。
Advertisement
幾步走到沙發邊,陸謹行彎腰坐在母親邊,俊臉的神看不出喜怒。
剛剛一通電話,玉直接把兒子了回來。不久前樓發生的事,都一五一十了遍。尤其提到薑家,更是火冒三丈。
“我早就過,這個薑家不簡單啊,外麵生的私生竟然瞞著我們陸家。他們好大的膽子,這是把我們陸家當猴子耍嗎?”玉本來就看不上薑家,如今又鬧這麽一出,心裏更加厭棄鄙夷。
“媽,這件事和薑久無關。”陸謹行抿起。
“怎麽無關?”玉蹙眉,怒聲道:“要是薑家順理章的兒也就算了,沒想到竟然還是野人生的。我們陸家什麽門第?娶那種門戶的兒進門已經夠委屈了,現在竟然還要弄個孽種進門?不行,這絕對不行,我們陸家的三絕對不能是這樣的人!”
原本陸家和薑家的婚事,起因也是薑久下藥攀上陸家。如今得知薑久是三生的孩子,玉簡直嫌棄到極點。這樣出的人,本配不上的兒子!
陸謹行斂下眉,手了眉心。對於薑久的世,他也是半點都沒想到。
徹底黑下來,臥室沒有開燈。陸謹行推開臥室門進去時,隻在窗邊看到一抹模糊的影。
他掉西裝外套,一步步走到窗前。
白沙發裏,薑久雙手抱膝,整張臉都埋在膝蓋間。似乎聽到腳步聲,緩緩抬起頭,這才看到站在窗邊的男人。
四周線昏暗,陸謹行還是一眼看到掛在臉頰的淚痕。他不自覺抬起手,指尖輕在的眼角。
薑久下意識往後回避了下,陸謹行微微俯下,單手撐在沙發扶手邊。
男人高大的影籠罩下來,屬於他上的沉香氣息吸鼻間。薑久覺得眼睛又酸又,咬下,努力想要把眼淚回去。
四目相對,薑久看著男人的眼睛,所有的話都卡在嚨裏,半個字也不出來。
第二早上,薑久是在噩夢中驚醒過來的。睜開眼睛,邊的位置是空的。
陸謹行什麽時候離開的,不知道。
全綿綿沒什麽力氣,薑久頭昏腦漲,手了額頭,竟然生病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25 章
偏執薄爺又來偷心了
“再敢逃,我就毀了你!”“不逃不逃,我乖!” 薄煜城眼眸深邃,凝視著曾經試圖溜走的妖精,當即搞了兩本結婚證,“現在,如果你再敢非法逃離,我就用合法手段將你逮回來。” 女孩小雞啄米式點頭,薄爺自此寵妻成癮,護妻成魔。 但世間傳聞,薄太太癡傻愚笨、身世低賤、醜陋不堪,根本配不上薄爺的寵愛。 於是,全球的十億粉絲不高興了,“誰敢嗶嗶我們家女神?” 世界級的醫學研究院跳腳了,“誰眼瞎了看不上我們的繼承人?” 就連頂級豪門的時大少都震怒,“聽說有人敢瞧不起我們時家的千金?” 眾人問號臉,震驚地看著那被各大領域捧上神壇、身份尊貴的女孩。 薄爺旋即將老婆圈回懷裡,緋唇輕勾,“誰再敢惹我老婆……弄死算了。”
176.2萬字8 141276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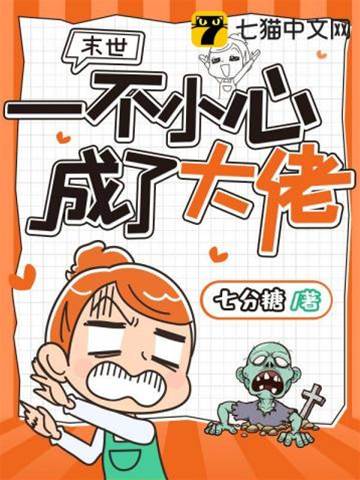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2925 章

影后的嘴開過光
「江小白的嘴,害人的鬼」 大符師江白研製靈運符時被炸死,一睜眼就成了十八線小明星江小白,意外喜提「咒術」 之能。 好的不靈壞的靈?影后的嘴大約是開過光! 娛樂圈一眾人瑟瑟發抖——「影后,求別開口」
524.2萬字8 15366 -
完結486 章

離婚後,虐她上癮的京圈大佬腰酸了
閃婚一年,唐軼婂得知她的婚姻,就是一場裴暮靳為救“白月光”精心策劃的騙局。徹底心死,她毅然決然的送去一份離婚協議書。離婚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裴總離異,唯獨他本人矢口否認,按照裴總的原話就是“我們隻是吵架而已”。直到後來,有人告訴他,“裴總,您前妻要結婚了,新郎不是您,您知道嗎?”裴暮靳找到唐軼婂一把抓住她的手,“聽說你要結婚了?”唐軼婂冷眼相待,“裴總,一個合格的前任,應該像死了一樣,而不是動不動就詐屍。”裴暮靳靠近,舉止親密,“是嗎?可我不但要詐屍,還要詐到你床上去,看看哪個不要命的東西敢和我搶女人。”
86.8萬字8 341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