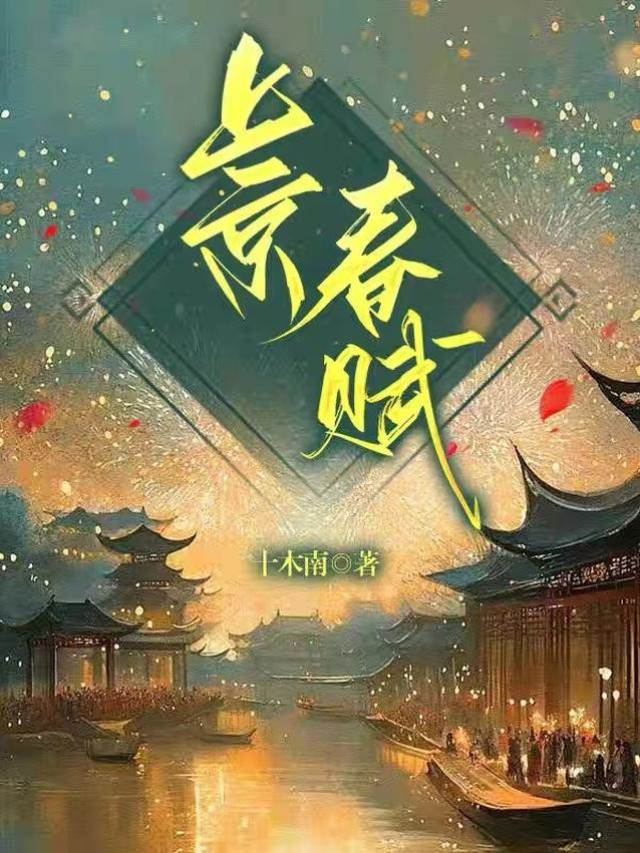《誤入春深》 第七章 查案
汶都晝夜溫差大,尤其冬至一過,日間還豔高照,天一暗風寒就直往骨裏鑽。
宋瑙在客房裏,門窗閉著,火盆裏的炭把屋子烤得滾熱,但仍有些冷。
眼下亥時剛過,正是宵夜的時間,豫懷稷食量大,一日要吃四餐,此刻在客棧一樓吃酒菜。約莫是七零八碎的吃食撐多了,宋瑙沒什麽胃口,就留在樓上烤火。豫懷稷回屋時,已蓋上三床被褥,癱在榻上昏昏睡。
豫懷稷走過去,拿話戲弄:“看夫人這樣,是有了?”
往日麵對他沒正經的調戲,宋瑙就算不敢直言怒斥,但總會報以批判的眼神,試圖傳達沉痛的忠告:你要控製你自己!
但這一次,顯然有氣無力,連個有氣勢的白眼都使不出來。
豫懷稷皺一皺眉,拿手背探向額頭,隻覺冰涼汗。他眼稍微向下,就見脖頸發紅,有大片細如牛的紅疹。
豫懷稷麵一沉,立馬將扶起來:“瑟瑟,先別睡,我們去看大夫。”
宋瑙迷迷糊糊地坐起,如同一隻提線人偶,任由豫懷稷給換上外,用裘裹得不風。起先以為是屋中炭火燒得太旺,容易人困乏,但此時也覺察出,可能是病了。
塌塌地被一番擺弄後,豫懷稷把抱出房間,吩咐客棧老板:“給我找個悉道兒、會趕車的,去你們這裏最好的醫館。”
老板不敢耽擱,迅速小廝到後院去把馬車趕來。他從祖上起就在汶都經營客棧,自小耳濡目染,深知豫懷稷是個不好惹的,再瞧見宋瑙一臉病態,生怕對方回頭會把這茬算在悅來客棧的飯菜頭上,便趁馬車還沒準備好,不住嘮叨他們家食材有多新鮮,後廚多幹淨雲雲。
Advertisement
豫懷稷聽得心煩,冷冷地丟去一句:“廢什麽話,我像是講道理的人嗎?”
老板瞬間噤聲,仿佛一把被命運掐住嚨,什麽都說不出了。
好在派來趕車的店小二沒他掌櫃這些心思,馬車駛得快而平穩,話也揀有用的說:“葉大夫是外鄉人,在這裏開醫館小一年,他經常為窮苦人家義診,醫也是公認的好。”
店小二眼見他們初來乍到,又是非富即貴的樣子,就把況多代幾句。
如此聽來,豫懷稷先為主地認為那應當是一位懸壺濟世的醫師,但他們到達茅舍時,天邊下起細夜雨,店小二冒雨去敲竹籬木欄,半刻後一男子出現在門後。
他一隻手拿一屜子,上頭陳放著曬幹的藥草,另一隻手解開欄桿。豫懷稷坐在馬車裏,自掀開的轎簾淡淡向外,恰與男人四目匯,眼睛驀地一跳。
宋瑙在昏沉中睜開眼,本想問他到了沒,卻在他異樣的神裏,改口問:“怎麽了嗎?”
豫懷稷溫和地搖一搖頭,取過紙傘放進手心:“外頭下雨了,我抱你過去。”
宋瑙充分展現出病患的自覺,咻地一張手,姿勢十分標準地方便他抱下車。
這是間布局簡單的醫館,院子用來晾曬草藥,看診的大夫葉鄂水三十來歲,麵骨瘦長,邊總是掛著淡笑,雙眼彎兩道黑的長線。
他把人請進屋中,再倒來兩杯茶,剛坐下要給宋瑙把脈,豫懷稷突然出聲:“等一下。”
豫懷稷出一絹帕子,蓋在宋瑙手腕上:“我夫人認生,出門在外也多有講究,不用別家的東西,請葉大夫理解。”
聞聲,宋瑙本要去拿茶喝的左手一滯,即便尚在病中,在他說鬼話的時候,腦子仍然相當靈,及時轉變方向,佯裝抬手去捋額前發。
Advertisement
葉鄂水笑笑:“外頭是不比自家萬事細致,講究點應該的。”他手搭帕替宋瑙診脈,又看一看的皮疹與舌苔,“有些水土不服,不要。”他拾起筆寫方子,“先吃幾服藥稍稍調節下,別貪食生冷,休養幾日便會痊愈。”
說完一些注意事項,他這兒有現的藥,就抓來幾包給到豫懷稷。
他原先提出為宋瑙針灸,排一排的寒,但豫懷稷以自家夫人暈針怕痛為由拒絕了。宋瑙自然夫唱婦隨,做出驚懼的模樣,瑟瑟往他後去。
他們配合無間,葉鄂水隻好作罷,他收下診金送兩人走出茅舍,在門口見到一清潤男子,手持白油紙傘,試圖叩門的手停在半空。
葉鄂水認出對方,笑道:“今兒個什麽日子,大半夜的我這寒舍這麽熱鬧,顧夫子找我?”
隻聽來人歎口氣,說明來意:“我是聽人說起,汲石巷的小乞丐六子幾日前風犯了,到葉大夫這兒看過,之後就不知去向,我有些放心不下,想來問一問您這邊可有什麽線索。”他略微拱手,“深夜叨擾,委實抱歉。”
他直起,這才看見與葉鄂水撤開一步遠的豫懷稷。
眼前的天穹大雨如注,傾盆砸下,似能力穿傘麵,葉鄂水讓開,請顧邑之去裏屋說話。一進一出間,豫懷稷與他錯而過,隔著黑的雨幕,顧邑之將紙傘微傾,遮住他上半子,擋開前方人的視線,他輕微朝豫懷稷行了一長揖。
他們像從沒見過,沒有停留談,仿佛一切該說的,都盡在這一揖禮中。
那夜,馬車返回客棧已是四更天,豫懷稷多給店小二一張銀票,差他想法子再去請一位大夫來。
店小二是機靈人,不該問的一句也沒問,有錢財收買,不多時就請來個年紀輕的。
Advertisement
他們來時雨勢極大,雖有打傘,但渾仍被澆了。
這種時候要找個肯出診的並非易事,豫懷稷便也不去挑剔這人資曆深淺,隻他確定了這方子沒問題,才按這個方子重新抓來新藥。
在等藥煎煮的時間裏,宋瑙想到豫懷稷在醫館的言行,知他繞這一大圈定是信不過葉鄂水,就問:“你認識那大夫?”
“沒見過。”豫懷稷坐到床邊,“但他上有我悉的氣息。”他沉著眼,緩慢地說,“是在死人堆裏滾過,滲進皮的腐腥氣。”
“一般人覺察不出來,也就我跟秋華這樣的,年行軍,殺人過多,對這味兒比較敏。”他道,“但葉鄂水是大夫,救死扶傷,理應是個有福報的,哪兒來這麽深的氣,我看這老東西還邪。不過我們來這兒是暗探,隻要他安分一點,我也不想平白找他麻煩。”
宋瑙聽他說著,點了點頭。一直明白善惡同生,如兩極,遇到哪一麵都不稀奇。
但有個詞,忍不住想糾正:“別的不說,可‘老東西’幾個字吧,用得可不大恰當。”
認真道:“畢竟他、他也沒比王爺大多。”
豫懷稷靜靜看須臾:“可以,膽了,敢拿我開涮了。”他語氣鬆散,但眸中帶笑,“以前王爺長王爺短的,現在倒好,同我說句話,不你呀你的,對我呼來喝去。”
宋瑙往他懷裏拱一拱,臉依舊泛白虛弱。親前有段時間過瘦了,婚後豫懷稷好不容易把養得圓潤些,可這一遭折騰,又有瘦回去的趨勢。
但的膽量卻有增無減,振振有詞地嘟囔:“自己家的相公,不要這麽見外嗎。”
豫懷稷把被頭拉高,蓋到宋瑙脖頸,食指搔一搔下,像逗黃八鬥一樣逗:“嗯,這話我聽。”針對適才的稱呼,他通舒暢地說,“以後都這麽喊,記住沒?”
Advertisement
宋瑙雖顯病態,但眼神晶晶亮,埋頭蹭一蹭他膛。
“不說話?”豫懷稷威脅,“不說我可親你了?”
宋瑙手捂上,囫圇道:“我生病了,不行的。”
豫懷稷奇怪:“又不做全套,親下怎麽了?”
宋瑙依舊倔強地拒絕,這麽拉鋸小鬧一會兒,後廚的藥已煮好,店小二在外輕輕叩門。
夜間的雨聲由強轉弱,而天幕越發暗沉,無一線。
大約是睡得遲,又或許是藥中有安神效果的原因,宋瑙一覺睡到次日午後。
稍微用點稀粥填一填肚子,半個時辰後再服下一劑藥,皮上的紅疹略見消退,但仍然頭暈力乏,吃什麽都犯惡心。雖說隻喝這兩劑藥,是沒那麽快會見好,但豫懷稷總不大安心。他給店小二一些跑路費,要他請個道行深的大夫來,言明葉鄂水除外。
“客就是指名請葉大夫,這幾天恐怕也不行了。”店小二接過銀兩,與他們說,“昨兒個夜裏,周縣令的夫人頭風病發作,疼了整宿,今早雨一停就去把葉大夫接進府裏,還不知何時會放回來呢。”
聽完,豫懷稷又向店小二盤問些汶都的況。得知周縣令已到不之年,人很胖,肚大如籮將近兩百斤,三年前才娶親,據說為人有點小頭,但總對百姓還不錯。
“三十又七才討到媳婦。”全篇聽下來,豫懷稷隻抓住這一點,發表評論,“真慘。”
宋瑙懷抱一隻湯婆子,無語地搖搖頭,認為的夫君真心奇怪,明明有諸多頭銜傍,任意拉出來一個都能吹上七天七夜,但他從不把這些當資本。唯獨已婚這一樁事上,他時常表現出莫名的優越,並對尚未婚配的譬如陸秋華,抑或是婚比他晚的,好比這周縣令,皆要一視同仁地奚落兩句。
宋瑙在百思不得其解中逐漸犯困,雙眼半合間,看見黃八鬥搖尾奔來,隨手拈了條牛幹喂給它。而它吃完也不走,似有常駐的意思,看得喜歡,便拿開湯婆子,把它換到懷裏揣著。
活的溫雖沒皿燙乎,但自有它起伏溫暖的生命力在,宋瑙很快就睡過去。
不得不說,葉鄂水為人或許有問題,但醫的確在水準之上,後來的大夫仍沿用他的方子,隻在裏麵添加幾味補氣的藥,宋瑙連吃幾天便好得差不多了。
豫懷稷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夜半時分,他趁宋瑙睡得正香,披起,係帶時門框嘎吱輕響,黃八鬥又躋進來。
往日它溜來跟豫懷稷搶媳婦,總會被男人用鞋尖挑出門外,但它是隻有名姓的狗,必然跟天下其他普通的狗不同,它越挫越勇,百折不撓。而這回豫懷稷沒趕它走,一手抱起它來,拿白布幹淨它四肢,然後輕輕放在宋瑙旁邊。
“這次便宜你了。”
豫懷稷拉開它後,指向它命子:“規矩點,管住你的爪子和舌頭,不然別怪我斷你子孫。”
黃八鬥嗚咽著想回後,滿眼的不可置信:你居然威嚇一隻狗?
豫懷稷向它冷笑:治的就是你這隻見起意的公狗。
最後他拍一下它的肚皮,這才躍窗而出。
深夜的長街靜謐無人,偶有更夫手敲竹梆子緩步前行,淺淡的甜香浮在夜空中。
豫懷稷去到顧邑之住,發現他不在家,隻留顧槐生一人在床榻睡。
他閑得無聊,拾顆小石子丟進去。小胖子不負他,完全沒有醒,似的在睡夢中反手摳一摳屁,翻個,拇指往口中一塞,邊嘬手邊打呼嚕。
豫懷稷角了,進到屋中。
在等待顧邑之的過程中,他給小胖子蓋了四次被子,用枕巾拭過五次口水,小徑上才傳來些細小的響聲。
他一閃飛至房頂,矮在黑漆漆的瓦片後,見顧邑之風塵仆仆地往家走。
他今日沒穿平常那件長衫,換了一茶褐布的,他推開院落走近時,月輝傾灑在四方小院,映出他長靴與擺上的泥漬。
顧邑之先去裏間看一眼兒子,而後退去隔壁,用火折子點起一盞舊油燈。
他在書架上取來一張汶都山脈的地形圖,用朱筆勾出幾條路線。他伏在案上,袖口沾的草灰蹭在圖紙邊緣。
燈芯燃盡前,一小隊穿衙役服的人進到他家,顧邑之將做過標記的地形圖至他們手中。
為首的頭子喪氣道:“顧夫子,我們按周大人說的,把葉鄂水家翻得底朝天,隻在幾牆發現點跡,沒室,也不見地窖有什麽,他家土都被咱們掘鬆了,現下人是在府裏扣著,到時扣不住放回去了,一準得察覺。”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01 章

農門醫妃:妖孽王爺纏上門
天師世家第八十八代嫡傳弟子阮綿綿因情而死,死後穿越到大秦朝的阮家村。睜開眼恨不得再死一次。親爹趕考杳無音訊,親娘裝包子自私自利,繼奶陰險狠毒害她性命,還有一窩子極品親戚虎視眈眈等著吃她的肉。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姐弟三個過得豬狗不如。屋漏偏逢連陰雨,前世手到擒來的法術時靈時不靈,還好法術不靈空間湊。阮綿綿拍案而起,趕走極品,調教親娘,教導姐弟,走向發財致富的康莊大道。可是誰來告訴為什麼她路越走越寬,肚子卻越走越大? !到底是哪個混蛋給她下了種?桃花朵朵開,一二三四五。謊話一個個,越來越離譜。俊美皇商溫柔地說:那一夜月黑風高,你我有了魚水之歡。妖孽皇子驕...
32.6萬字7.73 30934 -
連載1973 章

3歲小萌寶:神醫娘親,又跑啦!
“娘親,你兒子掉啦!”小奶包抱緊她的大腿,妖孽美男將她壁咚在墻上:“娘子,聽說你不滿意我的十八般武藝?想跑?”沈云舒扶著腰,“你來試試!”“那今晚娘子在上。”“滾!”她本是華夏鬼手神醫、傭兵界的活閻王,一朝穿越成不受寵的廢物二小姐。叔嬸不疼,兄妹刁難,對手算計,她手握異寶,醫術絕代,煉丹奇才,怕個毛!美男來..
177.8萬字8 17475 -
連載1305 章

和離后毒妃帶三寶顛覆你江山
虐渣+追妻+雙潔+萌寶新時代女博士穿成了草包丑女王妃。大婚當天即下堂,她一怒之下燒了王府。五年后,她華麗歸來,不僅貌美如花,身邊還多了三只可愛的小豆丁。從此,渣男渣女被王妃虐的體無完膚,渣王爺還被三個小家伙炸了王府。他見到第一個男娃時,怒道“盛念念,這是你和別人生的?”盛念念瞥他“你有意見?”夜無淵心梗,突然一個女娃娃頭探出頭來,奶兇奶兇的道“壞爹爹,不許欺負娘親,否則不跟你好了,哼!”另一個女娃娃也冒出頭來“不跟娘親認錯,就不理你了,哼哼。”夜無淵登時跪下了,“娘子,我錯了……
231.7萬字8.18 9007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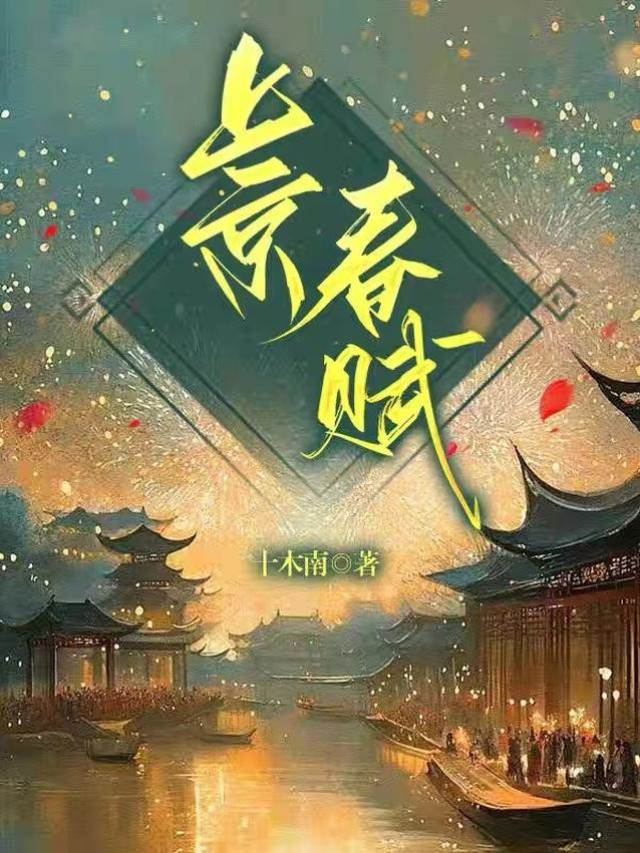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