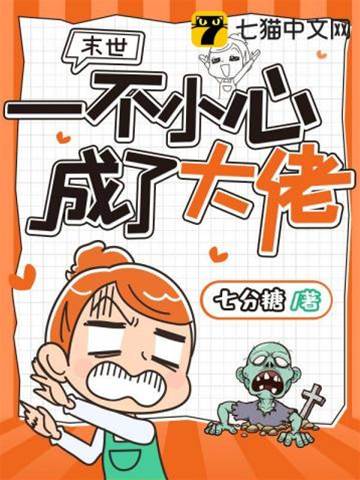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甜溺,厲爺低聲誘哄溫軟小乖寶》 第25章 屬於我的
厲瑾川詫異的看著眼前的人。
發現自己的自控力真是全方位下降了。
單憑這微紅的臉蛋,居然就能讓他呼吸急促。
“你洗過了?”他頭滾了一下。
江慕晚點了點頭,不自覺地將垂落在臉側的碎發勾於耳後。
“我覺得有些悶,所以到隔壁洗了。”
深吸了一口氣,發現耳邊隻是單純響起了他的聲音,就心神恍惚。
好奇怪,怎麽會這樣?
難道是因為今天剛住北山,所以有點張?
揣著手,心不在焉的越過男人,從浴室裏拿出吹風機,迅速把發尾吹幹,然後掀開被子把自己埋進了被窩。
厲瑾川眼神跟隨,接著拿起放在桌上吹風機。
一邊吹著頭,一邊不經意的掃過床上的小人兒。
漸漸的,他發現他高估了自己的自控力。
當他知道,湯是母親專程讓人送來的時候,就大概猜到了這個結果。
依母親的作風,應該不屑用什麽強烈的藥,所以藥膳是最好的選擇。
隻不過,現在藥膳的威力都已經那麽強了嗎?
是看著那個小山丘,他就已經有無數的想法在腦中滋生。
厲瑾川皺著眉堅持把頭發吹幹,他甚至不敢靠近床邊半步。
他沒有再看床上的人,將吹風機的線繞好,重新放回浴室的櫃子裏後,就義正言辭的落荒而逃了。
“你先睡吧,我去書房看會兒書。”他站在門邊解釋道。
江慕晚掖著被角輕聲的回了句,“嗯。”
走進書房,他歎了口氣,拿起書桌上的念珠,坐在椅子上,默念清心咒。
如此循環往複,直到心境逐漸平和,方才罷休。
Advertisement
“嗡…嗡。”
信息的震,似乎驚擾了男人的修行。
他抬了抬眼皮,打開手機。
“瑾川,你還在看書嗎?我…好像有些不舒服。”
不舒服?舒展的眉頭又逐漸深鎖,他著大步回到臥室。
臥室裏隻亮著一盞臺燈,盡管臺燈昏暗,他也沒有開燈,直接躺在側,抱著輕聲哄了哄。
“怎麽了?哪裏不舒服?”
江慕晚聽到他的聲音,撐著子靠在他懷裏。
“瑾川,我好像生病了。”
“生病了?”
“嗯,你快看看,我是不是發燒了?”
江慕晚拉過男人的手,將它放置於額頭上。
男人低頭苦笑,發現原來是自己想多了,他仔細對比了兩人的溫度,人的溫似乎比他的高一些,他皺了皺眉,低聲安著懷裏的人。
“沒事,不是發燒,就是有些熱,被子鬆鬆就好了,別蓋太多。”
“好,那…我不蓋了。”
二話不說把被子踢開。
眼就是擺已經被卷至大的睡,厲瑾川呼吸一窒,起掀起被子重新為蓋上,隨後扶著頭靠坐在床上。
“還是蓋一下吧。”厲瑾川咳嗽了兩聲,眼神有些不自在。
江慕晚抬起頭,乖乖在他的懷裏,撒般地問道。
“你一會兒,還要去書房看書嗎?”
靠著男人,隻覺得他上冰涼涼的,讓很舒服。
厲瑾川眸一暗,起的下,“你想讓我陪你?”
看著他,像是在思考。
半晌,搖了搖頭。
厲瑾川似乎已經預料到了,他輕聲一笑,了的發,“那就乖乖自己睡覺。”
Advertisement
江慕晚眨了眨眼,勾起手臂攬上他的脖子,蜻蜓點水般的覆上了他矜薄的。
的吻很青,帶著好,厲瑾川隨著的節奏,眼眸裏燃起了一異樣。
沒多久,到男人特殊的緒,江慕晚嚇得往後了,眼裏水霧繚繞。
“還想逃?”厲瑾川箍住的腰,將錮在懷中,再度吻上的,從溫到強勢,肆意索取。
男人不自的吻住了的耳墜,的側頸,然後從眉心到鼻尖,從耳墜到肩頸。
“寶貝。”他嗓音中帶著濃烈的。
江慕晚被吻得子發,隻能一言不發的抱著男人的背脊。
恍惚間,似乎還聽到有人在耳邊低,“我你,寶貝。”
……
次日,迷糊的從床上醒來。
江慕晚輕輕了子,覺全就像散架了一樣,尤其是從腰間溢出的酸痛,更是幾乎蔓延了全…
究竟是經曆了什麽非人的待遇啊,蒼天啊…
江慕晚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中。
“寶貝。”
直到後響起了男人特有的嗓音,昨晚的所有,才忽然一一在腦中掠過。
最後的記憶還是停留在淩晨。
厲瑾川的力…實在是太驚人了。
什麽人吶,鐵人嗎?都不用休息嗎?
吐槽之餘,江慕晚還是沒有忘記他的傷。
昨晚,那種程度的作,應該是高強度運了吧?他的,還好嗎?
扯了扯嗓子,發現自己已經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了。
“咳咳…你…你的…,還好…嗎?”
男人將抱得越發了,因為剛睡醒,說話時還帶著濃重的鼻音。
Advertisement
“我的沒事,你呢?有沒有覺得哪裏不舒服?”
聽到他說沒事,江慕晚鬆了口氣,拉著他的手,將它放在自己的腰上,語氣裏帶著嗔。
“腰好疼,好難。”
將人轉過來擁進懷裏,厲瑾川寬大的手掌在的腰上,耐心的按著,“都怪我,老公這就給你。”
腰間傳來他掌心的溫度,那酸痛也似乎減輕了不,著著,江慕晚竟舒服得差點睡著了。
可是再強的困意始終還是抵不住的侵擾。
安靜的臥室隨著“咕嚕…”一聲巨響,幾乎把半瞇著眼的兩人都給震醒了。
“了?”厲瑾川帶著笑意朝問道。
江慕晚紅著臉點了點頭。
心想,“忙活了一夜,能不嗎?”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25 章
偏執薄爺又來偷心了
“再敢逃,我就毀了你!”“不逃不逃,我乖!” 薄煜城眼眸深邃,凝視著曾經試圖溜走的妖精,當即搞了兩本結婚證,“現在,如果你再敢非法逃離,我就用合法手段將你逮回來。” 女孩小雞啄米式點頭,薄爺自此寵妻成癮,護妻成魔。 但世間傳聞,薄太太癡傻愚笨、身世低賤、醜陋不堪,根本配不上薄爺的寵愛。 於是,全球的十億粉絲不高興了,“誰敢嗶嗶我們家女神?” 世界級的醫學研究院跳腳了,“誰眼瞎了看不上我們的繼承人?” 就連頂級豪門的時大少都震怒,“聽說有人敢瞧不起我們時家的千金?” 眾人問號臉,震驚地看著那被各大領域捧上神壇、身份尊貴的女孩。 薄爺旋即將老婆圈回懷裡,緋唇輕勾,“誰再敢惹我老婆……弄死算了。”
176.2萬字8 141276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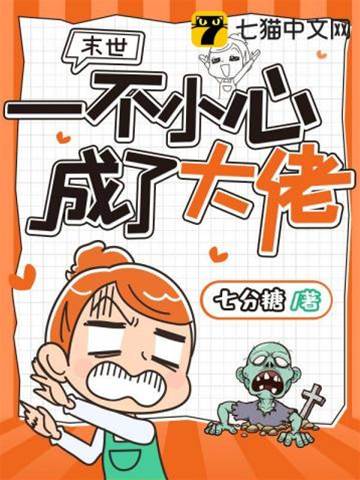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2925 章

影后的嘴開過光
「江小白的嘴,害人的鬼」 大符師江白研製靈運符時被炸死,一睜眼就成了十八線小明星江小白,意外喜提「咒術」 之能。 好的不靈壞的靈?影后的嘴大約是開過光! 娛樂圈一眾人瑟瑟發抖——「影后,求別開口」
524.2萬字8 15366 -
完結486 章

離婚後,虐她上癮的京圈大佬腰酸了
閃婚一年,唐軼婂得知她的婚姻,就是一場裴暮靳為救“白月光”精心策劃的騙局。徹底心死,她毅然決然的送去一份離婚協議書。離婚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裴總離異,唯獨他本人矢口否認,按照裴總的原話就是“我們隻是吵架而已”。直到後來,有人告訴他,“裴總,您前妻要結婚了,新郎不是您,您知道嗎?”裴暮靳找到唐軼婂一把抓住她的手,“聽說你要結婚了?”唐軼婂冷眼相待,“裴總,一個合格的前任,應該像死了一樣,而不是動不動就詐屍。”裴暮靳靠近,舉止親密,“是嗎?可我不但要詐屍,還要詐到你床上去,看看哪個不要命的東西敢和我搶女人。”
86.8萬字8 341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