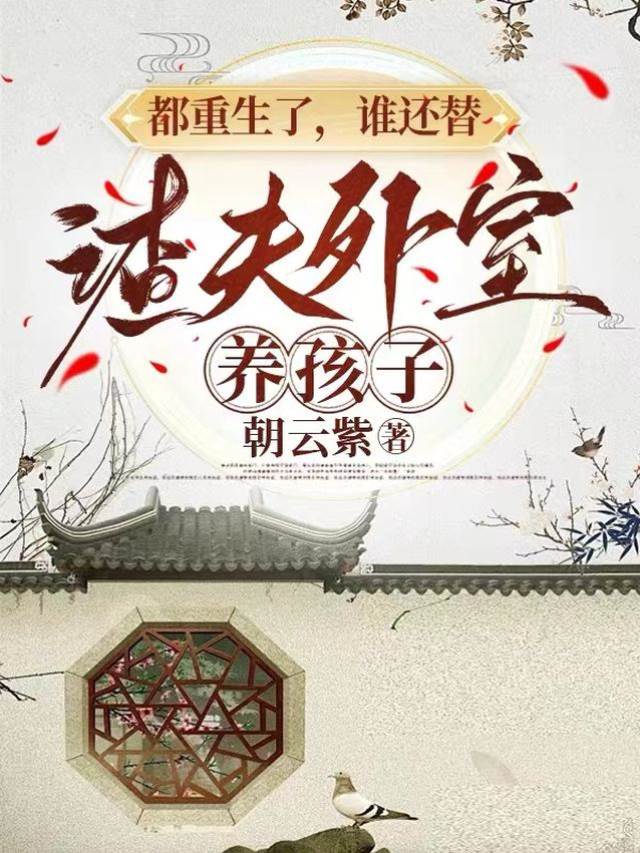《替身竟是本王自己》 第207頁
當初在東宮太子冷落,幾乎與打冷宮無異,這才咬咬牙自請侍奉皇后,倒是無心柳。
“妾省得。”阮月微道。
太子了的脊背:“辛苦你,大哥薨逝后母親越發易怒,孤知道你的難。但是將母親侍奉好,你便是幫了孤的大忙。”
“能為殿下分憂,妾便心滿意足了,”阮月微略帶委屈道,“殿下方才為何說那些話嚇唬妾?”
太子道:“孤就喜歡嚇唬你,一下你就……”咬著的耳朵說了句什麼,得阮月微用被子蒙住了臉。
方才太子危言聳聽嚇得不輕,忽然得知并未到這步田地,心弦不由一松,便又有心思想別的了。
“殿下,”仰起臉道,“今日你在宮宴上見到我蕭家表姊了麼?”
太子這才想起阮月微和蕭泠是姨表姊妹,心中一:“見到了。你們表姊幾年未見了?”
阮月微想了想道:“上回見大約是六七歲上,后來便再沒有京了。”
又佯裝好奇道:“我記得時生得很好,不知這些年變化大麼?”
太子暗暗一哂,知道是旁敲側擊在打聽蕭泠的容貌,若無其事道:“如今也生得不錯。”
頓了頓道:“畢竟是當初長兄看上的人,怎麼也不會差的。”
阮月微悶悶地“嗯”了一聲。
太子一笑,忽然將手進襟里:“但征戰沙場之人,當然沒有卿卿這樣水豆腐一般香的……”
Advertisement
阮月微嗔道:“殿下又取笑妾!”
將頭悶在被褥中,忿忿道:“殿下從哪里學來的這些渾話,為何不去輕薄你的心肝孫孺人……”
太子一哂:“還沒忘記那件事?你是太子妃,不過一個玩,當初孤只是故意氣你。”
他忽然靈一現:“明日阿耶請了你蕭家表姊去苑賞梅,你們表姊妹多年未見,你不如隨孤同去。”
蕭泠究竟是不是桓煊那外宅婦,他始終不能肯定。但阮月微慕桓煊,定會視那外宅婦為仇讎,對格外留意,即便時隔數年,說不定也能認出來。
阮月微遲疑道:“有外在,恐怕多有不便。”
太子道:“無妨,本來就是便宴,長姊也去的,何況蕭泠自也是子,你們在場倒還方便些。”
阮月微輕輕地“嗯”了一聲:“那便聽殿下的。”
也迫不及待想見見那蕭家表姊的真容——當初故太子對的示好視而不見,便是因為蕭泠,倒要看看究竟是什麼樣的子,能故太子那樣的人一見傾心。
聽太子的意思,蕭泠果然有幾分姿,就越發想一較高下。
“殿下說妾明日穿什麼的裳好?”問太子道。
太子道:“你看著辦吧,橫豎穿什麼都好看。”
阮月微掠了掠頭發:“殿下取笑妾。”
太子懶得敷衍,將寢除去:“卿卿這樣穿最好看。”
……
翌日,阮月微一早便起來梳妝,換了三四種發式、七八裳,方才收拾停當。太子侍來催了兩回,才拖著迤邐的裾款款出了房門。
Advertisement
上了馬車,阮月微向太子道:“殿下久等。”
太子笑道:“不久,等來個下凡的天仙,便是等上半日也值得。”
阮月微嗔了一聲,心中卻暗暗高興,不信這世上還有誰能將比下去。
今日的梅花宴設在蓬萊宮苑太池中的小島上。
島上遍植紅梅,梅林間建有飛檐雕欄的高閣,從閣上可以俯瞰彤云般的梅林與冰雪覆蓋的湖面,閣旁還附建有書齋與六角賞雪亭。
太子夫婦乘著步輦上島,沿著蜿蜒石徑往上。
阮月微一抬頭,便看見閣外的高臺上站著一個著紫綾面白狐裘的子。
阮月微起初以為那是大公主,隨即便發現一火狐裘的大公主正在那子旁與說話,便意識到了那人的份。
因是便宴,未穿武袍服,卻作子打扮,梳著驚鵠髻,只能依稀看見側影,卻莫名有些眼。
阮月微心頭一突,無端生出種不祥的預。
太子瞟了一眼,若無其事道:“長姊邊那位便是蕭泠。”
話音未落,那子若有所,轉過來,俯瞰石徑,阮月微便將的面貌看了個正著。
蕭泠也看到了太子夫婦,角噙著笑,遙遙地向兩人一揖。
這一笑比雪中紅梅還鮮明奪目,可阮月微此時已經顧不上的容貌了。
這正是恨的那張臉——那個贗品的臉。
只覺腦海中一片空白,難以置信地瞪大雙眼。
Advertisement
太子將神看在眼里,心往下一沉。
他握住阮月微的手,覺到手心冷黏膩,佯裝不明所以:“怎麼了?”
阮月微哆嗦,側過頭,在太子耳邊輕聲道:“殿下覺不覺得,蕭家表姊生得有些像一個人?”
太子道:“孤覺著有幾分像你。”
阮月微搖搖頭:“殿下可還記得三弟畜養的那個外宅婦?”
太子佯裝驚異:“你這麼一說,似乎是有幾分相似,可蕭泠怎會……”
阮月微亦是心如麻,當初趙清暉下手害那外宅婦是知的,若那子真是蕭泠,是如何死里逃生的?又知不知道趙清暉是為了才下手的?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81 章

奪嫡
他將她囚禁。背叛,滅族,辜負。她死于一場蓄謀已久的大火。燒到爆裂的肌膚,寸寸誅心的疼痛和撕心裂肺的呼喊,湮沒在寂寂深宮。重生歸來。她卻只記得秋季圍獵的初遇,和悲涼錐心的結果。人人避之不及的小霸王,她偏偏要去招惹。一箭鎖喉搶了最大的彩頭,虞翎…
45.9萬字8 106515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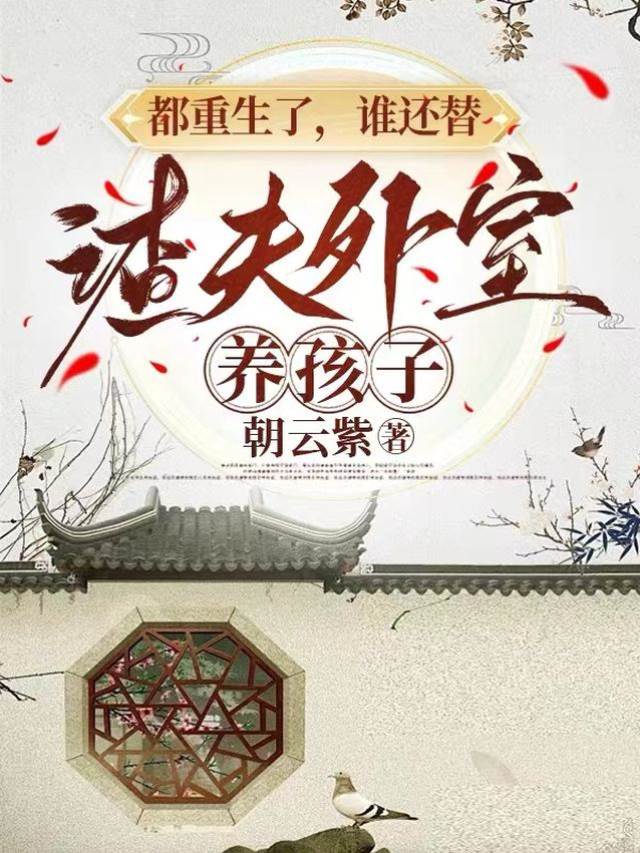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
完結222 章

霽月清歡
這日大雨滂沱,原本要送進尚書府的喜轎,拐了兩條街,送入了永熹伯府。 毫不知情的寧雪瀅,在喜燭的映照下,看清了自己的新婚夫君。 男子玉樹風逸、軒然霞舉,可一雙眼深邃如淵,叫人猜不透性情。 夜半雨勢連綿,寧雪瀅被推入喜帳,亂了青絲。 翌日醒來,寧雪瀅扭頭看向坐在牀畔整理衣襟的夫君,“三郎晨安。” 衛湛長指微頓,轉過眸來,“何來三郎?” 嫁錯人家,寧雪瀅驚愕茫然,可房都圓了,也沒了退婚的餘地。 所幸世子衛湛是個認賬的,在吃穿用度上不曾虧待她。 望着找上門憤憤不平的季家三郎,寧雪瀅嘆了聲“有緣無分”。 衛湛鳳眸微斂,夜裏沒有放過小妻子。 三月陽春,寧雪瀅南下省親,被季家三郎堵在客船上。 避無可避。 季三郎滿心不甘,“他……對你好嗎?” 寧雪瀅低眉避讓,“甚好,也祝郎君與夫人琴瑟和鳴。” 季三郎變了臉色,“哪有什麼夫人,不過是衛湛安排的棋子,早就捲鋪蓋跑了!雪瀅妹妹,你被騙了!” 寧雪瀅陷入僵局。 原來,所謂的姻緣錯,竟是一場蓄謀。 衛湛要的本就是她。
32.7萬字8.25 149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