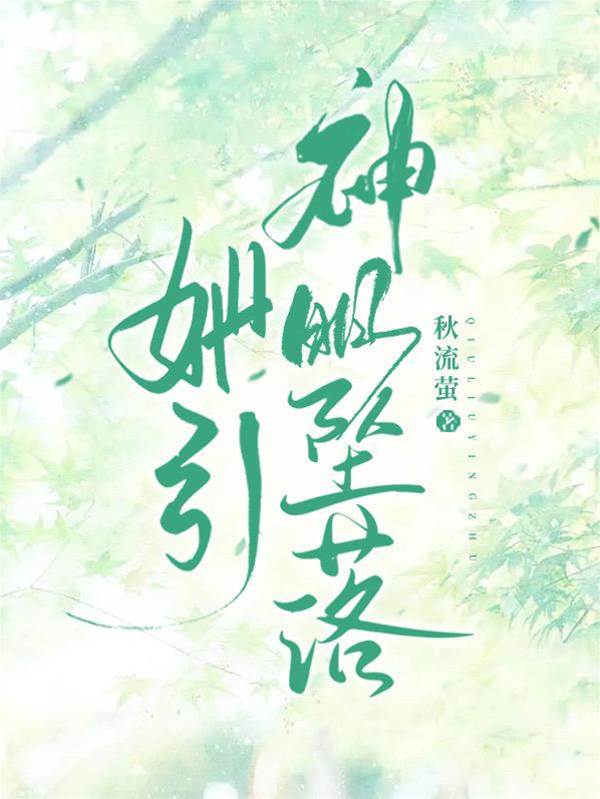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名門豪娶:大叔VS小妻》 第186章 242:婚禮(3)(11更)
陳霆的話一出,底下一片嘩然。
葉傾心震驚地轉頭看向景博淵,這事,他之前沒有跟過。
上次準備要結婚,他給了百分之十的集團份,沒同意,他也沒再勉強什麼,以為他已經歇了要給份的心思。
沒想到給來這麼一出。
「博淵……」
景博淵平靜又堅決地看向,說:「簽字。」
陳霆把文件需要簽字的那一頁呈現在葉傾心面前,同時遞過來一支拔了筆帽的簽字筆。
葉傾心搖頭。
嫁給他,不是為了他的財富。
承認,如果景博淵沒有財富作為基礎,或許不會像現在這樣,舉手投足都是功男人的魅力和吸引力,沒有能力在遇到困難時,輕易就出手解決,或許不會上他。
可是這並不代表要接他如此大的饋贈。
之有愧。
他給的,已經太多太多。
「心心。」景博淵捧住的臉,認認真真地盯著的眼睛,只說了兩個字,「簽字。」
不容拒絕的語氣,霸道又專制。
「我……不能……」葉傾心喃喃道。
景博淵不再說話,就這麼平靜地看著,他的眸波瀾不起,葉傾心拒絕的語氣卻漸漸下來。
葉傾心最終是簽了。
二十一歲的B大普通大學生,不僅一躍為博威集團老總夫人,更一躍為博威集團最大的東。
這是多人做夢都不敢想的。
雙重份,整個上流圈子,比尊貴比價高的,只怕找不出幾個。
葉傾心明顯能覺到落在上的目,變了很多。
景博淵此舉,分明是在替撐腰,他在用行告訴旁人,他究竟有多重視,他給了這麼高的份,亦是要讓那些在背地裏對葉傾心不敬、不把葉傾心放進眼裏的人,從此之後,不得不把葉傾心放進眼裏。
Advertisement
主婚人說著一些恭維的話,然後問景博淵:「不知道新郎還有沒有什麼想對新娘說的?」
景博淵接過話筒,深深地看向葉傾心,一字一句說:「十五年前一個暴雨夜,我開車途徑T城,一位母親抱著重病的六歲小孩攔下我的車,很慶幸,我當初救了那個小孩,十五年後的今天,很意外,我娶了當年順手一救的小姑娘……」
葉傾心怔怔地看著男人在燈下煜煜生輝的俊。
那些被塵封在記憶深的印象,約約在腦海浮現。
事的經過記得不是很清楚,只記得六歲那年,得過急闌尾炎,死去活來的那種痛,記憶猶新。
也知道是一位開車的叔叔救了,母親生前偶爾提起此事,都說好運氣,那晚要不是那位好心的叔叔答應開車送去醫院,並替繳了醫藥費和手費,可能早就沒了。
那時候,葉家的經濟條件本支撐不了一場手。
葉傾心眼眶發熱,曾經想過,倘若將來有一天,見到了當初救了的那位叔叔,一定要報答救命之恩。
卻從沒想過,的救命恩人,與日日同床共枕。
景博淵磁醇厚的聲音還在繼續,「心心,很抱歉,我沒能在你風雨飄搖的時里為你遮風擋雨,很憾,我沒能出現在你最需要我的時候,很幸運,當我出現,你恰好還需要我,有我在,以後什麼都不要怕。」
這大概是景博淵說的,最長的甜言語。
依然沒有什麼曖昧的字眼,可是,,藏在每一個字裏。
葉傾心聽完最後一句,恍然間想起來,六歲那年,躺在病床上,被護士推著進手室,很害怕,抓著邊人的袖,哭著說:「我害怕……」
Advertisement
那個人了的頭髮,聲音很好聽地說:「我在這,別怕。」
與景博淵相的近一年的時,他對說了很多次『我在這,別怕』。
尤其記得在蕭老夫人壽宴上,被一個陌生男人刁難那次,蕭家主驅離開,滿腔被辱的窘迫,是他摟著,替解圍,在耳邊說:「別怕。」
那一次,的心被這兩個簡單的字激起波瀾,很長的時間,這兩個字總是不經意在耳邊迴響。
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會對他這兩個字這麼有覺,現在似乎明白了,一切都是註定的。
他們的緣分,原來十五年前就已經註定了。
原來從十五年前,他就開始對好了。
母親忽然對他改變了態度,從反對到支持,並不停地說景博淵是個好人,也有這方面的原因吧。
那時小,記不得景博淵的長相,母親一定能認得出來。
葉傾心仰視著景博淵,笑著笑著,眼淚掉下來,滴落在前的婚紗上,暈了一層淺淺的痕。
失神間,景博淵為戴上戒指,親吻了的手背。
「心心,該你了。」竇薇兒手裏端著放戒指的托盤,見葉傾心發愣,小聲提醒。
葉傾心回神,拿起戒指,認真又虔誠地套在景博淵左手的無名指上。
婚戒是款式簡單的鉑金戒指,沒有一點花紋或者裝飾。
依舊是意外地合適,不一分,不松一毫。
「接下來,請新郎挑開新娘的頭紗……」主婚人聲音傳來。
景博淵抬手,輕輕掀起葉傾心的頭紗,孩傾國傾城的容緩緩展現,斜劉海婉約,頭上鑽石皇冠折著高貴典雅的芒,下面一陣尖歡呼。
葉傾心保持著注視景博淵的姿勢,似乎要將他刻在眼睛裏。
景博淵俯,一點一點,吻去臉頰的淚痕,最後,吻住的。
Advertisement
男人的尊貴強大,與孩的高貴,相得益彰。
下面又是一片歡呼。
接下來是證婚人致證婚詞,證婚人葉傾心認識,不過是在電視上見過。
切蛋糕,倒香檳,一切有條不紊。
到了拋手捧花的環節,現場所有未婚都躍躍試,竇薇兒沾了伴娘份的,和宋久兩人沖在最前面。
葉傾心背對著眾人,將手裏的捧花用力往後一拋。
所有人的眼睛盯著呈拋線飛下婚禮臺的手捧花,跟著往後移,竇薇兒個子高,捧花從頭頂越過的瞬間,高舉手臂輕輕一躍,穩穩接住。
剛落地還沒來得及站穩,側不知道誰用力推了一把,整個人不控制往右邊趔趄,一下子從T臺上掉下去,T臺不高,地上鋪了一層昂貴的地毯,摔是沒摔著,只是好巧不巧,以叩拜的姿勢摔在一個人的腳下。
整個大廳頓時陷一片死寂,繼而鬨堂一笑。
竇薇兒耳發熱,視線里,一雙緻的繡花布棉鞋在眼皮子底下,甚至,的額頭抵住了這雙鞋子的主人的。
「喲,這位伴娘也太可氣了,怎麼行這麼大禮?快起來吧。」聲音有點怪氣的。
與此同時,另一道溫和蒼老的聲音響起,「姑娘你沒事吧?」
聲音的主人雙手握住竇薇兒的手臂,用力托起。
竇薇兒咬著牙,藉著那雙手不大的力道起,抬頭看見一張壑縱橫的臉龐,面龐慈祥,渾濁的眼睛裏盛著關切與溫和。
竇薇兒看著陌生的老人家笑了笑,甜地道謝:「我沒事,謝謝。」
老夫人目落在竇薇兒脖子裏的項鏈上。
之前就注意到這個小姑娘脖子裏的項鏈,與當年瞳視若珍寶的項鏈一模一樣。
Advertisement
只是當年那項鏈被不珠寶商模仿,以假真的眼瞳項鏈見過不,每一次,都給帶來無盡的失。
這麼多年,心深一直潛藏著一期盼,明知希渺茫……
老夫人微微發抖,緩緩把手向竇薇兒脖子裏的項鏈。
竇薇兒低頭整理擺和摔得掉了好幾片花瓣的捧花,當察覺到老夫人的異樣,脖子裏的項鏈已經被人攥在手裏。
老夫人從兜里出老花鏡戴上,湊近竇薇兒的脖子,鑒寶似的細細端詳的項鏈。
竇薇兒覺得奇怪,張正要說什麼,策劃讓趕歸位,新人要離場換妝,伴郎伴娘需要襯托著新人再走一遍T臺。
「我還有事,您鬆手好嗎?」竇薇兒說著想從老夫人手裏奪回項鏈。
老夫人不知道看到了什麼,攥著項鏈的手忽然抖得厲害,眼淚從眼眶裏刷刷掉下來,另一隻手抓住竇薇兒的胳膊,力道大得似乎要掐斷竇薇兒的手臂。
「你是誰?你這項鏈哪兒來的?啊?」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4114 章
罪妻來襲:總裁很偏執
易瑾離的未婚妻車禍身亡,淩依然被判刑三年,熬過了三年最痛苦的時光,她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生活比在監獄中更加難捱,易瑾離沒想放過她,他用自己的方式折磨著她,在恨意的驅使下,兩個人糾纏不清,漸漸的產生了愛意,在她放下戒備,想要接受這份愛的時候,當年車禍的真相浮出水麵,殘酷的現實摧毀了她所有的愛。
361.9萬字8 2360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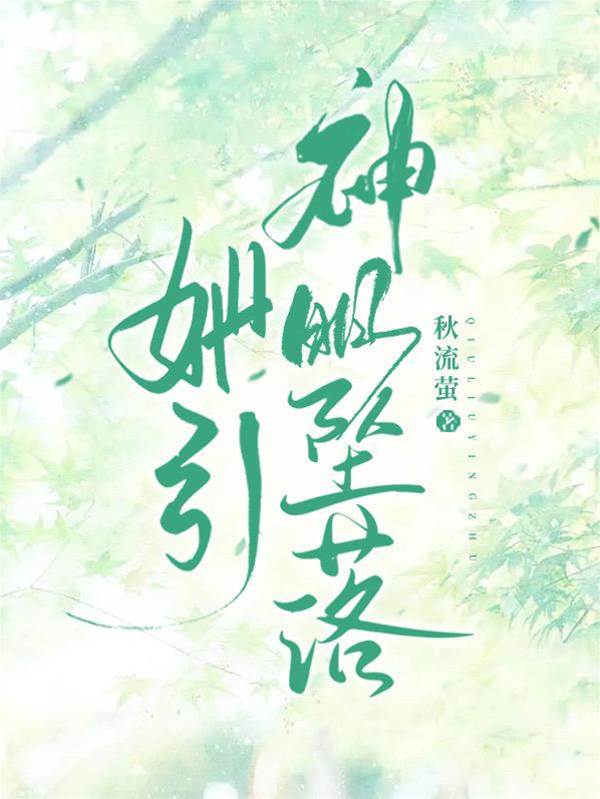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311 章

昨夜燈暖
三年前,蕭叢南被迫娶了傅燼如。人人都道,那一夜是傅燼如的手段。 於是他一氣之下遠走他鄉。傅燼如就那樣當了三年有名無實的蕭太太。 一夕鉅變,家道中落。揹負一身債務的傅燼如卻突然清醒。一廂情願的愛,低賤如野草。 在蕭叢南迴國之後。在人人都等着看她要如何巴結蕭叢南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 她卻乾脆利索的遞上了離婚協議書。
51.4萬字7.82 115868 -
完結120 章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小說簡介:宋家那個土里土氣又蠢又笨的真千金,忽然轉性了。變得嬌軟明艷惹人憐,回眸一笑百媚生。眾人酸溜溜:空有皮囊有啥用,不過是山里長大,
22.5萬字8.46 5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