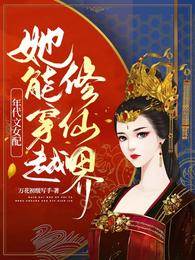《帶著倉庫回古代》 第一百五十二章 大教育家李咎
次日清晨,宋老三一大早就趕了來候著。
他從茶棚大爺那里討來一口涼水,就著涼水吃兩塊昨日吳書生給的白餅,直哽得嚨剌得發痛才勉強趕在吳書生開門前吃完。
吳書生已經梳洗完畢,穿得一青蓮的長衫,笑瞇瞇地喚他進屋子里說話:“我在金陵聽聞李先生萬般好,又聽說他為人風流,堪稱花叢浪子,尤其擅長調理人,邊有極為出的一班樂,這可是真的?”
宋老三嗆出一白餅沫兒來,嚇了吳書生和他隨從一跳。宋老三慌忙道歉說“得罪”,又趕拿出一條巾子拭桌椅。一邊桌子他一邊將腦子里那個有點傻愣的形象和吳書生說的“為人風流花叢浪子”拿來比較比較,怎麼都看不出有什麼共同之,怎會有這樣的傳聞?
隨從瞪起眼睛就要訓斥宋老三,吳書生按住了他,笑道:“怎麼?看起來,這是謠傳了?”
宋老三道:“確實是謠傳。小人的媳婦就在李園的‘木子鋪’上短工,一天總要在鋪里做上兩三個時辰的,聽聞潔自好得。就連侍婢,一天也不過能見著一面,這一面還是們和老爺說當天做了些什麼,花的多錢,掙的多錢,收的幾個單,并沒有其他話可敘。去年聽說咱們縣的舉人老爺還拿李老爺取笑,送了一車避火圖嘲笑他是個子!李老爺卻也不以為意,反勸舉人老爺惜福養云云。至于您說的樂……這說的是戲班吧?多老早前確實有打金陵來的一班樂,現正在李家戲園的‘宿舍’住著,離李園隔著一條路哩。”
“哦?這樣說起來,他又聰明,又會經營,仁慈善良,還不近,竟是個圣人了?”
Advertisement
宋老三道:“圣人不圣人的,咱們也不敢說。不過對咱們這樣的小民來說,能讓咱們不死的就是好人,能讓咱們吃飽飯的就是圣人,還能讓咱們家小孩兒讀書識字的,那是天上的星君下凡來了。”
“是這個道理。”吳書生聽出來本地人對李咎的敬意,按下了繼續打聽這些流言蜚語的想法,轉而問起其他青山縣的日常生活來。
宋老三已經自我覺醒了集榮譽,對青山縣的一切都非常驕傲,很樂意現給外地人看。并且據他的經驗,他無師自通地找準了能讓外地人驚嘆的點:整潔的道路、完容的濟貧、寬厚的待遇以及神奇的李老爺。
吳書生確實也如宋老三所料,邊聽邊表示贊嘆。他將宋老三的消息和昨晚與隨從們對出來的消息放在一起互相應證,心下的敬意又多了幾分。
宋老三最后說到的是教育:“對面就是李老爺的學塾,聽聞去上學不要束脩的,學校里還管一頓正飯。我們這的人天天等著盼著開門了好把娃娃送去,看樣子是快了。”
吳書生正在寫字兒記錄的手停下了:“不要束脩還管飯?這不是白給錢?為什麼?”
南方重視讀書,因而南人的科舉績一向比北人好,這是事實。但是再怎麼重視也該有個限度,免束脩還管飯就過頭了。
宋老三忙解釋說:“這個上學和舉人老爺的上學不一樣,李老爺是不教四書五經的。老爺說,世上能當的人畢竟,能治學的就更了,剩下的人考不上功名,又治不了學,則如何呢?像我們這樣的人家,供上一個娃的筆墨書本都不容易,倘若供出了秀才,也就妥當了。但是大多數時候連秀才也供不出來,倒白搭了這些年進去。”
Advertisement
吳書生點頭道:“這個不假。我自來游歷江南,最佩服的就是江南人頭腦靈活。科舉的路走不下去了,便轉行去做別的,再供養自家兄弟子侄繼續讀書。如此一代一代,總有人持家業,也總有人去念書,只要年景不差,總能慢慢地帶挈出一個大家族來。”
宋老三道:“正是這個理兒,我們家也是如此。李老爺這麼說了,原是讓能考試的娃兒們繼續讀書科舉,讓那些于科舉無的人來念雜學。學塾里頭的醫學已經招了些徒弟,一邊念書一邊行醫,如此既學了手藝,又有點進項不至于坐吃山空。向者聽聞去了好些人往北邊兒治天花,果真治好了,真是大功一件。學醫的旁邊聽說是什麼‘生’學,專門研究糧食蔬果的。咱們李老爺一直擔憂著他帶來的好種子退化減產,因此不敢對外說得。倘若那些學什麼‘生’的人將種子給治好了,也是大功一件。聽說還有教冶煉的,教蓋屋子修路的,還有教氣觀星的,分門別類,多了去了。”
吳書生道:“那我懂了,李先生的這個學校,原是給雜學旁收建的,這些門原也簡單,因此學一點皮就可以做一份事,給學塾帶點收賬,是以李先生不收束脩也不怕花錢。”
吳書生心里的一層憂稍微可以放下。他心里仍是認為四書五經才是正途,其他都是偏門左道。偏偏科舉太難,獨木橋太難走,多得是讀了三四十年的書都只是個聲秀才的人,哪能和那些學了一年手藝就能出去掙錢的雜學比?如果有人大規模地教那些雜學,必有短視的父母不教兒子好生讀書,倘或將好好的小孩兒們帶壞了,豈不是要和國家朝廷搶奪人才?
Advertisement
李咎自己避開了這個問題,明言只收沒辦法走科舉的,吳書生姑且認為他真的只是做慈善,并沒有別的想法。
宋老三道:“正是如此呢!還有更奇的。李先生收學生,不拘束男,男娃娃都可以報名,只分開上學罷,但是教的東西是一樣的。除了不拘束別,也不拘束年紀,那些五六十歲上的人,也可以趁著農忙的間隙來上學。聽說今年冬天就要開第一‘農閑’班了。李園幾位上了年紀的老媽媽老爹爹都會讀書看報的,說起來誰不羨慕?今年如果年好,到了那時候,我和我媳婦也想去報名學一學。”
吳書生對此卻不認可,但看宋老三眉飛舞的,顯見十分期待,他也就不說自己的真實意思了,問道:“那……你們縣的縣學也樂意李先生這麼折騰?”
“李先生說了,小孩兒到了上學的年紀,都先學經義。凡年滿六歲、九歲、十二歲時,各組織他們參加全縣城所有娃兒們的考試,考完后績好,能走科舉的,就去縣學讀書。績不好的,想拼一拼科舉也由著他們去拼,只有不想拼的或者家里實在窮困的,才可去李園學塾念書。為了讓孩子們都有出息,李先生買得一塊三百畝的地送給縣學,地里產出的錢銀糧食都給縣學。若有那學得好、品好卻不起束脩的,就用這筆錢幫他們束脩。老爺您說,誰不樂意看到這樣的折騰呢?都是大好事啊!”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161 章
女配一心修仙
穿越之後,裴如昔發現自己拿到白蓮花女配的劇本,專門和女主作對,還和女主搶男人那種。她想:這是修仙文,在修仙文修仙纔是正經事!鬥女主?搶男人?不好意思,女配一心修仙,目標直指飛升。
41.3萬字8 7545 -
完結73 章

我在豪門當咸魚
社畜姜知言,過勞死後穿越了。 現在放在她面前的是一份協議。 月薪十萬,合約三年,結束後還能拿到一套價值五百萬的房子和一百萬現金。 條件是……假結婚? “姜小姐,在結婚期間你不能干涉我的任何事,這些在合約上都已經列出來,如果有意見……” “沒有!沒有!” 望著面前的頂尖高富帥,姜知言很是上道地表示,“三年後我一定自動滾蛋。” “三年內,您有緋聞我替您澄清,您帶愛人回家我就是掃地阿姨,您要有孩子我把他當親生的照顧!” 望著一臉高興的薑知言,郁南衍把後半句“還可以再談”咽了回去。 他以為給自己找了個擋箭牌,實際上…… 郁南衍加班到十二點時,姜知言追劇到凌晨再睡到中午。 郁南衍連軸出差時,姜知言吃著空運過來的新鮮水果躺在花園吊椅上擼他的貓和狗。 郁南衍被底下蠢員工氣到腦疼時,姜知言和小姐妹拿著第一排的票看相聲,笑到肚子疼。 郁南衍:…… 姜知言:感謝組織感謝老闆,給我這個當鹹魚的機會!
31.4萬字8.18 20432 -
完結852 章

穿越之繼妻不好當
蘇惜竹因為地府工作人員馬虎大意帶著記憶穿越到安南侯府三小姐身上。本以為是躺贏,可惜出嫁前內有姐妹為了自身利益爭奪,外有各家貴女爭鋒,好在蘇惜竹聰明,活的很滋潤。可惜到了婚嫁的年紀卻因為各方面的算計被嫁給自己堂姐夫做繼室,從侯府嫡女到公府繼室…
229.6萬字8 32630 -
完結49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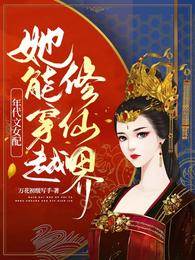
年代文女配她能穿越修仙界
(女主無cp年代修仙異能虐渣女配逆襲) 風婉清被堂姐陷害,家族放棄被迫下鄉當知青。 一次溺水后,她發現自己每晚能去一個神奇的地方,那裏人人追求仙道,到處都是飛天遁地的修行者,於是白天還是干農活都沒啥力氣的嬌弱女知青,夜晚卻是拳打妖獸,腳踢魔修的暴躁女仙。 若干年後,她那個奇奇怪怪勵志吃遍修仙界的師妹在聽聞她另一個世界的遭遇后,猛的一拍腦袋: 「我就說,你這個名字咋那麼耳熟,原來你是我穿越前看的年代文里的炮灰女配呀?你那個堂姐就是女主,難怪你鬥不過她」 此時已是修仙界元嬰道君早就報完仇的風婉清嗤笑一聲。 就她,女主? 想到早就被生活磨平稜角,丈夫又癱瘓的風綺,看來這女主當的還真不咋滴。
87.3萬字8 220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