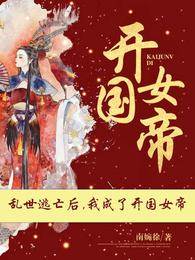《皇后的白月光另有其人》 第47章 第四十七章
國舅爺這邊懊惱地候在門外, 他很想問問雁回傷得重不重,那藥膏到底管不管用。
思來想去,國舅爺趁著雁回抹藥的空檔去客棧大堂尋了星河,讓星河將吃食端去給雁回, 他自個兒便又要出去走一趟。
又到了那診堂, 這鎮上的診堂自然是比不得京都的,這個時辰診堂就沒了什麼人, 忙碌一日的大夫坐在案邊敲算盤算著一日的利潤, 見國舅爺抬步往里走, 便抬眸出一個笑意相迎。
大夫記得國舅爺, 在這邊陲小鎮上, 國舅爺的風姿實在深人心, 一看便知曉是大家大戶。
“爺。”大夫停下打算盤的手, 問道:“那藥膏用得如何如今還需要點什麼”
國舅爺隨意應了, 目在診堂胡一梭巡, 問道:“可有磨傷用的藥膏”
“有。”大夫起要去找藥膏:“是哪磨傷了”
國舅爺有些于開口。
大夫并沒看出國舅爺的窘迫介紹道:“這不同部位用的藥膏是不一樣的, 弱的地方藥溫和, 稍微糙些的地方藥便猛一些。”
國舅爺愣了下,想到雁回用那用以鎮定腳傷的藥敷敷那,便有些急了, 急口:“大側。”
這回換大夫愣了一愣, 看著國舅爺這反應, 沉思了一瞬隨后笑意盈盈地去到診堂一矮柜,拉開木屜取出一瓶碧小瓷罐到了國舅爺手上,曖昧地看著眼前形高大的國舅爺道:“這藥便可,爺非這鎮上人不知,這條街左拐往巷子里行百步有一鋪戶, 那屠夫新娶的娘子便常常來我這買藥,買的就是這個,說是每每下不得床了往腫脹抹一抹,不肖一會兒便能消腫止痛,聽說這藥宮城里的妃子都用呢”
Advertisement
國舅爺出似懂非懂的神:“你在說什麼”
大夫出年輕人浮躁心火旺,都是過來人,我都懂的神。
國舅爺把藥罐往大夫上一攘:“不是這個,我買正常的鎮定舒緩藥膏。”
大夫擔心一個沒拿穩就將藥罐摔了,忙忙接過:“這藥最為溫和,爺不妨買回去讓夫人試試。”
國舅爺聽見夫人二字,一時微怔。
是了,這些天國舅爺一直覺得有什麼橫在了他與雁回之間。他一直未想明白,之前礙于份倫理,現下既然已為倫理跪了天地,他卻總是覺有一個難以名狀的東西擋了他與雁回,讓他們難以更進一步。
彼此深,卻好像又了什麼。
譬如為雁回腳傷敷藥,以前他不能是因為戒律清規條條框框,現在他不能,是因為發乎于止乎于禮。
經大夫無意一句,國舅爺醍醐灌頂終于想明白了,他了一個可以名正言順為雁回上藥的份。
那廂大夫還在推銷他這藥,這廂,想明白的國舅爺頓覺神清氣爽。
“行了。”國舅爺止了大夫的喋喋不休,道:“只是上有了傷,拿尋常藥便可。”
國舅爺都這般解釋了,大夫這才后知后覺自己誤會了什麼,忙連連致歉,去取了藥膏來。
國舅爺給了銀子,取了藥膏要走時,目不慎落在那碧小藥罐上。
大夫又道:“爺,不妨將這藥也帶著,總會用的上的。”
“用不上。”國舅爺斂了目。
大夫有些驚愕,上下打量國舅爺,似乎覺得國舅爺怎麼看也不是像患疾的樣子,然后他道:“我這里也有壯”
“我需要壯你在放屁。”國舅爺想了想又道:“你懂個屁”
雖說皇后遇刺消息已經傳開,宗人府已經在擬雁回后事。皇后新喪,雁回便也不是以往束縛的雁回了,是雁回,卻再不能頂著這個姓名生活。從前的瓜葛與再也無關,至親至信之人更加不能有聯系,雁回自由了也沒有家了。
Advertisement
國舅爺想給一個家。
在這之前,國舅爺不會有別的肖想。
所以這碧小藥罐他用不上。
國舅爺帶著藥膏回到客棧,這客棧是鎮上生意最好的,一樓大堂客人絡繹不絕。國舅爺回去時,廚房才恰好做好了星河要端給雁回的晚膳。
“我來。”國舅爺接過托盤,打發了星河便往雁回房間去。
他叩了叩門。
雁回已經涂抹好了藥,方才朝著門扉喚了兩聲,見國舅爺不見是想下樓尋國舅爺與星河的,轉念想到若是自己再不顧腳傷,恐惹怒了國舅,再者也不想拖累行程,于是乖乖地留在房里等著他們回來。
擔心藥膏會沾在上,雁回穿回了自己之前的那套素白勁裝,剛換過裳,便聞叩門聲。
門扉上印出國舅爺的形。
“阿回。”那人輕輕喚。
“進來便是。”
話音落下,屋燭火搖曳兩息,國舅爺這才推門進來。
雁回見國舅爺將托盤放在了圓案上,將飯菜和木箸好生擺好在案上,這才道:“了吧,快吃。”
雁回應了聲,從榻上起,想踱兩步往圓案坐下。
國舅爺“誒”了聲。
雁回看著他。
國舅爺是想來攙著自己的,但修長的手指在空中輕輕抓了一下又收回了,他撓了撓腦袋道:“阿回,這事本來得從長計議的,但現在看來刻不容緩。”
雁回心里一驚,不知發生了什麼。
國舅爺著:“父母之命妁之言,再加之三書六禮、四聘五金、八抬大轎、十里紅妝、十二版這算明正娶。也有互換定信相約長相廝守,這算私定終。”
雁回約猜到了國舅爺要說什麼,腔里的那顆心不控制地跳起來。
Advertisement
國舅爺道:“我想攙著你從榻邊到這案邊用膳,也想替你上藥”說到這里,國舅爺中滾了滾,嗓音有些啞卻是十分認真與炙熱:“阿回,我想問問你介不介意咱倆先私定了終。”
雁回抿著,垂眸蓋過眸中的緋紅。
國舅爺有些慌了:“當然,你若是不愿也沒關系,是我唐突了”
“沒有唐突。”雁回再抬眸,因著眼眶里蓄著淚看上去格外人,堅定道:“沈辭,與我私定終吧。”
“好誒,你莫哭。”國舅爺有些手足無措,他往上了,沒到什麼可以算作定信的件,但看著雁回撲簌簌落淚,又心疼地手去面上的眼淚。
雁回到面上溫熱的,抓住國舅爺的手腕,將臉龐置于他掌心:“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這是在皇家寺廟求的第二簽。
住持對說,娘娘若覺得茫然困不妨求上天給予啟示,我佛慈悲當會為娘娘授道解。
于是跪在金裝的佛像前,虔誠發問。
神明在上,信心有困懇求神明指示,信這一生還能與后院那人再見相認嗎
神明道,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亦知,后來國舅爺也去了,便藏在寺中菩提樹后,看著國舅爺纏著住持將求的簽看了又看,又說什麼帝后同心其利斷金。
國舅爺亦反應了過來,他忙道:“是我不好,沒能早些明白你的心意,阿回,你莫生氣。”
“我沈辭對天發誓,此生定不負雁回,若違此言不得好死。”
雁回聽見死字有些不安地皺了皺眉。
這點反應落了國舅爺眼中,他又改口道:“若違此言,我便出家為僧,青燈古佛孤獨終老。”
Advertisement
“我一窮二白,只能將自己的命贈予我家阿回,做這私定終的定信,今后我沈辭任憑阿回調遣,還阿回莫要嫌棄。”說完他平雁回微蹙的眉,復又莊重道:“禮”
雁回被國舅爺逗樂了。
國舅爺看了眼飯菜,這才展開雙臂:“飯菜快涼了,阿回,來,我牽你到案邊用膳。”
雁回輕輕點點頭。
手覆上國舅爺遞來的手心,腳下剛走一步。
國舅爺“嘖”了聲。
雁回看著他,后者道:“牽你不行,這腳還得落了地。”
隨后,偏過頭認真地看著雁回,眸中純粹并無:“阿回,你若不介意,我抱著你過去用膳吧。”
雁回低下頭,“嗯。”
話音剛下,落一個溫暖的懷抱。
二人皆是一愣,香溫玉抱在懷,念了無數個日夜的面龐近在咫尺。
雁回慢慢地手摟著國舅爺脖頸,未纏嚴實的袖順著白皙的手臂下,出那點守宮砂。
國舅爺深吸一口氣,忽然覺得自己的外甥真好。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87 章
腹黑毒女神醫相公
冬暖故坐著黑道第一家族的第一把交椅,沒想過她會死在她隻手撐起的勢力中.也罷,前世過得太累,既得重活一世,今生,她只求歲月靜好.可,今生就算她變成一個啞巴,竟還是有人見不得她安寧.既然如此,就別怨她出手無情,誰死誰活,幹她何事?只是,這座庭院實在沒有安寧,換一處吧.彼時,正值皇上爲羿王世子選親,帝都內所有官家適齡女兒紛紛稱病,只求自己不被皇上挑中.只因,沒有人願意嫁給一個身殘病弱還不能行人事的男人守活寡,就算他是世子爺.彼時,冬暖故淺笑吟吟地走出來,寫道:"我嫁."喜堂之上,拜堂之前,他當著衆賓客的面扯下她頭上的喜帕,面無表情道:"這樣,你依然願嫁?"冬暖故看著由人攙扶著的他,再看他空蕩蕩的右邊袖管,不驚不詫,只微微一笑,拉過他的左手,在他左手手心寫下,"爲何不願?"他將喜帕重新蓋回她頭上,淡淡道:"好,繼續."*世人只知她是相府見不得光的私生女,卻不知她是連太醫院都求之不得的"毒蛇之女".世人只知他是身殘體弱的羿王府世子,卻不知他是連王上都禮讓三分的神醫"詭公子".*冬暖故: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欺他辱他者,我必讓你們體會
149.1萬字8.18 75123 -
完結139 章

錦衣之下
雨點打得她頭頂上的蕉葉叮咚作響,甚是好聽,胖貓蹲她肩膀上瞇著眼聽。 雨滴順著蕉葉淌入她的衣袖…… 她仰頭看向陸繹移到自己頭頂的青竹油布傘, 心中不禁有點感動,這位錦衣衛大人總算有點人情味了。 “這貓怕水,淋了雨,怪招人心疼的。” 陸繹淡淡道。 胖貓哀怨地將陸繹望著,深以為然。 “……” 今夏訕訕把貓抱下來,用衣袖替它抹了抹尾巴尖上的水珠子, 把貓放他懷中去,忍不住憋屈道, “大人,您就不覺得我也挺招人心疼的麼?” 他沒理她,接著往前行去。 傘仍遮著她,而他自己半邊衣衫卻被雨點打濕。
42.9萬字8 12926 -
完結690 章

穿越后被迫登基
一朝穿越,葉朔成了大周朝的九皇子。母親是最得寵的貴妃,外祖父是手握重兵的鎮國公,他剛出生就一躍成為了最熱門的皇位爭奪者前三,風頭直逼太子。最關鍵的是,母親同樣有奪嫡之念。寵妃+兵權+正直壯年的皇帝,這配置一看就是要完,更何況,他前面還有八個…
106.4萬字8 8694 -
完結181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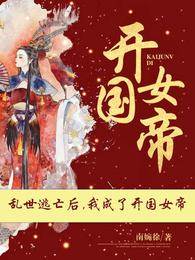
亂世逃亡后,我成了開國女帝
◣女強+權謀+亂世+爭霸◥有CP!開局即逃亡,亂世女諸侯。女主與眾梟雄們掰手腕,群雄逐鹿天下。女主不會嫁人,只會‘娶’!拒絕戀愛腦!看女主能否平定亂世,開創不世霸業!女企業家林知皇穿越大濟朝,發現此處正值亂世,禮樂崩壞,世家當道,天子政權不穩,就連文字也未統一,四處叛亂,諸王征戰,百姓民不聊生。女主剛穿越到此處,還未適應此處的落后,亂民便沖擊城池了!不想死的她被迫逃亡,開
238萬字8.18 16115 -
完結323 章

醫妃仵作鬧翻天
她出身中醫世家,一朝穿越,卻成了侯門棄女…… 從此走上了不一樣的道路。 她聞香識藥,一手銀針,技驚四座,剔骨剖腹怒斥庸醫,讓蠅營狗茍大白天下。 玉手纖纖判生死,櫻桃小嘴斷是非,誓讓魑魅魍魎無處遁形…… “姑娘?何藥可治相思疾?” 某男賴在醫館問道。 秦艽撥出剖尸刀,“一刀便可!王爺要不要醫?” 某男一把奪下剖尸刀,丟在一邊,“還有一種辦法可治!只要你該嫁給我就行。” 秦艽瞪著他魅惑的臉龐,身子一軟……
58.4萬字8 688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