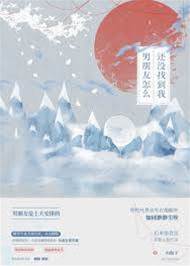《春風也曾笑我》 260.昏迷
向恒來過這里后的幾天,我神都還算可以,唯一的不好便是特別依賴沈世林,比以往更加依賴,以前喂飯穿服這些事,還可以讓仆人代勞,可慢慢地,仆人們稍微靠近一點,我就發瘋,砸東西,以前偶爾砸一下,而現在是歇斯底里的砸著,上午砸一次,下午砸一次,仆人心疲憊,沈世林也被我的狀況弄得心疲憊,公司和國外的上市公司都很忙,他并不能每天陪著我。
他下班后,看到一地碎片,看到我在墻角,仆人們束手無措狼狽的模樣,看了我許久,最終才朝墻角的我走過來,我小心翼翼看向他,他將我面前一些碎片全部撿起放進一旁的垃圾桶,看到我赤著腳的腳趾頭上有鮮流了出來,他看了許久,嘆了一口氣,隨即朝我出手,說了一句:“過來。”
我看了他一眼,他再次說了一句:“過來。”
我才緩慢靠近了他,將手放他手心,他將我從地下抱了起來,對我聲說:“脾氣不可以這樣暴躁,知道嗎”
我靠在他懷中,訥訥看向滿地的碎片,他抱著我出來后,便對門口站著的仆人說:“把房間打掃一下。”
仆人聽了,立即低著頭說了一聲:“是。”
沈世林將我抱出房間后,便將我腳趾頭上的碎瓷片取出來,他取的非常小心翼翼,可坐在一旁的我,早已經眼淚泛濫,不斷著腳趾頭不準他,他態度很強,握住我腳,本不容我彈,便拿著鑷子一點一點取出來,取了大約一個小時,碎瓷片理干凈后,他將我傷口的跡用棉花球和酒洗干凈,理好后,才放下一切工。
付博一直在后面耐心的等候著,仆人將所用的藥水和酒收起來后,沈世林問仆人我是否吃飯了,仆人聽后,在一旁說:“紀小姐今天砸了一天,也鬧了一天,本沒有吃什麼,我們都靠近不了。”
Advertisement
沈世林眼眸暗了暗,問:“也就是到現在還什麼都沒有吃,是嗎”
仆人說:“紀小姐”
“我不想聽你關于不吃飯的任何理由與借口,我讓你們來照顧,你們的責任自然是怎樣照顧,而不是現在一點東西都沒有用。”
仆人悶著不說話,沈世林沒有皺說:“如果還有下次,自己領了工資離開。”
之后沈世林喂我吃了晚飯,大約是白天都沒有進食,到達晚上時特別,沈世林給我吃什麼,我就吃什麼,大約吃了七分飽后,他便沒再給我吃,而是在飯后讓我吃了一些助消化的水果,等他在房間哄著我睡好后,才和付博繼續工作著。
我也不知道他和付博工作了多晚才回房的,只覺半夜他回了房間,上床后,往常一般將我摟進懷中,便呼吸綿長睡了過去,雖然不是特別沉,可和平時的淺眠相比,這一夜的他顯得睡意是如此深沉。
第二天后,他吩咐仆人這幾天要要照顧我,無論我要砸什麼東西,任由我砸,必須得按時吃飯,他吩咐了這些后,便叮囑了我幾句,便帶著付博離開,去機場趕去國外開會。
他離開后,無論仆人如何對我說話,如何用盡一切手段來讓我吃飯都沒用,他們沒有靠近我時,我只是蹲在角落不說話,們要是靠近我時,我會像發瘋一樣攻擊他們,所以基本上他們都不怎麼敢靠近我。
沈世林出差后的第三天,有仆人強制來喂我吃飯,我抓住脖子狠狠咬了一口氣,直到頸脖被我要出,在幾個仆人的驚呼和幫助下,才離我口中,捂著傷口,滿狼狽的站在門口看向角落角帶的我著氣。
其中一個仆人聲音有些慌說:“夫人況越來越不對了,以后會不會和瘋狗一樣咬人”
Advertisement
那個被咬的人,捂著不算流的頸脖,聲音滿是心有余悸說:“不行,趕打電話給先生,這樣下去,我們本無法控制。”
幾人商量了一下對策,便沒再趕靠近我,出了房間后,便將門死死鎖住,我在角落拭掉角的,平息口那惡心的腥味。
仆人給沈世林電話后,他第二天才夜晚的飛機,早上六點到家,可他回來后,我躺在床上陷昏迷不醒,誰喊都沒用,沈世林將我從床上抱懷中,喚了我幾句,我都沒有反應也沒有回答,沈世林抱著陷昏迷的我,擰眉問仆人我這幾天的狀況,剖人將我這幾天的狀況描述得清清楚楚,還著重描述了我當時咬人的事,沈世林在一旁聽了,眉眼冷了冷。
很快醫生便趕來了,檢查了我,發現并沒有冒或者休克的癥狀,一切都顯示正常,他也沒有查找出原因,付博在一旁提醒問:“會不會是因為神的原因”
醫生說:“這種可能也并不是沒有,這段時間紀小姐的況明顯越來越差,從之前呆坐不理人,到現在會咬人,會攻擊人,甚至神有點狂躁,轉變到現在昏迷不醒,我想大約是自己不愿醒來,所以一直于沉睡的狀態。”
付博問:“那現在怎麼辦有什麼辦法可以讓醒”
醫生說:“據我這麼多年治療經驗,很多神病人都是因為某件事的刺激下,才導致神崩潰轉變到神失常,當然,也不缺從小到達生活力大,到特定時間點,神陷奔潰的邊緣的人,這兩者都有,而紀小姐明顯是前者,心病還需心藥醫,必須找到心結所在,我們才好對進行治療。”
Advertisement
沈世林皺眉問:“那什麼時候會醒。”
醫生說:“這要看自己,自己想什麼時候醒,就什麼時候醒,如果自己不愿,我們誰都無法強迫。”
他說完,便從皮箱拿出吊水瓶子說:“為了保持的營養與生命,這段時間我們盡量輸點營養給,并且想辦法給吃點東西下去。”
醫生為我吊水后,又開了一些鎮定的藥,囑咐了藥的劑量,便從這里離開了。
沈世林坐在那兒看向陷沉睡的我,一直沒有說話,付博站在一旁看了許久,兩人都沒有說話,付博在這里站了許久,接聽了一個電話,便從房間離開了,沈世林沒有出去,而是坐在我床邊,看向那瓶懸掛在空中,不斷往下滴水的營養,又低頭看向我蒼白的手臂,他出手了一下了針頭的手,輕聲說:“怎麼我才離開幾天,你就不吵也不鬧了。”
他盯著我沉睡的臉看了良久,才將我上的被子拉了拉,了我臉頰邊的長發后,聲音溫說:“如果覺得夢里快樂,那就好好休息,我會在夢外等你。”
他說了這句話,房間還是寧靜一片。
之后醫生每天來為我輸營養,沈世林沒有去公司,而是付博將公司的事全部搬回別墅給他理,每天仆人都有熬粥,但喂我時,粥總是從角流涎而下,讓仆人們急壞了,可又不知道怎麼辦,坐在一旁的沈世林看到后,便對手中拿碗的仆人說:“把粥給我。”
仆人聽后,立即將手中溫熱的粥給他,沈世林接過后,用勺子舀了一勺子粥放在邊試探了一下溫度,他覺溫度可以時,自己吃了一口,隨即才鉗住我下頜,將我輕輕掰開,邊覆蓋上來,一點一點將里的食渡給我,我不吞下去,他基本上不會離開,甚至抵住我要閉的牙關。
Advertisement
就這樣一點一點喂我進食,碗的粥還剩一大半時,站在一旁的付博終于看不下去了,他對沈世林說:“沈總,紀小姐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不如送去神醫院治療吧,現在只會讓病越來越嚴重。”
沈世林對于付博的話置之不理,繼續喂著我粥,直到他將一碗粥味到碗底后,他沒再繼續下去,而是用仆人遞過來的紙巾為我拭了一下角,他將我拭干凈后,他放下手中的紙巾,對付博說:“沈恪現在怎麼樣。”
付博聽到沈世林提起沈恪時,神明顯愣了愣,但隨即他回過神來說:“我打電話過去詢問了,說基本上飲食方面都沒問題,就是夜夜啼哭要媽媽,誰哄都沒用,要哭大半夜,哭累了才肯睡過去。”
沈世林聽了,嗯了一聲,便接過仆人遞過來的茶水,含了一口,隨即吐在痰盂,他放下手中茶杯說:“這幾天把他帶過來。”
付博凝眉說:“可現在您不是覺得紀小姐是裝瘋嗎”
沈世林說:“不管是否裝,到現在,已經不能賭下去了,把他帶過來。”
付博聽了,半晌說:“那我這幾天把他帶過來。”
沈世林看向仍舊閉目的我,對付博說:“出去吧。”
付博聽了沈世林的話,沒再多有停留,便從臥室離開。
過了幾天,付博終于把嘉嘉抱了過來,嘉嘉到達陌生環境后不斷在哭鬧著,哭聲不斷夾雜著媽媽,他現在將媽媽這兩字的音咬得極其標準,沈世林從我床邊起,從付博手中接過不斷哭著的嘉嘉,他哄了兩句,沒用,不斷朝著床上躺著的我手喊媽媽抱,沈世林抱著嘉嘉來到我床邊,將他放在床上后,嘉嘉便朝我快速爬了過來,趴在我上,小手
不斷拉扯著我服。
正當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嘉嘉上時,吊水瓶子被嘉嘉扯住輸藥管,瓶子甩落地上,我手背口管回出來,沈世林第一時間便將藥停止輸,醫生將連忙將我手臂上的針頭出來,正當所有人被嘉嘉這一鬧,鬧得手足無措時,站在一旁的付博忽然開口說了一句:“紀小姐的眼皮了一下”
沈世林將正鬧騰不已的嘉嘉抱懷中,看向躺在床上的我,我睜開了一下,隨即又合住了,醫生在一旁看了好一會兒,立馬拿著一個東西開我眼皮,照住我眼睛查看了一下,又量了量溫,做了這一系列事后,所有人都對于我剛才睜開的一眼有目共睹,醫生收起聽診,明顯也松了一口氣,說:“明顯孩子的哭聲對于來說,有刺激的作用,母親對于孩子的哭聲是非常敏,能夠主睜開眼,雖然只是一下,但我相信,只要時常讓孩子和相,或者在房間吵鬧,我想,一定會有作用。”
醫生這樣說,在場的雖有人明顯都了一口涼氣,仆人將嘉嘉從房間抱走,醫生重新為我輸,之后那幾天,嘉嘉便一直在這里居住著,也是仆人在照顧他,沈世林會帶著嘉嘉來我房間玩著,但并不會玩很久,因為怕我適應了這聲音,反而起反作用,只讓嘉嘉在房間頂多完半個小時,便讓仆人接走。
這樣過了兩天,沈世林往常一般從公司回來后,便帶著嘉嘉在我房間玩一會兒,玩了半個小時,嘉嘉累了,仆人將嘉嘉抱房間休息,沈世林坐在那看了我一眼,因為很晚了,他起去浴室洗澡,等他從浴室出來后,手上正用干燥的巾拭著碎發上的水珠,他手機傳來郵件的提醒聲,他從桌上拿起隨便回復了一下,正要放下手機時,他手一頓,手機并沒有放在桌上,而是直接從他手上摔了下去,在房間發出尖銳的聲音。
我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看向他,他看了我許久,忽然說了一句極其平常的話,他說:“醒了。”
我一直看著他,本沒有過,他一直將碎發上的水珠干凈后,才放下巾,傾看向床上的我,他觀察我直愣愣的眼神,臉覆了下來,在我臉上吻了吻說:“這幾天過的開心嗎”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114 章

晚安,替嫁甜妻!
“這是我從死神手裏搶回來的男人,妳也敢搶?”木晚晚冷冷的看著那個要打藍鏡深主意的女人,可女人面露不屑,神色囂張,對著木晚晚譏諷道:“妳只是壹個見不人的私生女,妳更配不上藍鏡深!”“配不配,不是妳說了算!”藍鏡深攜著壹身冷峻的氣勢走來,攬過木晚晚的腰肢,在她唇上落下壹吻,隨後又旁若無人般暧昧說道:“夜深了,咱們該回去睡覺了。”
11萬字8 5469 -
完結434 章

柏少夫人太撒野
容知從小被抱錯,在鄉下生活十八年,家裡窮,高中就輟學打工 十八歲親生父母找上門,說她是京城容家少爺,來接她回京城 上有盯家產叔伯,下有親生兄姐 她被父母警告:向你哥哥姐姐多學規矩,不要惹是生非,容家丟不起你這個人 容知撥了撥額前的碎發,笑顏如花:“好的。” 所有人都等著看這個不學無術一事無成的容三少笑話,結果看著看著,人家混成了京城說一不二的太子爺 眾人:這跟說好的不太一樣? ? * 柏家家主回國,京城所有世家嚴陣以待,唯獨容家那位依舊瀟灑 某日宴會,眾人看見那位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柏家主彎下腰來,手裡提著一雙高跟鞋,語氣無奈:“嬌氣。” 再一看他身前那個穿著黛青旗袍的長發女子,光腳踩在他的皮鞋上,“我就嬌氣,你管不著。” 這熟悉的臉,這熟悉的囂張語氣... 眾人瞠目結舌,大跌眼鏡:容三爺? ! 【前期女扮男裝+微科幻+無邏輯+爽文+1v1sc】
74.9萬字8 70880 -
完結725 章

重生後在前世死對頭懷裏興風作浪
【清冷豪門千金 遊戲人間貴公子 重生 先婚後愛 單向暗戀 男主強勢寵】北城明珠秦寧重生了!前世秦寧死於自己的愚蠢,她愛得死去活來的丈夫聯合繼妹吞並秦家,在被利用完後她千瘡百孔的淒慘死去。再睜眼,秦寧腦子清醒了。麵對渣男虛偽哄騙,繼妹陰險謀奪家產,後母的陰謀算計,她全都冷靜應對,這一世,她要前世害她的人付出代價!為複仇她不惜拉下臉,找上前世那位被自己打了臉退婚的死對頭傅京寒談合作。素來倨傲的天之驕子,輕蔑冷笑作者:“秦大小姐,我從不吃回頭草。”她唇瓣一勾,“你不用回頭,我會走到你麵前,確定真不吃?”……眾人得知老死不相往來的兩人再度聯姻之時,全都說傅京寒是為了報複秦寧,肯定是為了狠狠甩掉她出氣。直到有人看到秦寧與傅京寒逛街,她嬌氣癱在男人懷中,“累了,走不動。”而那位傅少寵溺又無奈的在她麵前彎下強大的身子,嘴裏還溫柔的低哄道作者:“下回我累點,不讓你累。”口口聲聲說不吃回頭草的浪蕩子傅少,不但吃了回頭草,還吃得心甘情願。後來,傅少不但沒有甩了秦寧,反而還在婚後變成二十四孝好老公,比誰都疼老婆。
89.9萬字8.08 30793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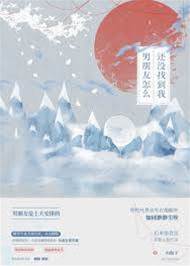
男朋友怎麼還沒找到我
十七歲的夏天,姜照一誤入了朝雀山景區的一片蓊鬱密林,走進了一座舊廟。 她伸手搖響檐下的白玉鈴時,一縷紅絲穩穩地綁在了她的手腕,絲線盡頭是金色流光,她看不見另一端究竟連接去了哪裏。 少女憧憬愛情,是從同桌遞過來的一本小說開始的。 因爲那根綁在她手腕,別人卻看不見的紅線,姜照一堅信老天爺給她配發了個男朋友。 後來她偶然發現,只要將一些東西輕觸紅線,就會被立即傳送到不知名的地方去。 —— 地獄沉睡數百年的修羅甦醒,卻發現亮晶晶的糖果和一封又一封的情書幾乎要將他淹沒在棺槨裏。 他隨手拆掉一封,展開信紙:“男朋友你怎麼還沒找到我!你好笨鴨!:)”署名——姜照一 —— 姜照一從高二等到大二,紅線另一端的男朋友還是沒來找她。 可是那晚和朋友們從ktv出來,喝醉的姜照一勉強看清自己紅線連接的另一端不再是半隱半現的虛無光色。 她順着紅線連接過去的方向,看清了那個男人帶着一道猙獰傷疤的腕骨。 然後姜照一就掙脫了朋友的手臂,哇的一聲哭出來,展開雙臂撲進他懷裏:“老公!” 她的朋友們:???QAQ
13.7萬字8 1427 -
完結290 章

溺玫瑰
好友一句话总结温书梨:漂亮而不自知。 最为轰动五中论坛的一幕,当属她在文艺晚会牵起小提琴演奏的《Daylight》。 少女身着浅白长裙,气质皎洁,光影倏然袭来,那一刻,她宛若众星捧月的天之骄女。 演出结束后,有男同学阻挡她的去路,“你真漂亮,做我女朋友吧。” 温书梨长睫微抬:“不好意思,我有喜欢的人。” 十五岁那年盛夏,她记忆犹新。 篮球场上,少年身侧轻倚枝干,仲夏细碎阳光憩于他脸侧,炙热又晃眼。 她努力收集有关他的所有碎片:喜欢夏天、汽水、玫瑰……却唯独没能知道他的名字。 - 沈厌——五中知名风云人物。 人又酷又拽,成绩碾压万人稳居年级榜首,无数小迷妹排队送情书,却都被他一一回绝。 少年语调恣肆:“抱歉,心有所属。” 无意的初见,他记了整整三年,但那时候,两人之间像是隔了一条无垠长河,触之不及。 后来,死党告诉他,有个很漂亮的女孩暗恋你。 他懒得问谁,直到无意间看见照片上熟悉的栗棕色长发。 少年喉结稍滚,不言轻笑。 高中再遇她,他一次次蓄意接近、步步为营,泛染强烈的私欲引她溺入绚烂成簇的玫瑰漩涡。 “温书梨,我喜欢你。” “小玫瑰,你在原地,等我去找你。” - 某次大学聚会,众人玩起真心话大冒险,沈厌抽到[吐露真言]的冒险卡牌。 周遭不约而同看向那对情侣,起哄。 温书梨问他:“阿厌,在你眼里,我是什么?” 沈厌轻笑,眉眼间尽是宠溺。 房间灯光晦暗,墨色延绵,他附在她耳边,嗓音低又沉:“是我的软肋。” -我的软肋只有你,只能是你。 迟钝直球美不自知的小玫瑰×酷拽专一的全能学神大佬
43.7萬字8 14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