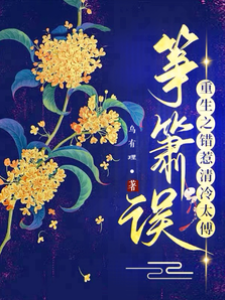《懷嬌》 第47章 第47章
薛鸝與魏玠目匯,一瞬間如墜冰窟,寒意充斥著四肢百骸,讓不由自主地發抖。
極大的絕與恐懼讓的胃里都一地發疼,所有的期都在此刻破碎,徹底沒了法子,著聲喚他:“表哥……”
魏玠看的目著一種冷漠的了然,“鸝娘想去哪兒?”
鋒利的劍刃落在薛鸝頸間脆弱的皮上,只要輕輕一劃便會流如注。微弱的線中,魏玠看不清薛鸝臉上的表,卻約能猜到是如何出楚楚可憐的模樣,想要讓他再一次心放過。
薛鸝彎傳來的疼痛讓連站起來都難,只能癱坐在地泣道:“我想阿娘……我想見一面,求表哥放了我吧。”
此刻狂風大作,空氣中彌漫著嗆人的煙霧。薛鸝心中知曉讓魏玠心是件極為渺茫的事,可毫無辦法,一旦此次再被抓回去,必定會被嚴加看管,日后不知何時才能得到自由,更遑論去找到梁晏了。
恐懼激發了薛鸝的怨氣,幾乎崩潰地大哭起來,毫無往日端莊婉的模樣,捂著臉哭得軀抖。
魏玠皺著眉打量,心中漸漸生出一種不解。
他為何要為薛鸝這種子了心神,貪生怕死,自私自利,里往往沒有幾句真話,甚至連許下的誓言都可以輕易反悔。
魏玠從心底鄙夷厭棄,偏偏又想留住,又期盼薛鸝如同喜梁晏一般喜他。
何嘗不是他在自作自,索殺了薛鸝,一切便又能回到當初。
他眼眸低垂著,神似悲憫又似漠然。“鸝娘只要我不好嗎?”
薛鸝的哭聲漸漸停了,噎著沒有立刻答話,便聽魏玠開口道:“若做不到,我放你離開便是。”
Advertisement
說罷,他當真收了劍。
薛鸝愣了一會兒,不可置信地看著他,而后心中狂喜,忍著痛狼狽不堪地起想要走,然而還未等出一步,心中強烈的不安便讓生生僵在了原地。
他溫聲道:“怎麼了?”
薛鸝了眼淚,靠過去抱住魏玠,眼淚蹭在他的襟上。的嗓子一陣發堵,還帶著哭腔說道:“我要表哥……”
才不信瘋子的話!只怕不等走出玉衡居的大門,魏玠便會毫不猶豫地殺了。
活著才是要事,無論有多屈辱都要著。
因為刮了大風,火勢難以止住,用來鎖住薛鸝的屋子被燒了個干凈。除了玉衡居,府中還有不院子被燒,若不是家仆及時趕到,魏翎只怕是要將自己都燒死在祠堂中。而后不久便下起大雨,火也漸漸滅了,并未鬧出什麼人命。
薛鸝被鎖在了琴房中,魏玠去理事務,將丟在此不管。
琴房安靜又冷,薛鸝一眼便看到了角落那張廢棄的琴。琴上遍布劃痕,琴弦盡數斷開。晉照用石頭砸中了薛鸝的,以至于如今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只能坐在原地怨毒地盯著那張琴。
薛鸝傷心夠了,躺在榻上歇息,夜里忽地不過氣,睜眼后對上一雙漆黑的眸子,嚇得一個激靈清醒了過來。
魏玠的五指落在頸間,力氣大到讓的呼吸都變得艱難,漲紅著臉去掰開他的手,語氣幾近懇求:“表哥……魏玠……”
眼淚砸在他手背上,魏玠眼睫了,似是生出一不忍,手指也忽地松了。
薛鸝大口著氣,口劇烈地起伏著。魏玠想要抬手一的臉頰,被又驚又懼地避開。眼看魏玠的目逐漸森冷,薛鸝平復了呼吸,強忍著恐懼主靠近,在他懷里將他摟。
Advertisement
的作帶著討好,魏玠顯然十分用,親地低頭吻。
他閉了閉眼,極輕地嘆了口氣。
果然還是……不舍得就此殺了。
這算是嗎?似乎并不快活,反徒增了許多煩惱。
薛鸝遠不如面上那般鎮靜,被魏玠的晴不定嚇得要發瘋。前一刻仿佛要取命,一句話后便能與耳鬢廝磨,從未見過如此難以琢磨的男子。
一邊配合地仰起頭與他親吻,一邊在腦子里迅速想著自己是否又做錯了什麼事。卻不知怎得,想起了多日前魏玠近乎威脅的話,倘若不能讓他到的快活,便沒有了留下的必要。如今的魏玠興許是到了厭煩,亦或是今日想要逃走,惹得魏玠心中不耐,已經對起了殺心。
一吻畢,薛鸝扯了扯他的袖子,眸子水盈盈的,瓣也好似染了一層花,艷無比。
不可否認的是,他的會因薛鸝而產生異樣,冰冷的吻也漸漸有了熱度。
薛鸝夷似的手指被他握在掌中,他呼吸有些不穩,額頭抵著薛鸝的肩緩緩平復,片刻后,似乎仍未有好轉,他的挲著薛鸝的側臉,嗓音低啞道:“鸝娘,你知曉該怎麼做嗎?”
薛鸝臉頰火燒似地發燙,咬了咬,半晌沒有吭聲。
魏玠做了二十余年的正人君子,繁衍子嗣的男歡是為天理,而這樣的下流行徑于他而言卻有幾分難以啟齒。
說不如做,他索了薛鸝的指尖,將帶向自己。
琴房一向是魏玠尋求清凈,去除雜念的地方。人生一世都有既定的命數,他要為了魏氏而活,恪守禮教節制念也是理所應當。只是他不曾想過,有朝一日會因為薛鸝,讓他奉行多年的儀態禮法在念前潰不軍。
Advertisement
侍者端來凈水與帕子,魏玠握著的手指一替洗干凈的時候,的腦子還在嗡嗡作響。誰能想到克己復禮的魏玠,在之時能發出這些聲音,讓一個聽者都憤死。
那些息與輕|在腦海中揮之不去,一直到魏玠若無其事地來侍者,仍覺得回不過神。
魏玠干了手上的水,沉思片刻,問道:“鸝娘對樂安做過這些嗎?”
他的心似乎還算愉悅,語氣便也帶了幾分溫和的笑意。“莫要騙我。”
薛鸝連忙答道:“不曾。”
接著又補了一句:“世上與我如此親的僅有表哥一人。”
魏玠連用過的杯盞都要丟棄,倘若與梁晏有過什麼還敢他,只怕不死也要被剁了這雙手。
他坦白道:“樂安已經離開了去往上郡。”
薛鸝強忍失落,只出些許無奈,說道:“我與世子無緣,能與表哥相守已經心滿意足了。”
他笑了笑,似允諾一般說道:“只要鸝娘我,我亦會永遠待你好。”
夜已深,魏蘊猛地坐起,薄衫已被冷汗浸,涼風一吹冷得霎時間清醒了過來。靜引來了守夜的侍,侍立刻遞上茶水,關切道:“娘子可是做了噩夢?”
魏蘊緩了緩,低落道:“我夢到了鸝娘,有人欺負,無論我如何追都追不上……”
薛鸝已經失蹤多日,侍不知勸了多回,只好安道:“薛娘子定會平安無事,娘子還是莫要為此傷神了,連平遠侯府的人都走了,娘子心急又有何用呢?”
魏蘊想到梁晏,不冷嗤一聲。
然而冷靜片刻,腦海中又響起了一道人聲。
“我今日似乎聽到了鸝娘的聲音。”
侍默了默,語氣越發無奈:“小姐做夢了。”
魏蘊本來心中猶疑,被反駁后反而堅定道:“玉衡居著火的時候,我好像聽到了鸝娘在哭,我本想去看看堂兄,他們不讓我進去……”
侍無奈道:“娘子莫要說傻話了,薛娘子不見了許多日,怎會與大公子有什麼干系。”
魏蘊呆呆地點頭,說道:“你說的是……堂兄他不是這樣的人,他若找到了鸝娘,必定立刻送回來。想必是火勢太大我昏了頭。”
侍又安了魏蘊幾句,一直等到重新躺下才離開。
然而這個念頭一旦冒出來,正如同瘋長的野草,無論如何都除不去,魏蘊徹夜難眠,清早起洗漱后,立刻拉過侍,面嚴肅道:“隨我去趟玉衡居。”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60 章

狂妃在上:絕色帝尊日夜寵!
穿越被下藥,撞見一絕色美男坐在火裡自焚……「帥哥,反正你也不想活了,先讓我救急一下!」某女撲倒在火中渡劫的邪帝,睡後溜之大吉。傲嬌帝尊醒來,咬牙切齒:「把那個女人找出來,本座要親手弄死!」君時月正沉迷宅鬥手撕渣男賤女不亦樂乎,邪帝滿身殺氣找上門,她以為自己死定了,誰知——「月兒想要什麼,本座給你!」「月兒想吃什麼,本座餵你!」「月兒想練什麼功法,本座陪你雙修!」軒轅大陸眾人一臉黑線:「帝尊,這就是您老所說的親手弄死嗎……」
92.9萬字8.36 421403 -
連載1644 章

福晉在上:四爺,狠會寵!
【1V1高甜】剛成親,楚嫻天天想著怎麼撩四爺抱大腿,後來,一看見他就想跑!眾皇子紛紛來訪:身為天潢貴胄為何想不開獨寵一人?左擁右抱不好嗎?「我家福晉長了一張必然得寵的臉,又乖巧聽話,別人比不了。」被關外臥房門外三天的四爺一臉嚴肅認真地回答。眾皇子一片寂靜:……從沒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徒!俊美禁慾的男人又兀自惋惜道:「隻除了體力不太好……」房門大開,小福晉纖纖玉指拽住男人的腰帶,已是惱羞成怒:「胤禛,你給我進來!」
152.1萬字8 50505 -
完結342 章
玉無香
溫二姑娘美貌無雙,人們提起卻要道一聲嘆息,只因她生來是個啞子。誰知有一日,從牆頭掉下砸在靖王世子身上的溫二姑娘突然開口說話了。
62.7萬字8 45331 -
完結262 章
氣哭,穿成真千金還要跟反派假裝恩愛
【扮豬吃虎+穿書+甜爽文+追妹火葬場+反團寵】 快穿局王牌特工南青風穿書了,成了苦逼炮灰真千金。 看假千金混的風生水起,還得了一幫道貌岸然的正派青睞。 南青風一手拿著鑼敲了起來,“收反派,收心狠手辣的反派,收喪心病狂的反派......” 什麼邪不勝正? 因為“邪”不是我。 我獨我,天下第一等,此間最上乘。
45.5萬字8.18 7742 -
連載573 章
侯府雙嫁
葉家心狠,為了朝政權謀,將家中兩位庶女,嫁與衰敗侯府劣跡斑斑的兩個兒子。葉秋漓與妹妹同日嫁入侯府。沉穩溫柔的她,被許給狠戾陰鷙高冷漠然的庶長子;嫵媚冷艷的妹妹,被許給體弱多病心思詭譎的嫡次子;肅昌侯府深宅大院,盤根錯節,利益糾葛,人心叵測,好在妹妹與她同心同德,比誰都明白身為庶女的不易,她們連枝同氣,花開并蒂,在舉步維艱勾心斗角的侯府,殺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最后,連帶著不待見她們二人的夫君,目光也變得黏膩炙熱。陸清旭“漓兒,今夜,我們努努力,再要個囡囡吧。”陸清衍“寒霜,晚上稍稍輕些,你夫君我總歸是羸弱之身。”
100萬字8 4203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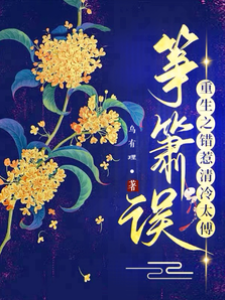
箏簫誤:重生之錯惹清冷太傅
【重生】【1v1雙潔、HE】原名:《箏簫誤》【深情克制“高嶺花”權臣✖️堅韌勇敢“不死鳥”千金】 *** *** 死光了男丁的祝府,窮的只剩花不完的錢。 樹大招風,孤立無援,前世被太子滿門抄斬。 一朝重生,祝箏為了保全全家,順了祖母招婿的美人計,生米煮熟飯,討個平庸的夫婿聊作靠山。 春酒助興下,紅羅帳燈昏,一夜良宵暖…… 但是……等等!哪里出錯了? 誰能告訴她……晨起枕邊人,為何不是祖母的安排? 而是當朝權臣,太傅容衍? —— 深山雪夜,月下梅前。 容衍給祝箏講了一個故事。 癡情的妖君與山神做了交易,換回他的公主死而復生。 祝箏凝眉:“他交易了什麼?” 容衍:“不重要。” 祝箏:“怎麼會不重要?” “公主不知道,所以不重要。”他目光沉靜,淡淡道,“妖君不在乎,所以也不重要。” “那什麼重要?” 容衍抬眼,眸光若皎皎冷月,籠罩著眼前人。 良久,道出兩個字。 “重逢。” - 情難自解,愛是執迷不悟,覆水難收 #非傳統重生文,立意“純愛萬歲,自由萬萬歲” #男追女,究極暗戀、蓄謀已久、甜寵微虐、復仇、沒有火葬場的漫漫追妻路、無雌競、非嬌妻、非女強、非強取豪奪、女主輕微回避型依戀(請自行排雷)
37.5萬字8 1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