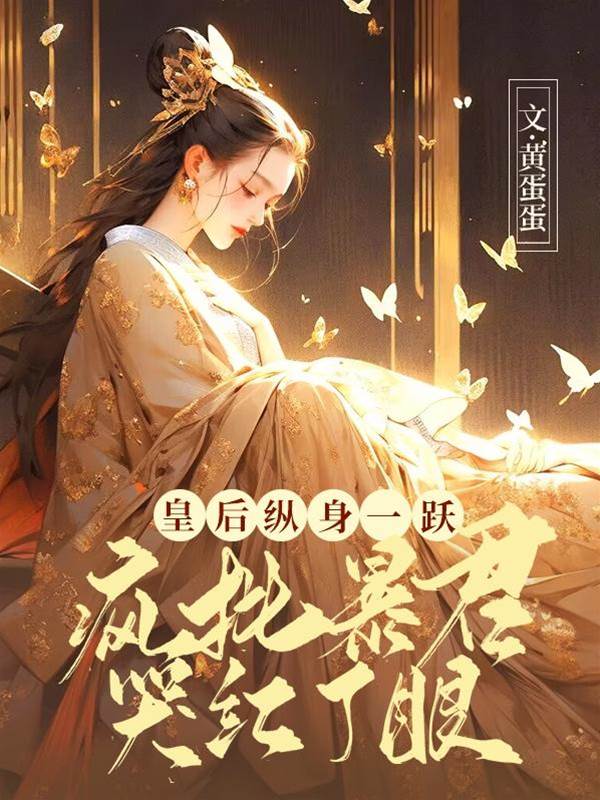《我打造了盛世王朝》 第146章 又被擺了一道!
一夜酒香醉心神,半醒仍似醉夢中。
日上三竿,照進廂房的很是溫暖,頂著窩頭坐起的薛奉年兩眼懵,回憶了很久才流出笑意,臉上還有幾分意猶未盡,似乎仍然沉醉在昨日的酒宴里。
他還記得昨夜赴宴,北王殿下拿出絕品酒塞北紅,酒香四溢,連新酒都遠不能及,舉杯推盞很是盡興,可謂是生平未有的樂事。
而后又被殿下留宿府中,好客之令人懷。
塞北紅是真香啊......
僅是聞著上散出的酒香,就是神仙下凡恐怕也得醉倒,這一行倒是沒有白來,而且還遠超了預料,可謂是收獲不小。
薛奉年很是滿意地微笑起,門外已經有王府的丫鬟靜候多時,連忙洗漱一番,薛奉年問詢之下,即刻隨著仆從去往了殿下所在的小院。
一路踏來,經過幾道走廊,龍紋雕飾浮現數次,王府的貴氣時刻縈繞旁,薛奉年再無昨日的傲氣,神變得嚴肅了幾分。
直到再小院,卻是見張之棟和殿下在落座閑談,桌上放著一壺清茶幾樣糕點,看起來已經有了些許時辰。
見這形,不勝酒力的薛奉年臉頰泛紅,他也算是個好酒之人,昨日竟是被生生的反倒,此事說出去實在丟人啊。
張之棟和北王手下的武將也就罷了,畢竟軍人常年習武好酒,酒量自然是沒得說,卻是沒想到連北王都酒量驚人,幾乎不見有醉意。
這實在是令薛奉年心頭震,已然視為了神人。
他哪里知道,塞北紅這種蒸餾酒度數遠高于當世的酒,對于秦風卻不算什麼,喝個半斤八兩就和熱差不多。
秦風見到這個二代穩步踏遠門而來,目帶有崇敬,表現出了幾分為主人家的客氣,微笑著注目而去。
Advertisement
“薛公子,早啊。”
這話一出,張之棟緩緩回頭來,薛奉年臉更紅,卻是不敢反駁,近前做禮應聲,腳底下都快摳出一大宅子了。
“殿下有禮,在下不勝酒力......若有失禮之,還殿下恕罪。”
薛奉年雖是出了得,倒也為人真誠,言行舉止頗有風度,不像尋常的權貴之后那般倨傲,確是難得。
聽聞誠摯的話語,秦風也沒有取笑,而是出豁達的微笑。
“無妨,飲酒乃是一大樂事,無需計較太多禮節。”
“本王正與張都督閑談,兩位遠道而來買酒,確是對新酒十分中意,本王自然不能小氣,已然命人備好了新酒一百斤,令贈塞北紅兩壇,待到稍后用過午膳,便可命人裝車,兩位若無他事,可在王府小住幾日,本王也好盡地主之誼。”
一番話說得是大度非凡,無論禮數還是氣度,都不愧皇室之風。
面對這種值得結的朝堂大員,秦風自然不會小氣,何況眼前的張之棟還答應了送來三千斤鐵礦石,解決了一件大事,至也得給人家一點兒甜頭才是。
這話一出,張之棟和薛奉年都齊齊做禮。
“謝殿下!”
薛奉年聽聞還送兩壇塞北紅,心里已經樂開了花,還聽到殿下要留他們用膳,幾乎對這位年輕的王爺好攀升了數倍。
王府的膳食都是廚手藝,再配上那塞北紅,滋味真是沒得說,就算是刺史府的飯食,都遠遠不能比。
今日可是有福了。
就在薛奉年還想再開口道謝,以表達激之的時候,張之棟卻是搶先一步出聲,語氣有些嚴肅。
“殿下盛,末將銘記于心。”
“只是此次前來......買酒,事出突然,末將軍務纏,薛賢侄也要趕回涼州為父祝壽,恐怕不能久留,待到新酒裝車,我等就得立即返回,還殿下見諒。”
Advertisement
“他日神兵出世,末將一定命人帶厚禮謝恩,殿下恕罪!”
突然的進言有些嚴肅。
薛奉年聽得心頭憾,礙于是張之棟所言,他也知道必有緣由,就未再敢多,顧全大局附聲做禮。
“還殿下見諒。”
一老一小齊齊做禮,氣氛有些肅穆,秦風也未挽留,不出意料地點頭微笑應允,隨即命令王勛親自安排裝車,并囑咐送出城外三里地。
深厚誼令人,薛奉年對這位殿下印象極好,引為同輩難得的妙人,再度謝恩真意切。
張之棟聞聲謝恩,心里閃過了一無奈,就此拜別北王,一路再無話語。
正午時分。
幾輛馬車駛出鄴城東門,王府參將王勛帶人護送,不同尋常的陣仗引人注目,不百姓熱議不斷,為了當日的熱門話題。
哪怕駛出城門,王勛依然護送而去,與那陌生兩人遠遠做禮拜別方才返回,重視程度可見一斑,更是引得了門前往來民眾的驚嘆,連守城衛士都神驚訝。
唯有孫二眼中得意,著悉的車隊和那一老一,心頭慶幸無比,笑容里漸漸出一副早已看穿一切的高深睿智。
看吧,打探大勝的果然都不是簡單角,還好小爺聰明!
車隊一路向北,漸漸消失在視線之中......
順著道一路前行出數里地,端坐在馬車中的薛奉年才平復下了心頭的激,收獲的喜悅漸漸平息,轉而注意到了張之棟無比嚴肅的神。
悄聲注目而去,只見悉的張都督面容凝重,好像心事重重,連昨日收獲神兵的喜悅都難看到。
不由得,薛奉年放下了手中的塞北紅,悄聲凝而去。
“張叔叔,北王未有異心,又民極高,顯然是位賢明的藩王,我們此行目的已經達到,甚至能被如此禮遇,理應歡喜而歸才是。”
Advertisement
“您為何......悶悶不樂?”
張之棟聞聲抬頭,了一眼年輕的薛奉年,見到這位賢侄神疑,稚的問話回響耳畔,只得輕輕一嘆。
“哎。”
薛奉年已經是極為出眾的青年翹楚,整個涼州城罕有人能相提并論,卻是仍然無法與北王相較,甚至在相比之下,顯得這般躁輕浮。
若不是親眼見到,張之棟也難以相信此事。
或許,這就是出的差異吧。
俗語有云:龍生龍生,老鼠的兒子只打。
薛奉年遠勝于尋常青年,也是建立在家世的基礎之上,刺史公子的起點,就注定了他俯視絕大多數同輩,無論人脈還是學識,必然遠超同輩,眼界更是尋常人終生難。
而那位北王秦風,出皇室的命運雖是波折不斷,卻也有了足夠的底蘊和眼界,幾乎是出生之時就立于大玄朝萬萬人的頂點之上,這樣的命運,令年僅二十歲的北王城府極深。
哪怕是張之棟,都到難以應對。
如此妖孽般的青年人,又豈是常理能論,普通人拿來相比,也未免有失公允。
著薛奉年愈發驚疑的目,張之棟收起了心頭慨,語重心長地教導出聲,神嚴肅到了極點。
“賢侄,我們又被北王殿下擺了一道,從今日起,我們已經和北王拴在了一起。”
擺了一道?
薛奉年聞聲皺眉,回響方才的一切,只覺心頭好似又云霧漸漸破開,清秀的面容猛然一。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