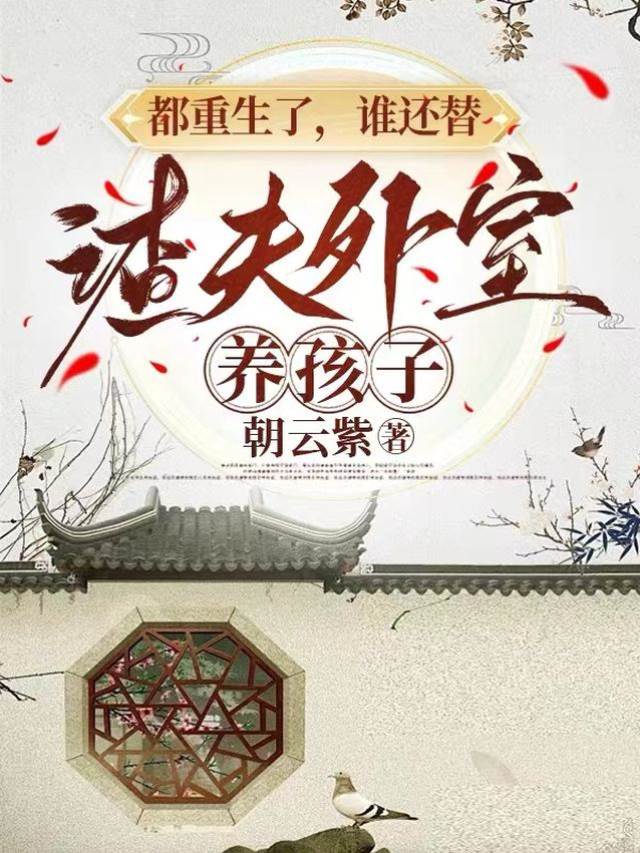《宦寵天下》 第540章 江瀲這家伙真是越來越不著調了
“本王目前也沒有很好的應對之策。”
宋憫苦笑之后說道,“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在加強防守的同時,多派幾路斥候去打探消息,左右飛虎軍距離尚遠,并不急于一時,我們不要自陣腳。”
“還有就是……”他頓了頓,盡量語氣平和地給眾人打氣,“飛虎軍再強大,不過八萬之眾,在南疆打了那麼久的仗,肯定會有傷亡,再從南疆千里跋涉而來,難免人困馬乏,我們以逸待勞,勝算滿滿,何懼之有?”
這番話功地驅散了眾人心頭的焦慮,大家都冷靜下來,暫時不再為此事擔憂。
然而,僅僅過了兩日,新朝東南方向與大周接壤的寧州府便被飛虎軍攻陷了。
新朝是宋憫為他們的新政權取的國號,從立至今所發展的地域便是山陜兩省的各州府,以及川北豫西的幾個州府。
寧州府位于河南陜西山西的界,因當地衛所將領和知府都是張壽廷的舊,在新朝建立伊始,便主歸順,與大周劃清了界線。
寧州府雖小,地理位置卻很重要,從前是扼三省咽之地,如今是兩國界之境。
這麼重要的地方,布防自然嚴,張壽廷還特意派了自己最信得過的部將在那里鎮守,任誰都想不到飛虎軍會把它當作第一個攻擊目標,更想不到它會如此不堪一擊。
變故發生在夜里,飛虎軍到來得悄無聲息,等到守城兵發現時,城城外已是一片火海。
戰斗開始的快,結束的更快,一夜之間,城墻便上了飛虎軍的旗幟,城中駐軍死的死,降的降,知府的腦袋被砍下來掛在城門上,一條白綾隨風飄搖,白綾上用鮮寫著五個大字:叛國者必死。
Advertisement
消息傳到西京,嚇壞了滿朝文武,宋憫更是又驚又怒,差點當場暈倒。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眾人七八舌,“攝政王不是說飛虎軍還很遠嗎,怎麼眨眼的功夫就到了?”
不僅到了,還無聲無息地攻下一城,砍了知府的腦袋,這也太神了吧?
張壽廷也坐不住了,把信使進來仔細盤問,飛虎軍究竟是怎麼到的寧州,又是怎麼攻的城門。
信使也不知道況,只知道飛虎軍的馬蹄都包了布,等到守城的聽見靜,人家已經到了跟前,南城門還在打,北城門已經破了,飛虎軍進了城,直接聲明不會傷及百姓,其他人若愿意歸降,放棄抵抗可免一死,負隅頑抗者格殺勿論,如此一來,城池很快就被飛虎軍占領了。
“就這麼簡單?”張壽廷不敢置信地大喊,“即便包了布,也不可能一點聲音都沒有,除了守城兵,城外還有哨兵呢,他們都干什麼吃的?”
“還用問,要麼被滅口了,要麼被收買了。”宋憫這時候終于緩過一口氣,聲音虛弱地打斷了他的喊,“飛虎軍再厲害,若沒有里應外合,也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攻下寧州城。”
“,怎麼可能有,那些可都是我的人。”張壽廷道。
宋憫扯笑了下,笑得意味不明:“他們能為你背叛別人,也能為了別人背叛你,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
張壽廷啞口無言,怔怔一刻又道:“可飛虎軍不還在路上嗎,即便他們兵分幾路,我們的人也不可能一點消息都打聽不到吧?”
“大將軍終于問了一個好問題。”宋憫掩輕咳兩聲,轉而看向李鈺,“陛下有何見解?”
Advertisement
“朕以為,打著飛虎軍旗號的,并不一定是飛虎軍。”李鈺十分篤定地說道。
群臣一片嘩然,隨即又連連點頭。
“沒錯,陛下說的有道理,飛虎軍明明離我們還很遠,就算長翅膀飛,也沒這麼快飛到寧州。”
“對對對,肯定是別的軍隊打著飛虎軍的旗號在行事,想嚇唬我們,迷我們,讓我們自陣腳。”
“狡猾,真的太狡猾了。”
“可即便不是飛虎軍,寧州還是丟了呀!”眾說紛紜中,一個聲音給大家兜頭潑了一盆冷水。
眾人頓時安靜下來,泄氣地又看向宋憫。
宋憫用力按著心口,臉白得嚇人,還是強撐著安眾人。
“眾卿不用怕,我們這次只是一時不察,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有了這個教訓,后面他們不可能再得逞,傳令各地加強防守,城外城都要增派巡兵,全將士十二時辰兵不解甲,隨時準備迎敵,另外,讓斥候軍切關注飛虎軍的向,以及每日行軍的人數,一日一報改為一日三報,不得延誤。”
“是。”朝臣們雖然仍是心有余悸,事已至此,也沒有別的好辦法,只能按照宋憫吩咐行事。
眾人都退去后,宋憫這才了長山過來,讓他親自去寧州打探消息,看看那支不聲不響攻占了寧州的軍隊是什麼來頭。
此后的時間,各州各府都按照宋憫的吩咐部署城防,時刻保持作戰狀態。
然而,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大周軍自從寧州一役后,就再也沒有過任何行,如同沉水底的炮仗,徹底啞了聲。
如果不是寧州的城樓上還掛著知府的人頭,還飄著飛虎軍的軍旗,他們都要懷疑這是一場夢,尤其是斥候軍最新傳回的消息稱,昭寧帝又在某地為百姓造了一座橋。
Advertisement
聽到這個消息,所有人都氣壞了。
他們在這里每日厲兵秣馬,枕戈待旦,人家卻在那里優哉游哉地鋪路造橋,完全沒把他們當回事。
這種覺就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本無使力,這仗還怎麼打?
宋憫也很氣,卻不能在朝臣面前表現出來,回到自己的寢殿后,屏退眾人,砸了一地的東西。
李長寧!
李長寧!
因為有李鈺在,他早就料到李長寧不會痛痛快快地和他正面對壘,但他還是沒想到,李長寧的劍走偏鋒會偏這樣,偏到他預想不到的角度。
怎麼能這樣!
怎麼能這麼可惡!
只可惜,他的咬牙切齒并不會對杜若寧產生任何影響,此時的杜若寧正站在山坡上,欣賞山下新修好的一座河大橋。
“你猜宋憫現在會是什麼反應?”看了一會兒,歪頭笑地問站在旁的江瀲。
江瀲的視線從橋上收回,轉著眼珠想了想,突然彎腰撿起一塊石頭砸了出去,同時捂住心口作西子捧心狀,氣急敗壞地喊道:“李長寧,可惡,又是你,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杜若寧愣了片刻,才明白他是在模仿宋憫,頓時笑得前仰后合。
江瀲這家伙,真是越來越不著調了。
要是被宋憫看到他這樣,會不會當場吐而亡?
哈哈哈哈……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81 章

奪嫡
他將她囚禁。背叛,滅族,辜負。她死于一場蓄謀已久的大火。燒到爆裂的肌膚,寸寸誅心的疼痛和撕心裂肺的呼喊,湮沒在寂寂深宮。重生歸來。她卻只記得秋季圍獵的初遇,和悲涼錐心的結果。人人避之不及的小霸王,她偏偏要去招惹。一箭鎖喉搶了最大的彩頭,虞翎…
45.9萬字8 106515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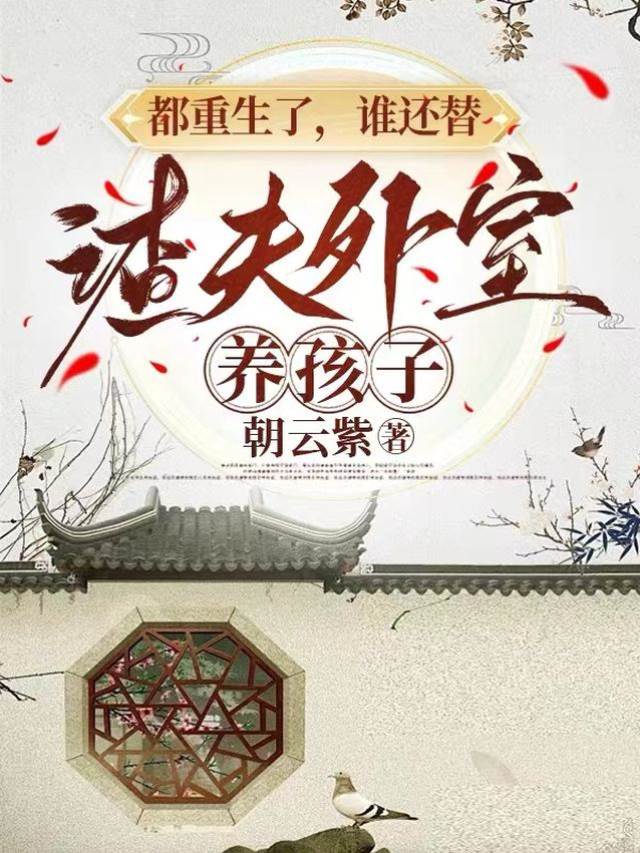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
完結222 章

霽月清歡
這日大雨滂沱,原本要送進尚書府的喜轎,拐了兩條街,送入了永熹伯府。 毫不知情的寧雪瀅,在喜燭的映照下,看清了自己的新婚夫君。 男子玉樹風逸、軒然霞舉,可一雙眼深邃如淵,叫人猜不透性情。 夜半雨勢連綿,寧雪瀅被推入喜帳,亂了青絲。 翌日醒來,寧雪瀅扭頭看向坐在牀畔整理衣襟的夫君,“三郎晨安。” 衛湛長指微頓,轉過眸來,“何來三郎?” 嫁錯人家,寧雪瀅驚愕茫然,可房都圓了,也沒了退婚的餘地。 所幸世子衛湛是個認賬的,在吃穿用度上不曾虧待她。 望着找上門憤憤不平的季家三郎,寧雪瀅嘆了聲“有緣無分”。 衛湛鳳眸微斂,夜裏沒有放過小妻子。 三月陽春,寧雪瀅南下省親,被季家三郎堵在客船上。 避無可避。 季三郎滿心不甘,“他……對你好嗎?” 寧雪瀅低眉避讓,“甚好,也祝郎君與夫人琴瑟和鳴。” 季三郎變了臉色,“哪有什麼夫人,不過是衛湛安排的棋子,早就捲鋪蓋跑了!雪瀅妹妹,你被騙了!” 寧雪瀅陷入僵局。 原來,所謂的姻緣錯,竟是一場蓄謀。 衛湛要的本就是她。
32.7萬字8.25 149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