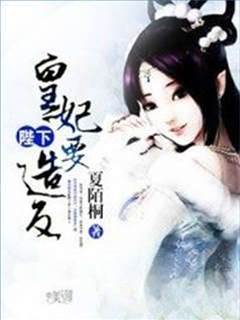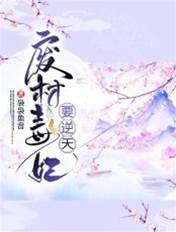《盛唐風月》 第1167章 王忠嗣賜鴆事件
杜士儀離開長安的時候,並沒有驚天子遣左相裴寬以及文武員郊送,更沒有驚長安民,只是出城和僕固懷恩所部主力會合,悄然渡過渭水前往潼關。在這千軍萬馬渡河的時刻,一座灞橋就顯得有些不夠看了,郭子儀讓人搭好,杜士儀親自檢視過的那幾座浮橋便顯出了先見之明來。即便歷經了這麼多人馬的踩踏,幾座浮橋卻都堅實耐用,直到親自殿後的僕固懷恩從灞橋上渡過了渭水,這纔回頭看了一眼長安。
“等我們再回來的時候,便是安賊叛軍剿滅殆盡之時!”
千軍萬馬從道上呼嘯而過,長安城中,當得知杜士儀竟然就這麼走了,李隆基著手中那薄薄的奏疏,突然掀開被子坐直了,厲聲喝道:“陳玄禮呢?他還守著那些沒用的東西呆在馬嵬驛?磨蹭了這麼多天就是不見回來,難不他們是擔心回了長安,就要繼續在十六王宅過暗無天日的日子,還是擔心杜士儀手狠起來,連他們這些皇族一塊殺?”
這樣誅心的言辭,高力士不在,沒有一個人敢輕易接話。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方纔有一個站在榻尾的中年宦小心翼翼地說道:“回稟陛下,我剛剛去侍監見過高大將軍,說是因爲陳大將軍回程的時候,有不之前逃散的侍攔路哭拜請罪,請求帶他們回長安,所以路上就耽擱了……”
一聽到是當初那些棄了自己而逃的宦作祟,李隆基登時氣了個半死。他在馬嵬驛中惶恐不安的時候,曾經聽說過一種說法,如袁思藝這些宦之所以逃走,是因爲他們本就不看好退往蜀中後能夠收復中原,因此本就打算跑去投降安祿山!一想到是自己給予了這些侍高厚祿,結果大難來時他們卻拋下自己這個君王去投靠別人,如今見事不妙又轉回來想要求自己覆水重收,他哪裡咽得下這口氣?
Advertisement
他奈何不了杜士儀,難道還奈何不了這些不忠不孝的閹奴?
“之前那些逃兵如何了?”
那個說話的中年宦沒想到憤怒的天子突然略過那些侍不提,而是問北門軍中的逃兵,猶豫了一下方纔低聲說道:“僕固將軍吩咐人在四鄉張榜文,三天之回長安西城金門和延明門自首者,減兩等押送朔方戍邊,若是逾期不回,來日殺無赦。之前掃了三天,僕固將軍一共拿住了八百餘人,全都已經押送朔方戍邊了。”
李隆基雖也痛恨那些軍往日待遇優厚,遭遇大變時卻不是背叛就是譁變,可眼看飛龍廄中多了一支那樣如鯁在的飛龍騎,他就算著鼻子,也需要相應的兵馬來抗衡。可還不等他預備施恩,僕固懷恩竟是自作主張把人送去了朔方!他只覺得心中那團火越燒越旺,當即冷冷說道:“去告訴裴寬,北門四軍乃是天子軍,就算犯了重罪,也自有朕這個天子來決斷,不到別人來越俎代庖!”
如果杜士儀和僕固懷恩以及那支大軍還在長安,李隆基也許還能繼續忍耐下去,可現如今他卻一刻都不想再忍。杜士儀想要帶兵就讓他去,趁著人不在長安,他如果不能把輿論以及大局完全掌控,回頭等他們大捷而歸的時候,他豈不是要更加被了!
“是,奴婢立刻就去傳話。”
見那中年宦答應一聲便要往外走,李隆基想起偌大的宮殿中,只有這唯一一個人回答自己的話,他便又將其住:“你什麼名字?”
“回稟陛下,奴婢程元振。”
李隆基微微一頷首,等到人快步去了,他方纔輕輕舒了一口氣,決定趁著杜士儀離開這段日子,儘快養好,儘快把朝中人事重新梳理一下。就算他現在不可能把兵權從杜士儀手中奪回來,可將來卻一定要設法拿回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Advertisement
然而,程元振一去就是一個多時辰,直到李隆基幾乎認爲他出了什麼不測,他方纔踏了大殿,面上竟是又驚惶又焦慮。面對李隆基那不耐煩的表,他不敢立刻開口,而是用眼神示意天子屏退了四周圍的人之後,方纔在榻前雙膝跪下,隨即低了聲音說道:“陛下,奴婢萬死,到了政事堂見到裴相國時,不敢轉述陛下的口諭。”
見李隆基那目一下子變得如同刀子似的,程元振卻顧不上害怕,咚咚磕了兩個頭後,這才帶著哭腔說道:“奴婢並不是擔心惹怒了裴相國,這纔不敢轉述,而是因爲山南道益昌太守王忠嗣命人送來了書呈文,說是有人冒陛下詔令,給他送去了鴆酒!”
李隆基之前在杜士儀上書請求重新啓用王忠嗣時,一度當了鴕鳥含糊過此事,當這個消息鑽耳朵的時候,他不由自主抓住了下那錦繡被褥,腦際轟然巨響,甚至連吞嚥唾沫的力氣都沒了。人人都知道王忠嗣曾經在宮中長大,是他這個天子的養子,而他更清楚王忠嗣那絕不會質疑君父的子。如果有鴆酒送到,王忠嗣肯定會想都不想就仰藥自盡,又怎會命人送上書陳?他又不是杜士儀!
竭力穩定了一下緒後,他終於恢復了開口的力氣,眼神兇狠地問道:“此事有多人知道?”
程元振當然知道天子是什麼意思,可是,想到自己去政事堂時,那裡竟是彷彿東西兩市一般沸反盈天,彷彿有頭有臉的文武員全都到了,即便他不想說出這樣的消息來刺激李隆基,還是不得不盡量含含糊糊地說道:“奴婢去政事堂時,那裡有數十人。”
十一個人也是數十,而七八十人也能說是數十!
Advertisement
李隆基重重捶在了牀板上,厲聲問道:“到底有多人?”
被質問到了這個份上,程元振再也不敢避重就輕:“中書省門下省五品以上,尚書省六部尚書侍郎和左右丞,十六衛大將軍,以及四品以上的各寺監職事,全都在。而且,益昌太守王忠嗣連送鴆酒的人都給押送了回來。”
糟糕了!
李隆基無論如何都難以想象,一貫忠義的王忠嗣竟然會採取這樣激烈的舉。剛剛纔經歷了慘烈的圍城一役,長安城中民百姓只怕有很多人還在怨尤他這個天子,沒能隨駕同行的文武員也有很多心存怨言,王忠嗣的這一舉就猶如在熱鍋裡澆下了一瓢滾油,直接把他架在了火上烤!天下是他的天下,爲什麼一個一個人都會接連背叛他,爲什麼?對了,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當初授意人去送鴆酒的時候,並沒有帶去詔書,只是口諭!
這樣看來,如若裴寬真的把這件事捅到前,他直接將責任推到楊國忠矯詔上就行了!
因爲這樣一樁突發事件,李隆基沒有心再去追究僕固懷恩將逃亡軍遣送到朔方戍邊,只想著如何將這件事平息下去。然而,他本沒有想到,政事堂中在最初的沸反盈天之後,裴寬卻在嘆了一口氣後,鄭重其事地衝四面八方拱了拱手道:“各位,著實沒想到楊國忠竟如此膽大妄爲,居然矯詔謀害國之大將!幸而王忠嗣察其,否則我大唐又要折損一員大將!”
杜士儀臨走前讓崔承訓轉告的話,王縉已經都收到了,他因爲太子李亨的死而大爲挫,此前大病了一場,崔九娘卻又和他鬧彆扭回孃家,如今的他看上去頗有幾分消瘦。如果只是李亨死了也就算了,偏偏張良娣爲了挽救李亨的命,把廣平王和建寧王都一塊坑死了,他如今就算在宗室當中燒冷竈,卻也已經晚了。而且,杜士儀拋出橄欖枝的同時,甚至表示要用自己的兄長,他不得不端正一下態度。
Advertisement
從前杜士儀只是封疆大吏,可現在卻是一言一行便可令大唐風雲變的權臣了!
所以,他見四周圍衆人無一吭聲,突然低聲說道:“依我看,此事還是快刀斬麻,立刻以矯詔之罪將這幾個去過益昌郡的人死。另外,爲了避免長安軍民因此誹謗君父,不若復王忠嗣職,令其節度河西,抵吐蕃!安思順曾爲王忠嗣麾下大將,料想舊日上司重新復職,也就不用擔心高達夫制不住他了。”
儘管大多數人都知道,給王忠嗣送去鴆酒的事絕不可能是楊國忠矯詔,一定是天子因爲安祿山那一句擁戴太子的口號,而真的產生如此心意,可現如今李隆基的昏君名聲已經都快鐵板釘釘了,再多上這麼一件事,只會更加麻煩。所以,即便爲王忠嗣鳴不平的人,也覺得與其鬧騰出來審訊不休,還不如快刀斬麻讓王忠嗣復職,如此則再無需擔心河隴那邊吐蕃是否會趁虛而。
於是,在裴寬點頭贊同之後,政事堂中清一全都是附和的聲音。可直到衆人散去,這麼一件事的餘音依舊未平。三省六部各寺監無不用著數以千計的流外吏員,消息在這些人當中的流速度是最快的。就在這一天太落山,城門閉鎖宵之前,如此消息就如同龍捲風一般席捲了長安城一百多個裡坊,甚至連坊間小民都知道,王忠嗣被賜鴆酒之事。天子對此裝聾作啞,朝中那些大人們則打算息事寧人,殺了執行者,然後讓王忠嗣復職。
天底下還有沒有天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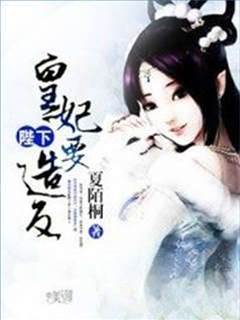
陛下,皇妃要造反!
她獻計,逼他娶她爲妻.他卻在大婚之夜,紅羅帳前,將她賜給王府的下人. 她睿智,助他登上皇位.他卻在封后之時,宮門之前,賜她一夜長跪,賞一夜春雨,聽一夜纏綿聲. 她妖嬈,他便藉此命她出使雲容國,引誘雲容皇,換取相思引,只爲他愛的那個女子. 一場大火之後,她不再是她,卻依舊記著那個愛他,護他的使命.一步一步,再度淪爲他的棋子. 傾心的付出,換來的竟是一場步向死亡的盛宴;徹底的給予,得到的竟是一杯奪人性命的毒酒.恩愛,纏綿,背棄,凌辱,身亡… 容華謝後,君臨天下,只是他身邊再也不會有一個她.他這才明白真正的相思之意.這次,終於還是該他償還她了;這次,終於也該他爲她尋求相思引了…
66.6萬字8 16711 -
連載1728 章

神棍娘子:狀元相公不信邪
淩相若是現代天才玄學研究者,口無遮攔被雷劈到了異世一個叫華亭縣的地方。易玹是安國公世子,金科武狀元文探花,主動申請外放華亭縣調差賑災銀失竊案。一個是神棍,一個不信邪,天生相斥卻偏偏成了親!淩相若:“聽說你是冇考中狀元,冇臉在京城待下去才跑出來的?哎,你要是早點到本小姐裙下拜一拜早穩了。”易玹:“胡說八道,我就是狀元!”淩相若不解:“你不是探花嗎?”易玹:“武狀元比文狀元更厲害,要不你試試?!”
312.7萬字8 21743 -
完結2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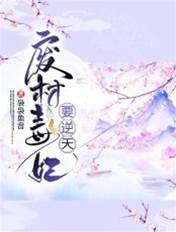
廢材毒妃要逆天
驚!盛家嫡女和三王爺新婚之夜,竟是在亂葬崗完成的!一朝穿越,她成了三王爺的嬌妻,成了天下笑談?笑話,她可是醫毒雙修,逆天醫術救死人,醫白骨的妖孽。憑借一雙素手從墳場的泥濘裏爬出來,她勢要將欺她,辱她,害她的渣渣虐到跪下唱征服!等等,旁邊墳坑裏怎麼還有一個男人?盛明畫看到美男子頓時沒了硬氣,“夫君!夫君別急!我這就給你挖出來!”盛明畫像拔蘿卜一樣把活閻王三王爺給拔了出來,但拔到一半的她頓感不妙。迎著某人刺刀的眸子,盛明畫逃之夭夭,“大恩不言謝,王爺不必謝我挖了一半的恩,後會無期!”某人:“找死!”
239萬字8.18 50793 -
完結226 章

予千秋
定安十八年,謝王府父子二人戰死沙場,滿門忠烈唯餘小女謝瑤一人尚存人世,帝憐謝王遺孤,下旨將謝瑤賜婚與東宮太子。 偌大的王府倒下,謝瑤如風雨中的浮萍,百日守孝後嫁入了東宮。 一時人人悲憫,人人笑話。 悲謝瑤孤女無依,又笑太子體弱多病東宮早晚易主,怕是要孤女配病秧子,再成可憐寡婦,守着一家子靈位過活。 * 初入東宮,謝瑤處處低調地做着隱形人,本想和這位病弱溫和的太子相敬如賓,日後等他病逝或者登基,也能得個清閒日子安安穩穩地過後半輩子。 誰料顧長澤今天頭疼召她侍疾,又是高熱又是咳血,她不得已留宿貼身照顧,兩人夜夜同床共枕,明天又婉言拒絕了皇帝讓他納妾的好意,說他久病難愈不想拖累別人,東宮有一位太子妃就夠了。 於是民間一邊感嘆這位病秧子太子只怕要英年早逝,一邊又盛傳太子寵愛太子妃,兩人同進同出好一對眷侶。 流言甚囂塵上,謝瑤擔心太子身上落個“懼內”名聲,便善意提醒。 顧長澤對她溫和一笑。 “孤久病不想拖累你,若他日病逝,就向父皇請願還你自由之身。 流言是外面的人亂傳的,你且等等,孤找人擺平這些。” 可謝瑤左等右等,沒等到顧長澤病逝,也沒和他相敬如賓,反而等來了他病好,奪位登基,又在衆目睽睽之下,給她套上了鳳袍。 謝瑤:嗯?不是病秧子嗎?! * 宮變那天,滿地鮮血流到謝瑤腳下,背對着她的那人將長劍拔出,一轉頭和她四目相對。 謝瑤驚恐畏懼地瑟縮了一下,顧長澤漫不經心擦去手上的鮮血,踩着滿地屍骨走到她面前,在她額頭上落下個冰涼的吻。 “別怕。” 彼時她才知,那些流言全出自東宮書房,溫和無害的皮囊,不過是他陰鷙殘忍的掩飾,所以這世上怎麼會有他擺不平的流言?甚囂塵上,不過是因爲他願意聽。 什麼自由之身,都是空話。 他對她,早有所圖,蓄謀已久,從來就沒打算放手。 “她陪我走過漫漫長夜,見皚皚飄雪皇權鐵戈,從東宮太子,到君臨天下。”
32.6萬字8.33 186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