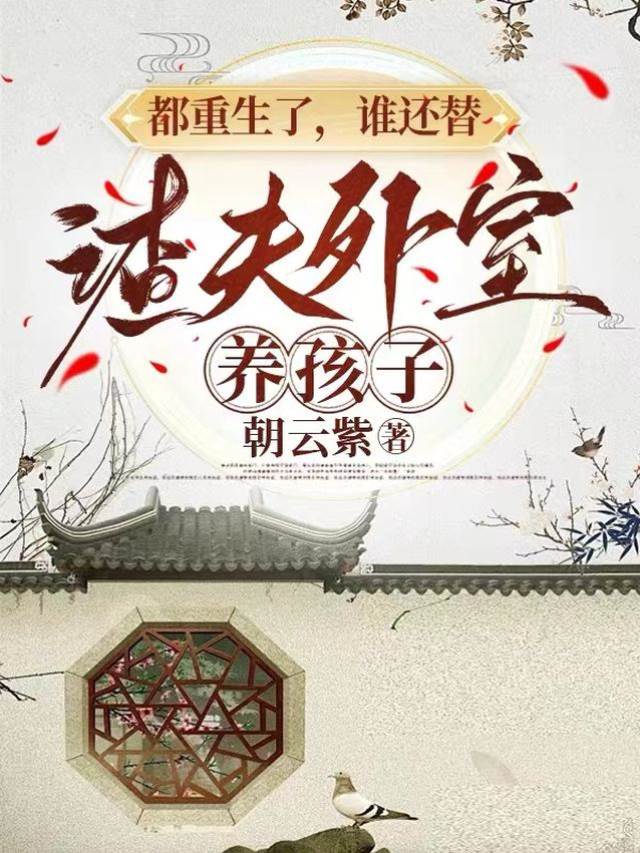《邪帝狂妻:醫妃傾天下》 第九十八章:絕無可能
算起來,從懷徇謹囚我到現在,已經將近兩個月,而我幾乎再未與他說過話。
可是今夜,聽著他的話,我突然冷笑:“呵,懷徇謹,你得了我的子,眼下竟還想要我的心嗎?!”
借著約從窗外投下的月,我看著自己手腕上因長期被捆綁,而產生的難以消除的淤青,盡力無視那只橫在腰上的手。
一聲嗤笑就在邊綻放:“懷徇謹,我的人一直都不是你,以前、現在、未來。若有可能,你就囚我一輩子吧。”
這兩個月,懷徇謹幾乎夜夜求歡,我的嗓子已經沙啞,說話時聲音嘔啞嘲哳,很是難聽。
懷徇謹良久未曾說話,就在我以為他已經放棄和我流的時候,他突然開口:“芊芊……你可知,人這一生,不可能只一個人?”
“……”
“我和阿珮,你和他,我們這兩對都不是彼此的良人,所以即便是曾經深,也會從各自的生命中消失。芊芊,只有你我的命運,是纏繞在一起的,我們是注定分不開的。”
Advertisement
我不知他哪里來的自信,已經不想再和他多說一句話了。
“芊芊,同樣的人,就該擁抱,才能呼吸,才能存活。我們是同類人,不論你如何排斥,也無法否認這個事實。”
說完,他就側睡去了。只是那一只v沉重的手臂還橫在我腰上,半點都沒有要拿開的意思。
濃濃的氣息,夾雜著懷徇謹上的清茶香,在這個大殿中彌漫開來。
臨睡前,他說:“芊芊,為我生個孩子吧。”
說完,便傳來了細微的鼾聲。
最終只留下我一人,徹夜未眠。
這一夜,我想了很多。逸哥哥我大抵是再也沒有機會和他在一起了,可是我必然是不能留在這里和懷徇謹生孩子的。
所以我一定要出去。
只是此地防守嚴,憑我一人之力想來是難有機會跑出去……
這一想,就到了第二天早上。
Advertisement
懷徇謹早上自己起床,換好朝服后,轉對我道:“芊芊,我昨晚說的……你好好想想。”
“絕無可能。”
原本裝睡的我,睜開眼睛,兩個月來第一次直視懷徇謹,看著他漆黑如墨的眼眸,我再次冷冷道:“絕無可能。”
聞言,他瞇起雙眸,語氣不明的說:“你……不愿意為我生孩子嗎?即便這孩子未來繼承我的位置,即便他會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你也不愿意?”
我再次閉上眼,不再說話。
故而他留下一聲淺淺的嘆息,就離開了。
我躺在床上,怔怔看著天花板上復雜的花紋,還有上面纏繞的紅線,以及紅線上懸掛著的鈴鐺。
現在的我,上天無路,下地無門。
我,怎麼才能離開這里?
莫非當真要留在這里一直做懷徇謹的下之臣嗎?!
我有些迷茫,迷茫中下意識去挲上最后一件我自己的東西——一個紅瑪瑙的戒指。
Advertisement
當初我的藥箱、做人皮面的那些家伙事兒,早在一個月前就被懷徇謹全部搜走了。只留下這一只戒指,大抵是以為沒什麼用吧?
呵呵,還好,我上向來沒什麼無用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81 章

奪嫡
他將她囚禁。背叛,滅族,辜負。她死于一場蓄謀已久的大火。燒到爆裂的肌膚,寸寸誅心的疼痛和撕心裂肺的呼喊,湮沒在寂寂深宮。重生歸來。她卻只記得秋季圍獵的初遇,和悲涼錐心的結果。人人避之不及的小霸王,她偏偏要去招惹。一箭鎖喉搶了最大的彩頭,虞翎…
45.9萬字8 106515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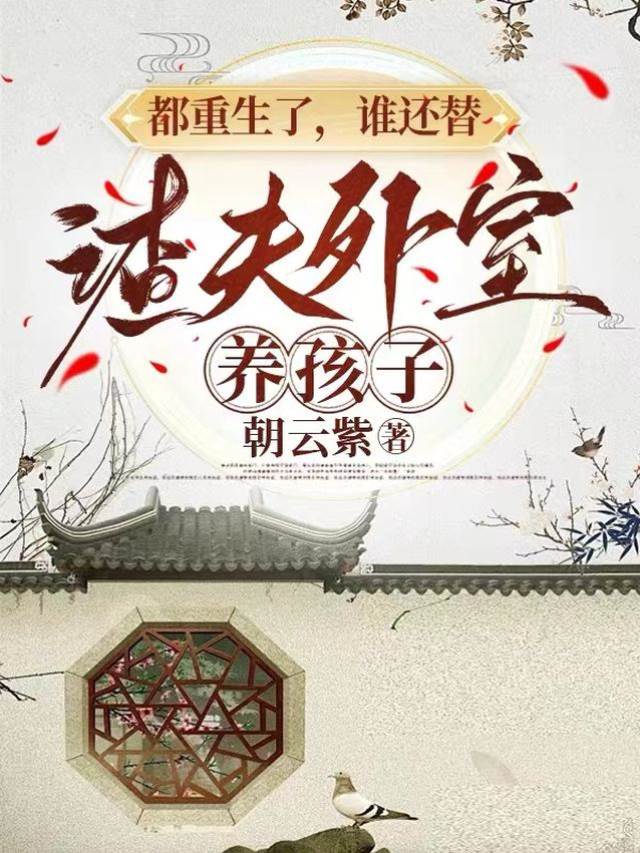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
完結222 章

霽月清歡
這日大雨滂沱,原本要送進尚書府的喜轎,拐了兩條街,送入了永熹伯府。 毫不知情的寧雪瀅,在喜燭的映照下,看清了自己的新婚夫君。 男子玉樹風逸、軒然霞舉,可一雙眼深邃如淵,叫人猜不透性情。 夜半雨勢連綿,寧雪瀅被推入喜帳,亂了青絲。 翌日醒來,寧雪瀅扭頭看向坐在牀畔整理衣襟的夫君,“三郎晨安。” 衛湛長指微頓,轉過眸來,“何來三郎?” 嫁錯人家,寧雪瀅驚愕茫然,可房都圓了,也沒了退婚的餘地。 所幸世子衛湛是個認賬的,在吃穿用度上不曾虧待她。 望着找上門憤憤不平的季家三郎,寧雪瀅嘆了聲“有緣無分”。 衛湛鳳眸微斂,夜裏沒有放過小妻子。 三月陽春,寧雪瀅南下省親,被季家三郎堵在客船上。 避無可避。 季三郎滿心不甘,“他……對你好嗎?” 寧雪瀅低眉避讓,“甚好,也祝郎君與夫人琴瑟和鳴。” 季三郎變了臉色,“哪有什麼夫人,不過是衛湛安排的棋子,早就捲鋪蓋跑了!雪瀅妹妹,你被騙了!” 寧雪瀅陷入僵局。 原來,所謂的姻緣錯,竟是一場蓄謀。 衛湛要的本就是她。
32.7萬字8.25 149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