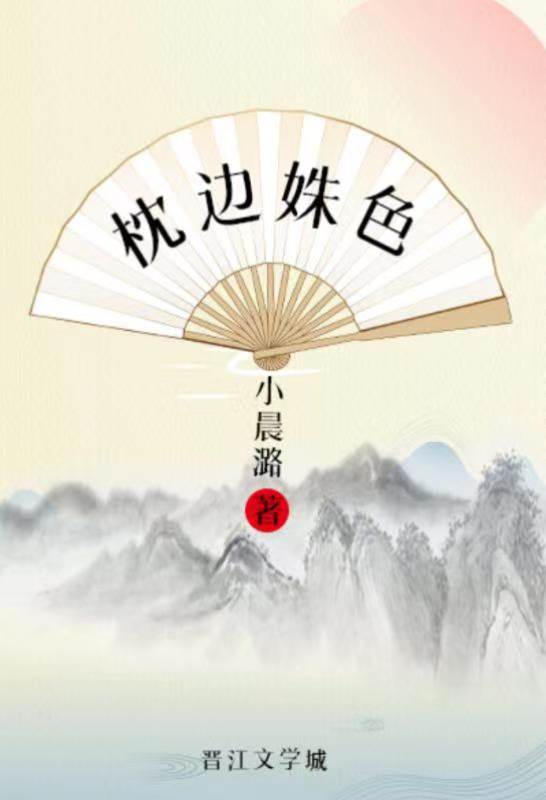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王妃,你的鞋掉了》 第一百一十三章欺人太甚
談話間終于抵達新月,遠遠看去,城樓輝煌氣派,與乾陵悅旅游時見過的古城復原圖有得一比。
“我以為這樣的驕奢逸只在國都。”直到城門名字掛到了的腦袋頂,才放下門簾坐回到馬車里,嘆著。
哪怕是京城的城門,也只是多了橙黃大旗,僅此而已。
“新月的富余怕是連京城都及不上。”項天禮淡漠地回答,在不可置信的眼神中多說了幾句,“新月商人居多,大多富可敵國,一個漂亮的城門,不算什麼。”
“那城主豈不是腰纏萬貫?”乾陵悅繼而推測。
“猜得真準。”他毫無靈魂地夸贊。
默默翻個白眼,末了又想到什麼似的,“這樣皇上也不管嗎?”
“他管不上,也沒能力。”項天禮說話直白,也不怕被人聽了去。
乾陵悅細思下很容易理解,項天仁新帝上任,周遭挑釁不斷,唯有先集中力解決大事,才能騰出手來管理小頭。
不合時宜地生出對項天仁的同,那緒又迅速散去。
兩人直接去了城主住。
乾陵悅再度發出驚嘆,一個小小城主,居住之所卻富麗堂皇,比之皇宮有過之而無不及,口的擺飾做工細,稍微多看了一眼,蔽刻著一個微弱的痕跡,眼睛放大。
拉了拉項天禮的角,低聲道,“這里的擺飾與皇宮里的出自同一個工匠。”
這本該是可以拉出去砍頭的事了,但城主仍然大大方方地擺著,有炫耀之意。
“嗯。”他并不意外,淡定地跟在丫鬟后面。
乾陵悅的注意力這才從擺飾拉到丫鬟上,愣了一瞬,不可置信地又仔細盯著看了一眼,這服用料未必也太奢華。
Advertisement
依稀記得柜子里也有幾套這樣用料的服,雖不算極貴,但也不是一般丫鬟都能配備的,就連王府里的丫鬟,也都是比這下等一些的布料。
“可以收一下你的眼神嗎?”項天禮實在看不過去,提醒著。
忙收起看的視線,垂首跟在丫鬟后,瞬間收斂。
城王府比想象的要大,跟著丫鬟走了將近半刻鐘,城王府的主殿才屹立在眼前。抬頭看著高聳云的門,一時呆住。
進來時外面明明是平原,怎麼后面藏著座這麼高的山?
項天禮暗自嘆口氣,強行攬著的肩,喚回離的神志。
“城主,人帶到了。”丫鬟的聲音也格外清亮,比其他自帶卑微的丫鬟要正常許多。
乾陵悅倒是對這樣的人頗有好,至不會無端卑微。
“嗯。”站在臺階上的城主揮手示意下去。此人長相獷,材高大,舉手投足之間盡是糙漢氣質,全卻穿金戴銀。
在乾陵悅眼里就是活的暴發戶形象。
擺完架子,城主才緩緩踱下臺階,走到項天禮邊,笑得像在看小輩似的,“安王爺,好久不見。”
“的確好久不見。”項天禮抿著客套的笑,沖他頷首,不聲地與他并肩。
乾陵悅乖巧地跟在他后,謹記項天禮的教育,沒有沖行事。
“安王妃出落得更婀娜多姿了。”城主的視線越過他投到上,帶著讓人不舒服的打量,乾陵悅皺眉,覺他像極了路邊的混子,不過相對來說財大氣而已。
察覺到的不悅,項天禮不著痕跡地擋住城主看過去的視線,將護在自己后,態度堅決,“我們不如里面說?”
“瞧我這記,許久不見安王爺,連禮數都忘了。”城主一拍腦門,臉上卻沒有半分懊惱,甚至還有微微的得意。
Advertisement
小人得志。乾陵悅默默在心里點評,因著剛才他那一眼,對他印象特別不好,自然帶了更深的偏見。
城主在前面帶路,項天禮與乾陵悅跟在后,一路上路過幾個侍衛,看他們的眼神都不怎麼恭敬,反而含著淡淡的嘲諷與不屑。
城王府里的珠圍翠繞再也提不起乾陵悅任何興趣,忍著怒氣,悶聲跟著進了主殿。
“上座。”城主說這話的時候只是隨意了手,半點禮數都沒有。
向來眼里不得沙子,更何況對方已經是明面上的挑釁,不回豈不是任由他們欺,“看來城主的確是半分禮數都不記得了,不過新月城富碩無比,應當也不缺禮數教典。”
萬萬沒想到會被反駁的城主坐下的姿勢半途停住,轉頭看著,作十分稽,“安王妃好機鋒。”
“你說機鋒不機鋒的,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北楚有北楚的規矩。”乾陵悅選擇直接剛,新月到現在沒有離北楚,必然有他的原因。
比如鄰國暮五不夠強大到替他對抗北楚。
城主臉微變,項天禮下意識起,替乾陵悅道歉,“悅兒極與我出門,諸多得罪之,還清城主諒解。”
“安王妃也是護主心切,可以理解。”城主冷哼著。
這下兩人臉都難看起來,護主心切?把比作什麼?
剛要再糾正,被項天禮暗中牽住手,緩緩搖頭,示意不要輕舉妄。
“不知二位貴客有何要事?”自以為扳回一城的城主得意洋洋地坐在高位上,大手一揮,示意丫鬟給自己倒酒。
主殿里的丫鬟明顯比外頭的丫鬟高了不止一個等級,相貌材更是上乘。
邊有丫鬟接近,項天禮自覺抬手,誰知丫鬟竟然一轉,為隔壁大臣模樣的人倒起了酒,最后一圈倒完都沒有理會他們倆。
Advertisement
簡直欺人太甚。
乾陵悅一錘桌面打算發作,城主卻搶過話頭,“丫鬟不知禮數,還請二位自行斟酒。”
“城主,原來這就是您的待客之道。”他的話并沒有阻止的冷嘲熱諷,“連我府上的下等婢都知道來人尊貴時須得盡心盡力,以保住自家主子的面,這麼看,您的丫鬟倒是不怎麼未您著想啊。”
這一番話里先是一通比較,將他的人府邸及下人貶的一無是,再反咬一口,讓他臉面盡失。
城主只是一個大糙漢,皮子功夫自然不如乾陵悅,被懟得一愣一愣的,一句話都說不出。
項天禮一邊覺得解氣,一邊又擔心城主盯上,再度出來打圓場,言辭溫和,“悅兒只是氣不過貴府下人趾高氣揚,對您并無任何異議。”
這話說了等于白說,含沙影地罵著他教導無方,才有這樣的丫鬟。
在場被懟的丫鬟們臉一白,十分不悅,紛紛瞪著乾陵悅,恨不能把活生生盯死,至于項天禮,又有哪個人會和那張俊俏的臉蛋作對呢?
若非在他們來之前城主再三叮囑不要給好臉子,多酒們都能給他斟完。
與此同時,乾陵悅算是正式引起了城主的注意,城主靠在座位上,原本雙手支在膝蓋上,現在改為一只腳搭在座椅上,另一只腳踏在地上,以對著他們。
這是極為不禮貌不尊重的坐法,可見他對項天禮的輕蔑。
遠在乾陵悅預料之外的狀況使的樂觀降到谷底,看來此行不會順利,說不定對方還會順手藏陳氏真實去向。
原本就在邊的問話重新吞回去,笑瞇瞇地繼續,“我與王爺此番來,便是驗一下新月城的風土人,久聞新月城風花雪月,卻沒有想到城主待客之道差強人意。”
Advertisement
話里沒有毫討好,甚至還故意對著干。
城主眼中帶著玩味探究,“王妃可知如此詆毀我的后果?”
“那你可知如此詆毀我的后果?”到底初生牛犢不怕虎,與他針鋒相對。
項天禮已經放棄圓場,默默計劃著等下落腳后便往京城寫封信,趁早人過來支援。
“王妃果然是爽快之人。”城主忽然臉一變,起端著酒一步步走下來,神莫名,一眼都沒有看項天禮,直直停在跟前,“不如與我對酌一杯,之前的冒犯便一筆勾銷。”
這不是變相讓道歉?又沒有錯,道歉豈不是荒謬。
“我想城主搞錯了什麼,”直起,目堅定地與他對視,毫不避讓,“這件事當是您的丫鬟向我們道歉。”
圍觀的人早就呆住。
出門在外,講究鄉隨俗,哪怕他們是京城來的也不例外。新月城有新月城的規矩,誰來都是一樣對待。
至接待客人這麼久,還沒有敢和城主板的人。
項天禮扶額,任由乾陵悅發脾氣。
城主瞇眼仔細打量著這個小丫頭,之前也見過面,但那時候的人溫順可,大型場合一聲不吭,典型的大家閨秀,怎的現在如此火?
不過,他喜歡。
曾經乾陵悅還未嫁王府時,城主便向先皇求過親,理所當然被相國大人拒絕,此后回到新月,也時時刻刻想著。
“城主,請道歉。”乾陵悅不知他心里齷齪的想法,冷靜迫。
城主臉忽的一變,爽朗一笑,“是們的疏忽,”說著冷聲,“過來,道歉。”
丫鬟們戰戰兢兢地走過來,高低不一地道了歉。
城主卻又道,“手都出來。”
一雙雙白玉蔥手出。
乾陵悅詫異地看了一圈,心說這里流行小學課堂里的打手掌心?
原本坐著的項天禮陡然起,嚇了一跳,聽他沉聲道,“城主,不必如此。”
“們冒犯了您,自然需要的。”城主說著猛地拔出腰間佩刀,手起刀落,乾陵悅剎那間明白他要做什麼,眉頭鎖,閉上眼睛。
“錚……”刺耳的兵相接聲刺激著的耳,睜開一條,項天禮正單手執劍擋住城主來勢洶洶的刀。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4 章
錯嫁皇妃帝宮沉浮:妃
一夜承歡,失去清白,她卻成了他代孕的皇妃。紅綃帳內,他不知是她,她不知是他。紅綃帳外,一碗鳩藥,墮去她腹中胎兒,她亦含笑飲下。惑君心,媚帝側,一切本非她意,一切終隨他心。
64.9萬字8 15557 -
完結568 章

爽翻天!穿到古代搬空國庫去流放
【空間 女主神醫 女強 爽文 虐渣 發家致富 全家流放逃荒,女主能力強,空間輔助】特種軍醫穿越古代,剛穿越就與曆史上的大英雄墨玖曄拜堂成親。據曆史記載,墨家滿門忠烈,然而卻因功高蓋主遭到了皇上的忌憚,新婚第二日,便是墨家滿門被抄家流放之時。了解這一段曆史的赫知冉,果斷使用空間搬空墨家財物,讓抄家的皇帝抄了個寂寞。流放前,又救了墨家滿門的性命。擔心流放路上會被餓死?這不可能,赫知冉不但空間財物足夠,她還掌握了無數賺錢的本事。一路上,八個嫂嫂視她為偶像,言聽計從。婆婆小姑默默支持,但凡有人敢說赫知冉不好,老娘撕爛你們的嘴。終於安頓下來,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紅火。墨玖曄:“媳婦兒,我們成親這麼久,還沒有洞房呢!”赫知冉:“想洞房,得看你表現。”墨玖曄:“我對天發誓,一輩子心裏隻有你一個女人,不,下輩子、下下輩子也是。”赫知冉:“你說話要算數……”
104.2萬字8.43 421630 -
完結347 章

娘娘總是體弱多病
邰家有二女,長女明豔無雙,及笄時便進宮做了娘娘 二女卻一直不曾露面 邰諳窈年少時一場大病,被父母送到外祖家休養,久居衢州 直到十八這一年,京城傳來消息,姐姐被人所害,日後於子嗣艱難 邰諳窈很快被接回京城 被遺忘十年後,她被接回京城的唯一意義,就是進宮替姐姐爭寵 人人都說邰諳窈是個傻子 笑她不過是邰家替姐姐爭寵的棋子 但無人知曉 她所做的一切,從來不是爲了姐姐 所謂替人爭寵從來都是隻是遮掩野心的擋箭牌 有人享受了前半生的家人寵愛,也該輪到其他人享受後半生的榮華富貴
52.3萬字8 52 -
完結3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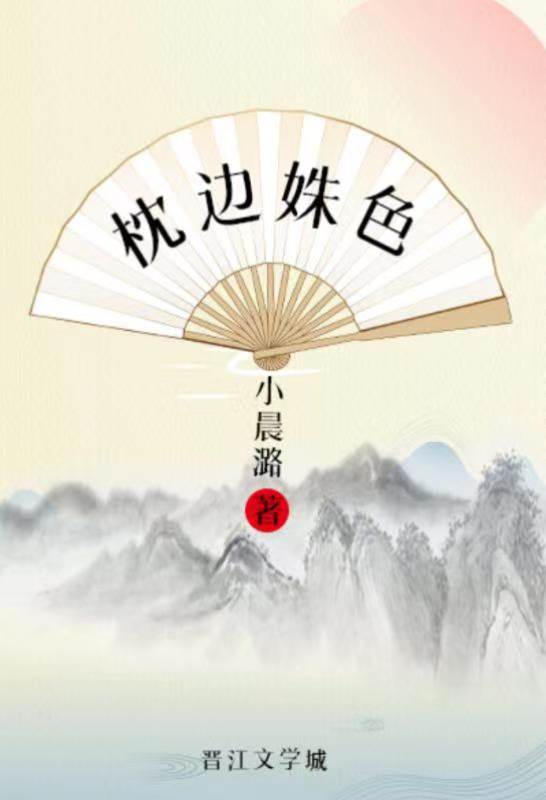
枕邊姝色(重生)
阮清川是蘇姝前世的夫君,疼她寵她,彌留之際還在爲她以後的生活做打算。 而蘇姝在他死後,終於明白這世間的艱辛困苦,體會到了他的真心。 得機遇重生歸來,卻正是她和阮清川相看的一年。她那時還看不上阮清川,嫌棄他悶,嫌棄他體弱多病……曾多次拒絕嫁給他。 再次相見。蘇姝看一眼阮清川,眼圈便紅了。 阮清川不動聲色地握緊垂在身側的右手,“我知你看不上我,亦不會強求……”一早就明白的事實,卻不死心。 蘇姝卻淚盈於睫:“是我要強求你。” 她只要一想到這一世會與阮清川擦肩而過,便什麼都顧不得了,伸手去拉他的衣袖,慌不擇言:“你願意娶我嗎?”又哽咽着保證:“我會學着乖巧懂事,不給你添麻煩……我新學了沏茶,新學了做糕點,以後會每日給你沏茶喝、給你做糕點吃。” 她急切的很,眸子澄澈又真誠。 阮清川的心突然就軟成一團,嗓音有些啞:“願意娶你的。” 娶你回來就是要捧在手心的,乖巧懂事不必,沏茶做糕點更是不必。
58.5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