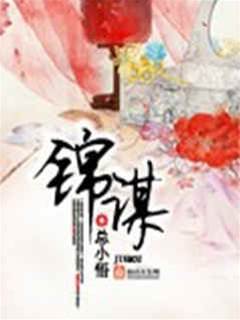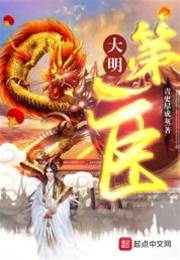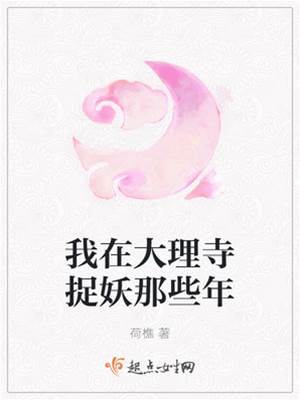《回到大明當才子》 第61章 張青天斷案(上)
「笨!王紀和鄒元標都是東林黨的人,他們當然不會把這條可以幫你減輕罪名的口供記錄——如果記錄了,王化貞就得和你共同承擔擅自撤回山海關的罪名了。」張大爺心中冷哼,又轉向周應秋問道:「周大人,這事你有印象嗎?」
「有。」正有希升任尚書的周應秋果斷點頭,答道:「有這事,下記得清清楚楚,鄒元標鄒大人和王紀王大人都問過這個問題,熊廷弼也是這麼回答的——可王化貞卻矢口否認,說是熊廷弼命令他撤退,他是奉命而行!」
「那為什麼沒有記錄在案呢?」楊淵搶著問道。張大爺何等狡詐,馬上猜出楊淵是想把這個疑點攪大,最終把當時的首輔葉向高和左都史鄒元標、刑部尚書王紀都拖下水,把這個案子繼續攪大,牽連進越來越多的人,讓這汪水徹底攪渾,那這個案子的結案日期就遙遙無期了。所以張大爺當機立斷,馬上搶著說道:「周大人,是不是當時的書辦記了?」
說著,張大爺向周應秋使了個眼,周應秋會意,馬上答道:「哦,我想起來了,當時記錄的書辦正好急不在堂上,所以記了這點。」楊淵大失所,只能恨恨坐下,咬牙切齒的說道:「那個書辦,真該殺!」
Advertisement
「是人都會犯錯嘛,楊大人何必如此斤斤計較呢?」周應秋笑了笑,順便向張大爺表心跡,笑道:「就象當初的鄒元標鄒大人和王紀王大人一樣,本來我反對把熊廷弼和王化貞並論死罪,可他們堅持要定熊廷弼的死罪,二比一,我沒辦法只好同意。」——周應秋這話倒不是假話,當時他確實不同意把為楚黨的熊廷弼和為東林黨的王化貞並論死罪,可那時候的東林黨勢力實在太大,他又還沒有加魏黨,不敢得罪東林黨更不敢得罪王化貞背後的首輔葉向高,被迫同意了王紀和鄒元標的定罪,所以九千歲面前的大紅人張大爺這次給熊廷弼翻案,當時的主審周應秋現在既不敢反對翻案,也勉強算是彌補當年的過錯。
「上次刑部書辦記這點,就請李大人查一查責任人是誰,酌理。」張大爺迅速了解此事,又向眾人微笑問道:「張國公,宋公公,周大人,李大人,對了,還有楊大人,差點把你忘了。我覺得案非常清楚了,熊廷弼承認他沒有救援廣寧,也沒有組織軍隊死守寧前,而是選擇了率領遼東軍民撤回山海關,他對戰的判斷是對是錯辜且不論,關鍵是這一點——如果熊廷弼確實是在和王化貞商量、並且取得王化貞同意的況下才放棄救援廣寧和堅守寧前,選擇撤回山海關!那麼廣寧大敗罪不在熊廷弼,放棄遼東擅自放棄撤回山海關,罪責就應該由熊廷弼和王化貞共同分擔。這麼一來,熊廷弼的死罪是否就判得太重了一些?」
Advertisement
「對,如果熊廷弼和王化貞是意見才撤回山海關,那麼咱家也認為熊廷弼罪不當死。」監審太監宋金第一個附和。那邊香油泥鰍李養正和周應秋不敢隨便得罪張大爺背後的魏忠賢,也是一起點頭附和,楊淵雖然想反對,可一時之間卻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駁。而英國公張惟賢則盤算了良久,終於還是點頭說道:「本也同意張大人的意見,如果率領遼東軍民撤回山海關這一點,是熊廷弼和王化貞共同商量的結果——那麼判熊廷弼的死罪,就過重了。」
「很好,既然諸位大人和宋公公都沒有意見,那還楞著幹什麼?」張大爺故意不去看楊淵氣急敗壞的模樣,微笑說道:「把犯王化貞帶上來吧,讓他和熊廷弼對質。」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8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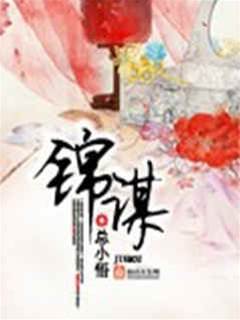
錦謀
古人說:天降大任必先苦心志。 晏錦哀呼,在這個勾心斗角的深宅,她只想護住父母。 苦心志……還是睡覺吧。 至于大任…… 天塌下來,不還有個他嗎?
147.5萬字8 22570 -
完結567 章
大唐好大哥
“母亡子降,手足相殘,十六年太子卒”這樣的歷史,我李承乾不服。“都說皇家無親情,我偏不信這個邪,我就要皇家,高堂滿座,兄敬弟恭,兒孫繞膝於前”
104萬字8 34007 -
完結92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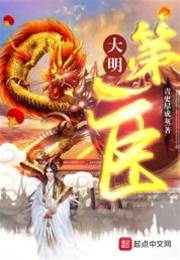
大明第一臣
元末濠州城外,朱元璋撿到了一個少年,從此洪武皇帝多了一條臂膀。抗元兵,渡長江,滅陳友諒,伐張士誠。創建大明,光複燕雲。 我無處不在。 從此洪武立國,再無遺憾。大明根基,固若金湯。 針對小明王的事情,我們需要采取四階段戰術。 首先,我們宣稱什麼事都冇有。 其次,我們說或許發生了什麼事情,不過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再次,我們說或許應該做點什麼,可惜什麼都做不了。 最後,我們很遺憾小明王以身殉國,當初要是做點什麼就好了。 …… 有人問:身為太祖第一心腹重臣,如何輕鬆避過風風雨雨,安享天年? 張希孟謙虛地說:“仆隻是大明朝卑微的社會公器,用來盛放太祖皇帝深思熟慮的果實!”
199.3萬字8 10136 -
連載8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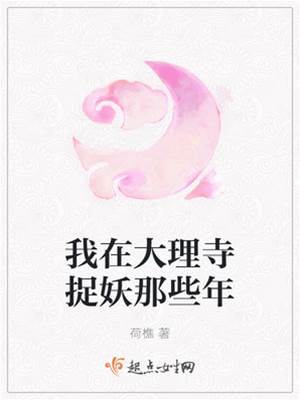
我在大理寺捉妖那些年
都說京城居,大不易。前往長安的道一,路上遇風雨,臨機起卦,觀之,樂之,“出行遇貴人,大吉大利呀。”其實這是一個小道士,與師父在線雙忽悠,想要去京城混日子,順便為九宵觀尋香客,遇見了行走的“百妖譜”。然而,混日子是不可能混日子的。很快,道一就明白了這個道理。......
150萬字8.18 313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