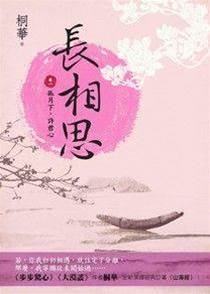《重生之庶女歸來》 第764章 一錯不能再錯
「對一個男子漢大丈夫而言,值得追求的事有很多,譬如財人啊,絕世武功啊,上古名劍啊,功名富貴啊……哦,富貴功名已被前任老侯爺一手包辦了,不用你追求了,咳咳,所以說段,你還有許許多多可以做的事。」
「給我鬆綁。」段曉樓要求。
廖之遠跟他講理:「讓綁你的人是老大,將你關進冰窖的也是老大,跟我一文錢的關係都沒有,自始至終我都沒阻礙到你,所以啊曉樓哥哥,千萬別記恨兄弟吶。」
「鬆綁。」
「今天一天你折騰得不輕了,不如睡一覺吧?我陪你睡?」
「鏈子,鬆綁。」
「你咬傷了我的手,我還反過來陪你睡覺,如何?我夠不夠意思?來,曉樓,給小爺笑一個。」
「松、綁。」
廖之遠無言天,只到一片冰雪屋頂,不由怨道:「何小妞啊何小妞,你活著的時候就是個麻煩人,怎麼人都死了還要惹這麼多麻煩?」
「鬆綁,否則等我能出去的時候,第一個要殺的人就是你、妹、妹。」
廖之遠打了個哆嗦,認真端詳段曉樓,沒有一要開玩笑的神。猶豫片刻,鬆了他的鎖鏈。
這裏是城北飲馬鎮上的白沙山莊,夜半子時。
昨日傍晚,陸江北在宮門口捉了段曉樓,先去安寧侯府向段母說了況,氣得葛夫人大罵,「逆子,逆子,快把他打死!」
陸江北用玄鐵鏈子加牛筋繩子捆了段曉樓,送房中。本要立刻進宮向皇帝請罪,不料還沒出侯府的門,就聽見一聲驚,是伺候段曉樓的丫鬟,「啊!不好了,侯爺不見了!」
段曉樓「不見」的方式,是直接在丫鬟眼前消失,床上瞬間只剩一堆繩子鎖鏈。
陸江北暗道不妙,段曉樓用了!
Advertisement
那種,是十年前廠衛花了重金從番邦異人手裏買回來的,到手之後有很多人練過。開始都能小有所,後面則非死即傷,存活下來的人還不到一,廠衛英登時損折去上百人!
陸江北和其他幾名資深武者,包括已死的蒙古相爺高君,細研后才發現,是廠衛買籍的時候騙了,拿到的只是一部殘籍,就算武學天分再高也不可能練。進一步推測,是某些人為了削減廠衛的勢力而做下的陷阱。此後,殘籍被封存在東廠地下書庫。
誰料不久前,居心叵測的曹鴻瑞引著高絕和段曉樓去練烽火功、這兩門。高絕覺不對勁就停了下來,勸段曉樓也別練了,後者不聽,強練下去,結果出了一場極其嚴重的事故,造的惡果一直還延續到今日。
此事只有陸江北和段曉樓兩人知道。
段曉樓最後練了,但陸江北與段曉樓約定,,今生今世只能再用三次。看來段曉樓早就打破了他們之間的約定。
分三重境界,第一重是,但形仍在,打鬥之中能捕捉到他的實;第二重是形,實消失。既然段曉樓能掙去鎖鏈,證明他用的是第二重形。陸江北不大急,形的後果,對段曉樓,對其他人,都只能帶來無盡的傷害!
九天十地搜魂,傳說中的邪異武功之一。廖之遠從前只是聽說過,頭一回見陸江北用出來,才見識到了那種令人咂舌的威力。整個侯府的草木全都連拔起,像剛遭遇了一場極地龍捲風。
最後總算搜出了段曉樓這不讓人省心的傢伙,一把鎖牢捆好,關進白沙山莊的冰窖里了事。
在段曉樓的威之下,廖之遠只好給他鬆了綁,引去見陸江北。畢竟老大就是老大,這時候最後可靠了,沒為何當歸之死而傷心到不統。
Advertisement
「老大,老大!我已經儘力拖住他了!段居然拿我家人的命作要挾,這差事沒法兒幹下去了!」隔著大老遠,廖之遠就先扯著嗓子告狀。相比之下,沉默不語的段曉樓就是吃虧的那個。
走進廳里,才發現不止陸江北一人,還有位神訪客,形高大,暗灰布罩衫,全上下遮得只剩一雙眼睛。
廖之遠見了卻大:「和尚齊玄余,你不用藏了,化灰我也認得你!」
訪客隔著一層布悶笑道:「廖施主好眼力,不過我扮這樣不是怕你認出,而是為了躲避『帝凰』的耳目。失禮之,還見諒!」
「啊?」廖之遠不信,「你不是『帝凰』的京城負責人嗎,你躲你自己?」
陸江北道:「山貓別鬧,機塵大師很有誠意同我們合作。」
段曉樓冷笑道:「齊玄余,你來得正好,我刀頭,正要用你頸上的熱來喂刀。拿出你的真本事來!」
齊玄余不急不怒地說:「段施主息怒,小僧正是聽說了你發怒的事,才特意來登門解釋,希能獲得施主的諒解,否則,小僧罪莫大焉!」
「諒解你個頭!」廖之遠代段曉樓言道,「他現在只恨不能變吸蝙蝠,吸所有人的,和尚你自己犯傻送上門來,莫怪咱們不講江湖道義,三個打你一個!——老大,你是我們這一派的,對吧?」
「阿彌陀佛!」齊玄余問,「如果小僧說,何當歸尚在人世,段施主依然要取小僧命嗎?」
「你說什麼?!」段曉樓雙手扣住齊玄余的脖子,用力搖晃。
廖之遠:「可你門下弟子說,何當歸讓人給生吞活剝了,死無全。和尚你又來說沒死,你耍我們玩呢?」
「小僧不打誑語,句句屬實。」齊玄余避重就輕地說。
Advertisement
「那就是你的弟子在撒謊?」廖之遠不依不饒。段曉樓一掌送他上房頂涼快,搖晃著齊玄余問:「你說沒死?你沒騙我?在哪兒?」
「阿彌陀佛,的去向還不清楚,但應該尚在人世。」齊玄余解釋道,「何當歸被擄走之後,小僧因為自己制於人,不能直接出手救,就讓弟子遜也通知孟七公子。誰知七公子的人馬遲遲未到,遜也一心想幫小僧離魔窟,藉著這份私心,竟跑去告訴段施主『何當歸已死』,想騙段施主與小僧聯手,推倒帝凰老巢,小僧也就落了自由。小僧也是半個時辰前才得知,沒能及時阻止段施主,小僧慚愧不已。」
段曉樓揭開面罩,瞪著齊玄余口中吐出的每個字,末了還是搖晃他,問:「活著?你怎知道還活著?」
廖之遠從屋頂的裏探頭,涼涼道:「人比野人還兇,喜歡吃生,喝生,扯了大骨當兵,我和蔣邳合力才能打敗一隻。就憑何小妞一個人?嘖嘖,我看懸。」
「咳咳!」齊玄余道,「請廖施主別再火上加油,小僧快被段施主掐死了!」
「還活著?」段曉樓死命搖晃。
齊玄余盡量讓自己顯得更更誠懇些,力證道:「是真的,小僧為起了命盤,顯示『長壽福厚』,也沒有斷絕生機,一定還活得好好兒的。其實那日被擄走時,並不顯得多慌張,清醒鎮定,相信易地而,小僧也不能做得比更好。」
陸江北也道:「我與當歸曾換過很多報,對廠衛的幕非常了解,還知道伍櫻閣的所有運作,其詳細程度令我驚訝。或許,掌握了人的弱點,有辦法也說不定。」
齊玄余看向段曉樓,求道:「關於劣徒遜也的置,能否由小僧辦?小僧一定會讓他深刻牢記此教訓。」
Advertisement
段曉樓繼續搖齊玄余,求他:「你算一卦,算算在哪兒?」
「很抱歉,這種事,除非我齊氏父子二人聯手,否則是不可能辦到的。」
「那你父親在哪兒?」段曉樓迫切地問。
「不知道,我還在不斷找。」對於段曉樓的失落,齊玄余也深抱歉。
第五日,城外騎兵駐營。
熠迢好容易設法支走了紫霄,然後苦勸孟瑄:「一錯不能再錯,您留這麼個人在邊,已經是對不起郡主了,現在絕對不能再用辦『那件事』。我有種強烈的覺,一定會出賣我們!」
孟瑄伏在案臺上,懶洋洋地說:「哦熠迢,你越來越了不起了,比人還有覺。可自從我罰了戴品,引得眾人怨我,辦事越來越懈怠。熠彤是賭氣留書出走,你是婆婆媽媽,再說這裏你也走不開。這麼一數,我都快孤家寡人了,不用用誰?」
熠迢咬牙:「總之不能用!」
孟瑄往後闊椅上一躺,呈「大」字形攤開,瞇著眼睛,用慢騰騰的拖腔說:「我是大將軍,還是你是?我的話就是軍令,你管。哦,我小憩一會兒,沒有要事的話,你等天黑了再喊我。」
說罷,鼻端就傳出鼾聲來。
熠迢握拳瞪了他一會兒,氣沖沖地質問:「你還是公子嗎?你還是熠迢一心一意追隨的英明公子嗎?你看你現在像什麼樣子!」
「嗯?」綿綿的聲音像綿羊低咩,「好吵,幹嘛吵人睡覺。」
熠迢更火了,呼啦指著孟瑄的鼻子罵道:「你知道你現在像誰嗎?你就像兩個月前皇城裏半死不活的老朱元璋,又老又昏聵,吃著來歷不明的藥丸,每天只知道睡睡睡!如果你力不足,不能再當這個大將軍,你就該向皇帝請辭,出這枚將印!」
孟瑄睜開睡眼,裏面盛滿了無辜,「睡覺而已,用得著這麼兇嘛。藥丸是清兒給我的,我為什麼不吃?」
「郡主?何時給你的?」
熠迢不信。公子腰間的那個青瓷瓶,是何當歸死後才掛上去的。熠迢直覺著,那裏面裝的絕不是什麼好葯,公子吃后傷口癒合雖快,人卻哈欠滿天,一天有六七個時辰都在眠中,其餘時間也是走神不斷。
孟瑄理所當然地說:「就是前天啊,熠迢你不是看著我服藥的嗎?」
熠迢抑著怒氣問:「你是說,郡主前日親手送葯給你?」
「嗯。」
熠迢又炸了:「你真是耳聾眼花了不?郡主死了半個月了,託夢送葯給你?!快說,你到底從何人手裏得的葯,看清楚了沒?是紫霄那個人嗎?」
孟瑄皺眉:「就是清兒給我的,騙你幹嘛。紫霄幫我們不忙,何必事事針對?」
「啪!」
帳外有響,似乎是兩個人撞一起的聲音,伴隨著紫霄的驚呼——
「你還活著?你是人是鬼?」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9 章

位極人臣后我回家了
戰亂逃難時,才七歲的常意被人推入活井,險些淹死,九死一生爬上來,轉眼又被父母丟下。多年來,沒有一個家人找過她。如今海晏河清,父親淮陰候突然找上門來,言辭懇切,要接她回家,好好補償她這些年受的苦。已經隨當今皇帝征戰十年,官至一品,干到文官之首…
24.5萬字8.33 6882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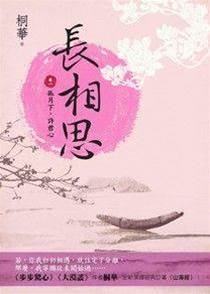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
完結124 章

長寧將軍
姜含元十三歲的時候,在父親的軍營里,第一次見到了那個表字為謹美的男子。彼時,少年安樂王代天子撫邊犒軍。銀鉤光寒間,笑盡杯酒;弓衣縱白馬,驚破了黃沙塞外的霜曉天。很多年過去了,久遠到姜含元已忘記那個深秋了,有一天,她被告知,他向她的父親求親,意欲娶她為妻。此時,他已是京闕中的那位攝政王了,高坐輔佐,權傾朝野。她愿做他馬前卒,為他平山填海,開疆拓土,雖死而無悔。然而,除了她自己,這世間,不會再有第二人知,那個快馬追風弓聲驚鴻的邊塞深秋的清早,也曾是她為少女...
46.2萬字8 8937 -
完結141 章

盛寵:權臣大人的掌心嬌
(重生 嬌寵 權謀 宅鬥 1v1 雙潔)重生到出嫁之日,楚嬌嬌不逃婚了!想到上輩子她逃婚後的淒慘下場,楚嬌嬌發誓一定抱緊權臣大人的大腿!新婚之夜——“夫君~”蓋頭下頭傳來一道酥麻蝕骨的甜膩女聲,顧宸不由挑眉,右手撫摸著扳指,隨即玩味勾唇一笑。都道楚家小姐國色天香,刁蠻任性,他今兒倒是要好好瞧瞧這新婚妻子是否如傳聞那般絕色.......顧宸其願有三:一願吾妻長命百歲,無病無災。二願吾妻來世今生,均入吾懷。三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文獻:臨淵羨魚不如退而擁你,隔岸觀火沒有生若伴我。 願凜冬散盡,星河長明,他與夫人共白首。(第二部籌備中,預計五月與大家見麵。)
12.2萬字7.85 41796 -
完結150 章

朕那失憶的白月光
鍾薏失憶了,醒來後丫鬟告訴她,自己是侍郎府嫡女, 有把她捧在手心的父母家人,千嬌萬寵長大。 她遇到了九五至尊做她的心上人,光風霽月溫潤如玉,承諾弱水三千只取她一瓢。 一紙詔書,她滿心歡喜嫁入皇宮,皇帝變成夫君。 後宮無爭鬥,日子如神仙般逍遙安寧。 除了夫君有些過於頻繁的索取和有點窒息的佔有慾,一切都無比完美。 鍾薏以爲,自己會一直這樣幸福下去。 直到某一日,失去的記憶如潮水涌入腦海—— 她終於想起,眼前的皇帝,是那個曾經因她和別人多說了幾句話,就將她囚禁於寢殿的瘋子。 她受不了他恐怖的愛和控制慾,選擇逃跑,墜入水中失憶。 如今,記憶迴歸,恐懼也隨之而來, 於是她表面仍舊與他日日親暱,背地悄悄籌謀,想再次逃離,卻被他一眼識破。 皇帝勾着一如往日的溫柔笑意,將兩人手一同鎖在榻邊的雕花金柱,吮去她眼角溢出的淚水。 烏髮迤邐交纏,他摩挲着她的臉頰,嗓音低啞繾綣:“看,這般我們就再也不會分離了。” * 【男主視角】 朕有一愛人。 她機敏,聰慧,略懂醫術,是天底下最好的女郎。 年少時,她救我於生死間,巧笑嫣然,用花言巧語討我歡心。 我信了,也甘願沉淪其中。 我想把她留住,可她是一隻留不住的鳥,於是我將她關在房中,爲了安慰她,許她世間珍寶、千萬榮寵,甚至將無上鳳位捧到她面前,只爲博她一笑。 可她竟還是總着離開我。 我捨不得傷她,所以,她第一次逃,我便斬盡她身邊侍婢;她第二次逃,我將蠱惑她之人的頭顱送到她面前。 我以爲,只要用盡一切將她留在身邊,總有一日,她會懂,懂我的愛。 可她拼了命地逃出皇宮,寧願去死也不願再多看我一眼。 我無計可施,跪在她面前,問她,爲何不再愛我? 那日江風獵獵,吹得她搖搖欲墜,她雙眼通紅,流下清淚,說,陛下從不懂情,又何來愛? 好在,上天憐憫,又給了我一次機會。 她失憶了。 那麼這一次,我便換個法子,學着做一個溫柔的郎君,細細地纏着她,哄着她。 等她深陷其中,等她徹底愛上,再告訴她—— 永遠別想離開朕。
35.7萬字8 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