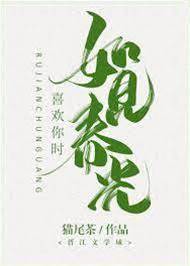《不斷作死后我成了白月光》 第125章
裴寂沐浴完畢, 回到臥房時,見到寧寧坐在床上,一本正經在想些什麼。
想得皺了眉, 很出過這樣嚴肅又苦惱的神, 在見到他的影時眸一亮。
裴寂下意識覺得, 導致如此苦惱的罪魁禍首,可能與他有關。
他與寧寧結為道尚未多久,時常離開玄虛, 在四海之漫無目的地游玩。
寧寧是個閑不下來的子,一地方還沒呆上多久,便急不可耐地想要去別轉轉。
偏生又頗為念舊, 時常舍不得獨一格的景,一來二去之下,兩人干脆在心儀之地都購置了房屋, 等來日心來,再劍前去住上一宿。
比如南城里這間竹樹環合的院落。
寧寧今日在麒山遇見故友, 同陸晚星等人小聚半日后, 這會兒已沒了多氣力, 綿綿靠在床榻上。
比裴寂早些沐浴,長發被一玉簪輕輕挽住, 垂落幾縷零散的青,被窗外晚風一吹,輕飄飄拂過臉龐。
“裴寂。”
寧寧正著他,語氣是前所未有的凝重:“我有件事,想跟你討論一下。”
說著一頓, 似是有些難以啟齒, 朝他勾勾手指:“你過來。”
于是裴寂乖乖上前, 坐在床邊。
離得近了,就能聞見側清幽的梔子花香。
寧寧之前說得毫不猶豫,心里的話臨近出口,反倒出了略顯局促的神,耳廓漸漸涌上紅。
好在他極有耐心,垂了眸挑起耳邊長發,將其別在耳后:“什麼?”
“就是……”
寧寧抬眼迅速瞧他,又很快垂下眼睫,說著抿頓了頓,在經過片刻停滯后,似是破釜沉舟般開口:“就是,你難道不覺得,每次晚上的時候……你都太兇了嗎?”
Advertisement
裴寂一怔。
他總算明白寧寧為什麼會臉紅,乍一聽見這句話的時候,他的耳朵也忍不住兀地發燙。
他有“太兇”的時候嗎?
他們剛結為道,對于這方面都沒有太多經驗。在夜里的時候,往往是兩人神識纏,彼此試探,然后他順勢探尋得越來越深,靈力激,而寧寧——
寧寧似乎……時常會著氣,疲力竭般他停下。
雖然他很會照做,就算照做了,也會咬著牙拉住他手臂,啞著嗓子說繼續。
而且每到第二日,無論前夜如何,寧寧都會把這茬忘得一干二凈,從來沒表現過不滿。
于是裴寂紅著耳朵,很認真地問:“我讓你……難了?”
“倒也不是難,我很滿意——啊不對!”
寧寧越說氣息越,本想用強勢一些的語氣,嗓音卻始終保持著近乎于倉惶的艱:“我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我、我要當主導的那一個!”
終于說出來了!
寧寧心底貓貓落淚,為自己的勇氣瘋狂點贊。今天就要農奴翻做主人,推翻裴寂的無良統治!
裴寂愣愣看著。
寧寧強裝鎮定地與他對視,由于不知道對方將作何反應,張得心臟半懸在口。
然后看見裴寂微微一。
剛沐浴完畢的年爬上床鋪,一把拉過右手,按在他單薄睡袍上。
然后往旁側輕輕一。
“……像這樣?”
暴擊。
致命暴擊。
他做了這樣的作,口衫半遮,出里瑩白,表卻是一向的認真,帶了點探尋與困的意味。
又純又。
寧寧的臉很沒出息地發了燙,而裴寂見沒有反駁,保持著握住小姑娘右手的作,向床鋪里靠了靠,躺坐在床頭。
Advertisement
一副“我已經躺好了你隨意”的姿勢。
他如此直接,作為口口聲聲說要主導的那一方,寧寧反倒到了慌。
好在他們之間的經驗雖然很,卻好歹聊勝于無,努力做好思想準備,順著裴寂的作,年向下落的前襟。
像是緩緩剝開一顆被珍藏許久的果實,屬于裴寂的那一部分,逐漸毫無遮掩地闖視線中。
劍修的經過常年鍛煉,都能見到明顯的。
他屬于偏瘦的類型,上曲線流暢且和,薄衫一點點落,途經腰腹之時,現出陡然收、向合攏的線條。
寧寧坐在他著了長的上,晃眼一瞥,見裴寂按在被子上、因太過用力而微微泛白的右手。
這是一種只有在張時,才會不自覺出現的微作。
他總是死鴨子,無論心里作何想法,都會努力表現得云淡風輕。
房燭火未歇,為整個空間籠上一層朦朧暗紅,連帶著年人白凈的側臉和黑眸。
這本應是極為賞心悅目的畫面。
如果忽略掉他上縱橫的傷疤。
裴寂從小到大過不傷,早先是因為尋不到傷藥,無法及時治療;后來長大了玄虛,又對于傷痕習以為常、不甚在意,有特意療傷的時候。
因而如今掀開,上舊疤,在口、臂膀與腹部,皆凝深褐與淺紅長痕。
像是被撕咬過,又或是來源于鞭子和藤條。
裴寂到的目,眸一黯。
他知曉自己這疤痕遍布,看上去猙獰丑陋。寧寧曾經從來都小心翼翼地不去,如今——
淺淺的怯與恥辱涌上心頭,裴寂沒由來地到心慌,低聲喚了句:“別看,寧……”
Advertisement
話音未落,近在咫尺的小姑娘忽地低下頭。
在溫暖的火里,寧寧吻在他鎖骨下方的刀痕上。
長睫無措抖,裴寂頭輕,發不出聲音。
那些疤痕象征著他最為落魄的過往,每一條都難看又可怖,如同盤旋在各的蜈蚣,連他自己都心生厭惡。
可寧寧卻吻在那里,用了十足溫的力度。
“寧寧。”
他心里既又燥,喑啞出聲:“那里……不好,別。”
寧寧抬頭,與他四目相對。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裴寂臉通紅。
他生了雙極為漂亮的眼睛,眼尾向上勾起,暈開一片桃花般的淺。黑瞳里蒙了層霧,看上去迷迷蒙蒙,將平日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意盡數遮去,有如遠山落雨,攜了膽怯的。
裴寂害起來……原來是這種模樣嗎?
像冰冰冷冷的冬雪慢慢融化,淌開一灘得過分的春水。
寧寧坐在他之上,將一切緒盡收眼底,恍惚中,覺得自己的條快要被清空。
看著眼前的疤痕,想起裴寂曾經的過往種種,總覺得心里難。
他一直厭惡這些傷疤,因而把與它們相關的記憶全部埋在心底,不向任何人訴說,靜靜等待腐爛。
裴寂的這些心思,都知道。
他總是一個人在悄悄難。
寧寧的作沒停,與他對視一眼后,重新低了頭。
那些傷痕其實已經不痛了,唯有在雨天氣的時候,骨頭里會傳來的悶疼。
可瓣輕,上道道質長痕時,被他所厭棄的死竟有了知覺,意橫生。
有熱氣自心口向全涌。
裴寂下嚨里的氣音,深吸一口氣,用右臂擋住雙眼,不讓喜歡的姑娘見到自己狼狽的模樣。
Advertisement
那道陌生的停在口某地方。
他聽見寧寧的聲音:“這里……是不是很疼?”
說話時移開出手,指尖停留在一道深褐疤痕,不敢用太大力道,輕輕一,有如掠影浮,引來稍縱即逝的電流。
裴寂心如麻,不經思索地應:“已經……不疼了。”
“是嗎?”
寧寧的指尖轉了個圈,視線沒從它上面挪走:“看上去傷得好重。”
“這是我尚未拜玄虛的時候,途經駱洲,于山野之間……”
裴寂啞聲開口,甫一抬眸,對上孩清亮的眼瞳。
那雙杏眼漂亮得不像話,好似深夜微漾的幽潭,當寧寧垂了眼睫注視他,瞳仁里盛滿躍的燭,恍如水中明月。
在看著他。
看見他上每一不堪的地方。
這個念頭攜了淺淺熱度,讓裴寂心口一燙。
此時此刻,仿佛連最簡單的注視都了種不可言喻的曖昧,年頭微,調整氣息:“于山野之間遇見了魔的妖修,他以劍道,劍氣正中此。”
“然后呢?”
被深深埋在心底的記憶重新涌上腦海,裴寂沉聲應道:“我那時沒有劍,只會用小刀,趁他神志混,頂著劍氣上前去——”
他說罷眸愈深:“寧寧,這不是什麼好故事。”
裴寂不愿告訴更多。
他的過去暗無,沒有任何值得稱道的地方,如同寥落臟的,聽了只會人心煩。
可寧寧不同。
自小生長在無憂無慮的溫鄉,從不知曉那些臟污與疾苦,裴寂也不想讓知道。
月亮就應該高高遠遠地掛在天空,世間所有的好與清明澄澈,怎能讓染上里的暗。
裴寂不愿寧寧為他到難過。
從他那里得到的,理應只有溫和快活。
覆在口的悠悠一旋,途經他肋骨上尚且完好的皮時,加重力道輕輕一咬。
那位置靠近腰。
的氣息像團滾燙的霧,裴寂屏住呼吸,右手攥單薄床單。
“這里呢?”
寧寧的視線一點點下,來到他小腹。
裴寂很瘦,并非纖細多病的孱弱,而是理勻稱、壯漂亮的拔,從的視角看去,能見到塊塊結實的腹。
以及上的一條凌厲長痕。
理智被無數道錯雜的緒盡數吞噬,上的刺激似有若無,被隨心所地牽引。
凝結的視線有如實,他從未被如此認真地注視過。
裴寂快瘋了。
“這是我娘……”
最后那個字被吞咽回嚨里。
寧寧低低“嗯”了聲,繼續向下。
一個接一個的吻輕輕,如同春日里的第一場細雨,水滴細,落在沉寂許久的池塘上,漣漪圈圈漾開。
池水輕,風的呼吸亦在輕,漣漪滲進不為人知的池塘深,惹來陣陣不由自主的戰栗。
最后來到更下面一點的位置。
也更恥且一些的位置。
牙齒緩緩咬住細白的長帶。
寧寧抬了眼睫,勾著角向他。
燭微搖,映亮漆黑的眼瞳,與白玉般細膩的。
像只小狐貍或貓。
“裴寂。”
寧寧忽地笑了,聲音被得很低很低,尾音帶了點狡黠地上揚,將他整顆心都一并勾起來:“繼續嗎?”
結驀地一。
心底被強下的思有如暗涌,尖嘯著沖破層層枷鎖,迅速填滿四肢百骸。克制、矜持與斂被吞沒得一不剩,那只沉睡在口的野,悄悄出了尖利的爪子。
毫無征兆地,寧寧左手手臂被猛然握住,徑直一拉。
裴寂一直安安靜靜,怎麼也不會料想到這個作,大腦一片空白之際,順著他的力道向前跌倒。
束在黑發上的玉簪倏然一晃,掉落在地時,引來傾瀉的青如瀑,以及哐當一聲脆響。
接而便是整個人被不由分說翻了個,平躺在裴寂之前所在的地方。
一上一下,兩人的姿勢徹底互換。
等、等一下。
手臂被死死按在床鋪上,寧寧的陷進被褥,能清晰到他余留下來的溫和熱度。因這個突兀的作睜圓了雙眼,張了試圖發出抗議。
明明說好了,今天他會由著來——
裴寂這是犯規!
可惜這番話沒有機會被說出來。
裴寂雙眸幽深,俯擒住瓣。
同他冷白上的紅痕不同,寧寧被一襲雪白薄衫完完整整裹住,乍一看去并無異樣,唯有雙頰泛了紅,襟因為方才那番作凌地半遮,現出層層褶皺。
他探出骨節分明的手,薄衫之下,多出一道游走著的弧度。
裴寂的作多了幾分平日里罕見的急躁,卻自始至終稱得上“溫”。寧寧到他掌心的熱度,只覺渾滾燙。
戰栗有如野的牙齒,肆無忌憚啃咬經脈與。即便之前有過嘗試,每當被他,都會下意識到害。
窗外不知何時下起了雨。
雨疏風驟,晚來寒流,樹葉、梢頭、燭、人影,一切都在急促晃,宛如風浪里的小舟。
夜漸深,雨勢漸弱。
寧寧再睜開眼,只能見年人纖細的鎖骨,與線條流暢的冷白皮。
——說是冷白,其實早就浸了層和淺。
那抹薄薄的悄無聲息暈開,自脖頸漸變著趨向于白,穿過道道蜿蜒的深褐疤痕,蔓延至的每一寸。
或許是察覺到微微仰頭的作,裴寂抱在寧寧后背的雙手下意識一僵,頸上紅暈更濃。
他這會兒知道不好意思了。
寧寧已快沒了力氣,將腦袋埋在他頸窩里,極盡輕地親了親。
的聲音也一并被錮在頸間,聽上去悶悶的,帶了笑:“裴寂很好看。”
旁的人呼吸明顯頓住,寧寧得寸進尺,繼續蹭蹭他下:“只要是你,不管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或是上的任何地方……我都喜歡。”
這樣喜歡他,無論何等的狼狽與不堪,寧寧都愿意毫無保留地接納。
更何況,裴寂從來都沒有過“不堪”的時候。無論生活怎樣蹉跎,他都始終咬著牙,把脊背得筆直又漂亮。
空氣里出現了極為短暫的停滯。
裴寂被蹭得有些,再開口時,周的氣息不自覺一團:“不管什麼地方……都喜歡?”
寧寧沒做多想,點頭應道:“對呀。”
聽見一聲很低的笑。
裴寂嗓音里蒙了層意,像蛛網蓋在耳上,忽然冷不防:“寧寧。”
被他抱在懷里的小姑娘了腦袋,答得很乖:“嗯?”
裴寂:“……”
裴寂:“我們繼續。”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90 章
盛夏晚晴天
結婚三年,面對丈夫的冷漠,她從來都沒有顯示過軟弱,但當小三懷了他的孩子鬧上門,她第一次淚眼婆娑。面對他鮮有的錯愕,她挺直脊梁倔犟的轉身!背后他冷語嘲諷:夏晚晴,憑你市長千金的身份,多的是豪門巨富登門求親,何必束縛我?離婚協議簽署的那一刻,她拾起驕傲,笑靨如初。她說:莫凌天,如果愛你是一種錯,那麼這三年,便是我為自己的錯承擔的后果,以后,你再也沒有機會因為這份愛而傷害我!離婚后,一個月。本城喬氏大公子,歸國海派富二代,那個驚鴻一瞥,在她最狼狽時遇到的男人,登門拜訪來提親。他說:嫁給我,不僅父母安心,還可以打擊那個傷害你的男人!他說:嫁給我,保證這輩子不會背叛你,因為我愛的那個女人,再也不會回來了!面對這個風度翩翩,笑意融融,卻深不可測的男人,她還有理智。她問:既非為愛,必有所圖,娶我要什麼條件?答案簡單而無情:很簡單,你是市長千金!呵,果不其然,憑她的身份,想嫁個不錯的男人,易如反掌,若非為愛,婚姻又能持續多久,但若是為愛,還不是鎩羽而歸?所以,她定定的望著眼前的男人,這一次選擇了沒有愛情的婚姻!
72.2萬字8 20125 -
完結52 章
似癮
沈家老三素來清冷,隻有一起長大的朋友敢拿他打趣,調侃他清心寡欲,活得像是苦行僧玩笑話沈晏清從來不答,時間太久旁觀者大概也都忘了,他曾經有過女人,也有過摁住就親,徹夜不眠的方剛血氣. …
15.7萬字8 15233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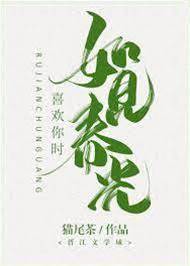
喜歡你時,如見春光
朋友給周衍川介紹了一個姑娘,說她不僅臉長得好看,學識也很淵博。 周衍川勉為其難加好微信,禮節性問:“林小姐平時喜歡什麼?” 林晚回他:“我喜歡看鳥。” “……” 周衍川眉頭輕蹙,敷衍幾句後就沒再聯繫。 後來朋友問起他對林晚的印象,周衍川神色淡漠,連聲音都浸著寒意:“俗不可耐。” · 時隔半年,星創科技第三代無人機試飛,周衍川在野外見到了林晚。 她沐浴在漫山春光之中,利落地將三角架立在山間,鏡頭對準枝頭棲息的一隻小鳥,按下快門時,明艷面容中藏進了無限柔情。 回城的路上,周衍川見林晚的車子拋錨,主動提出載她一程,怕她誤會還遞上一張名片:“你放心,我不是壞人。” “原來你就是周衍川。” 林晚垂眸掃過名片,抬頭打量他那雙漂亮的桃花眼,幾秒後勾唇一笑,“果然俗不可耐。” 周衍川:“……”
28萬字8 19261 -
完結268 章
春臺記事(仰見春臺/嬌啼/嬌靨)
上京城內的高門貴女心中有一個共同的白月光。謝家嫡子謝韞,俊美無儔,矜貴無比。但桑窈不喜歡他,起因是某次她在他旁邊不慎崴了腳,這人分明伸手就能扶住她,卻不動聲色的往旁邊躲了一下,眼睜睜看桑窈摔倒,讓她丟了個大臉。這事桑窈記了好久,每每從謝韞旁邊經過,都要賭氣哼一聲,但謝韞從來沒多看她一眼。桑窈:更生氣了(`Δ?)!直到桑窈機緣巧合下撿到了謝韞的手冊,翻開一看——里面不僅詳細記錄了謝韞對她的迷戀,還有不少以他倆為主角的香艷情史,更離譜的是還有謝韞寫給她的情書,尺度之大,簡直離譜!桑窈惱羞成怒,啪的合上手冊,小臉通紅。從此,她看謝韞的目光就不一樣了。果然再優秀的人都會有煩惱,謝韞看似無所不能,其實也只是一個愛而不得甚至現實不敢跟她講一句話,每天只能在夢里幻想的小可憐罷了。桑窈向來心軟,偶爾大發慈悲的主動跟謝韞講話。謝韞仍然冷淡。桑窈:害羞罷了。后來族中逢變,桑窈迫不得已求見謝韞。于謝韞而言,這不過是一場需要簡單敷衍一下的會面。他面色冷然,淡淡開口:“姑娘請回,此事已成定局。”就知道這狗男人不會輕易答應她。桑窈二話不說上去親了他一口,“別裝了,這下行了吧。”死寂之中,二人四目相對少時成名,向來從容冷靜的謝韞終于開始正視這個色膽包天的少女。某次謝韞身邊偷偷磕桑窈與謝韞cp的小廝,在某一天發現自己精心創作的禁忌同人話本不見了!后來。雖然話本子不見了,可他磕的這麼冷門cp居然成真了!?再再后來。消失許久的話本出現在了他家夫人手里,夫人指著話本告訴他。“別看那個小古板看起來正兒八經的,其實內心可狂野了。”
40.2萬字8.18 7104 -
完結189 章

同住一屋的哥哥是我前男友
【偽兄妹+雙潔+蓄謀已久】【拉扯為主+穿插回憶】陸靈兮八歲住進裴家。 初見時,男孩坐在高高的書架階梯上,燈光照在他頭頂,白衣黑褲,冷漠矜貴。 陸靈兮咧著嘴對他笑,“哥哥。” 他只是看了她一眼,淡淡評價,“小屁孩。” 原本以為老死不相往來的兩人,誰曾想,后來成為一對深愛的戀人。 - 陸靈兮一直知道裴辰霖是個小惡魔,內心純壞。 在熱烈相愛的那幾年,他的壞展現到床上,壞得淋漓盡致。 后來他們分道揚鑣,再重逢時,已是三年后。 兩人重新做回兄妹,只是他看她的眼神,不再單純。 看到她與其他男人接觸,他嫉妒發瘋。 雨夜,他將她摟在懷里,貼耳威脅,“乖,和他斷了聯系。”
32.6萬字8 46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