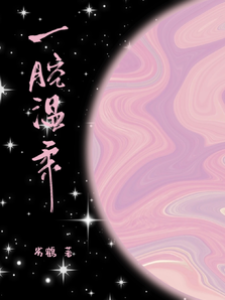《不斷作死后我成了白月光》 第78章
孟訣與天羨子一樣, 仍然沒有醒來。
看來下在九洲春歸里的藥果然與寧寧猜想一致,修為越高,中毒也就越深。好在裴寂與賀知洲已經清醒, 說明這并非致命毒藥, 想必再過一段時間,他們兩人也能漸漸蘇醒。
“若是二位還有別的要事, 大可讓他先行留在此地。”
賣畫的安好孩們, 輕咳著溫聲道:“孟訣很乖, 一直喚我, 與其他孩子也相很好, 你們無須擔心。”
孟訣此人看似多卻最是無,平日里總是溫溫和和地笑,實際對誰都不上心。
這種格主要源于他兒時的經歷, 娘親是地位低下的姬妾,生下唯一一個兒子后大病而亡,爹不疼主母不,孟訣無異于深宅大院里一顆被丟棄的棋子,連小廝都能肆意欺辱。
聽說唯有一名上了年紀的老婦對他頗為關心,可惜后來宅院被妖修襲擊, 除卻孟訣外無人生還。
在那之后不久, 他便被前來除妖的天羨子收為親傳徒弟,也正是打那以后, 孟訣待人更加疏離,鮮。
如今他醉了酒, 或許是將這位當作了當年那名慘死的老婦。
在這個修真界里,生離死別似乎格外近又格外遠,時日久了, 只剩下些許故人的殘影還留在心頭。
寧寧想起原著里與孟訣相關的描述,在心底暗暗嘆了口氣,只得輕輕點頭。
駱元明在茶館里說過,鸞娘在昨晚之后一直與他形影不離,今日亦是有丫鬟小廝陪在邊。
倘若當真犯了事,既要在城主府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瞞過去,又要盡快驗收果,最佳的時機,便是等到夜半三更、所有人都沉沉睡的時候。要是他們能在深夜前去城主府探查一番,說不定會有所發現。
Advertisement
“真奇怪。”
寧寧將手里的畫作上下打量一遍,最終把目落在鸞娘的回眸上:“一共做了兩幅畫,為什麼鸞娘見后,只買下了那張畫著兩人背影的?”
“這還不簡單?”
承影一張小叭叭叭,自從聽見寧寧的那句“喜歡”,就激得像是生吃了整整一肚子興劑:“要想生活過得去,頭上必須帶點綠。城主頭頂已經在開始長草,要是鸞娘把這幅畫也帶回去,等他見到畫像上自己媳婦的臉,還不得直接從草原變茂大森林?”
自然聽不見這段話,因此也無從與承影辯駁。寧寧思索再三得不出結論,只好先把這個問題拋在腦后,收好畫卷后低聲道:“,我很喜歡這些畫,想把它們買下來。”
“姑娘若喜歡,隨意拿去就好。”
老嫗灰暗的瞳孔里溢出幾亮,似是淺淺笑意:“已經很久沒人說喜歡這些畫了。你不知道,我年輕那會兒是這條街畫技最出眾的人,連花魁小像都是由我所做的,見過的人無一不稱贊栩栩如生——只可惜我老了,現在已經幾乎賣不出去。”
寧寧笑著搖搖頭。
來到鸞城之后,幾乎把所有零用錢都花在了夜明珠上,此次在境中歷練一番,收集到不珍惜藥草,出來后賣了個不錯的價錢。若是都送給,應該能支撐這一大家子一段時間的溫飽。
窮就窮吧,反正已經習慣了。
寧寧下定決心,正要從儲袋里拿出錢袋,忽然聽見裴寂冷淡的年音:“五千靈石,買所有畫。”
寧寧瞪大了眼睛看著他。
靈石的匯率不比人民幣,五千可不是小數目,他不會是看出打算傾家產的念頭……所以搶先一步,讓自己代替傾家產了吧?
Advertisement
“五、五千靈石?”
不止,連阿卉也出了不敢置信的神:“這位公子,這些畫值不了這麼多錢的!”
“無礙。”
裴寂罕有地出了稍顯遲疑的目,面無表地飛快一眼寧寧,又迅速把視線移開,如同蜻蜓點水,語氣亦是冷淡:“喜歡就好。”
他是怎麼做到,用如此波瀾不起的語氣說出這樣的話啊。
寧寧:……
寧寧同樣沒什麼表,神僵得像木頭,察覺到阿卉直直投來的視線時,有些局促地低了頭,拿右手鼻尖。
阿卉又看一眼抱著劍的裴寂,一時半會兒沒忍住:“噗。”
=====
夜半,城主府。
寧寧匿了周靈氣,與裴寂一同潛府里。
這是頭一回干這種狗的事,心里難免很是張,為掩人耳目,還特意穿了黑,往同樣黑發黑衫的裴寂邊一站,兩人幾乎能直接進夜里。
他們掌握了鸞鳥像的運轉規律,趁著視覺死角潛府上。夜半的府邸空寂無人,濃郁墨映襯著流水一樣的月,幾盞燈火幽然,無端顯出些許詭譎之氣。
由于之前來過幾回,寧寧已經大致清了府邸走向,能憑借記憶一路來到城主與夫人的臥房之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這棟房間房門虛掩卻空無一人,唯有門前燭火搖晃,大抵是由小廝所點。
這麼晚了,這對夫妻能去結伴做些什麼?月下瓜田刺猹?
房門開著,說明那兩人之前應該回過臥房,之所以來不及關門便離開,或許是發生了什麼意料之中的突發況。
——可究竟是什麼事兒,能讓他們如此匆忙地從屋子里離開?
寧寧與裴寂對視一眼,朝他做了個小小的口型:“進去看看?”
Advertisement
裴寂點頭。
臥房里并未亮燈,幽寂之便顯得愈發沉重。這間房屋表面看來并無異樣,木雕大床、輕紗籠帳,然而直至此刻,男主人卻都未歸來,實在很難讓人不起疑心。
那兩人行蹤有異,房間里或許留存著些許線索。寧寧不能點燈,更不敢發出太大聲響,本想上前一些細細搜查,卻猛地察覺旁裴寂一——
自房門之外的不遠傳來人的一聲笑,隨之而來的,還有踏踏腳步聲響,想必是駱元明與鸞娘深夜回房。裴寂眼疾手快,看準了一旁佇立的木柜,一把拉住胳膊藏進去。
木柜只有大半個人高,里面裝了些零零散散的。寧寧毫無防備,一下子倒在他膛上,還沒完全適應眼前的黑暗,剛要微微一,便察覺上被覆了層溫溫的東西。
裴寂捂住了的,那是他的手心。
等、等一下。
是被裴寂……不由分說直接抱在懷里了?
寧寧從剎那的茫然中迅速回神,在狹窄昏黑的木柜里努力辨認他們兩人此刻的姿勢。
裴寂已經松開了抓在肩膀的那只手,雙叉開弓起坐在柜中,而被順勢一拉,理所當然落在他兩條中間的木板上。
年劍修形消瘦,膛卻出乎意料地寬敞,當寧寧被整個桎梏其中,無法逃離更難以彈,只能覺到后背上劇烈的心跳,像一團躍著的熾熱火苗。
這個姿勢出乎意料地并不難,甚至于萬分溫存,讓有些舍不得離開。
不對。
萬幸裴寂在后,看不見寧寧驟然通紅的臉。
……在胡思想些什麼,誰會想要一直被裴寂抱、抱在懷里啊。
裴寂一直沒,也沒做出任何表示。
Advertisement
這雖然是由他發起的作,在手掌接到的瞬間,寧寧卻很明顯地到后的年渾一僵,心跳加快許多,像是十分張。
怎麼會不張。
裴寂按耐住心頭躁,微微闔上眼睫。
木柜并不高,他坐在里面,幾乎是把寧寧整個擁在了懷中。
孩的近在咫尺,腦袋則輕輕抵著他下,有細細的發悄無聲息劃過結、脖頸與頸窩,如同無聲的逗弄。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輕微打開的隙里滲出許亮。
黑暗讓除視覺之外的所有異常敏銳,那縷微則若若現,為整個空間蒙上一層朦朦朧朧的紗,看不清也不著,曖昧至極。
最為張的部位,是他右手。
寧寧的呼吸盡數灑在食指上,像羽那樣輕輕抓撓拂蹭,帶了點暖洋洋的熱度,百轉千回。而手心則著的瓣,有時會因為張下意識地抿,雙便會不經意地掃過手心皮。
就像親吻一樣。
他莫名又想起醉酒的那一個晚上,心頭煩悶更甚。
駱元明的修為遠在他們二人之上,若是輕易用靈氣,很可能被他察覺。
寧寧與裴寂無法傳音,只能保持著這個姿勢默不作聲。
“今夜可乏死我了。”
桌上的燭燈被點燃,耳邊傳來鸞娘的笑聲,慵慵懶懶,像只貓:“我們早些歇息吧。”
駱元明亦是笑:“好好好。今夜是哪種熏香?夫人最桃花,不如就用它吧?”
“夫君用慣了竹香,而今上的味道同我這樣一改,不知又有多人要在背后風言風語地說閑話。”
“那又如何?他們那是嫉妒我有這樣一位夫人。”
然后便是一串放浪的笑,以及挲的聲響。
駱元明當真如傳聞所說極了鸞娘,語氣里盡是遮掩不住的意與慕:“娘子,真想日日與你這般相親、耳鬢廝磨。”
鸞娘的聲音如同浸了酒,將他所說的幾個字低低重復一遍:“我們現下不正是如此?既然已經相親、耳鬢廝磨……那我便是你的。”
著裴寂手心的寧寧呼吸一滯。
可惡,這對夫妻平時講話都這麼麻嗎?聽得皮疙瘩起了滿。
黑發纏繞在寧寧發的裴寂一僵。
……只要這樣,就算是他的?
他帶著寧寧藏進柜中時,并未把柜門完全關上,因而出了小小一道隙,若是細細去看,能瞥見房兩人相擁的影。
寧寧從小看著古裝劇長大,對于這種場景見怪不怪,沒有任何心理負擔地瞇了眼睛,正要向外一探究竟,忽然察覺眼睛前蒙了層厚重的黑。
不是吧。
裴寂這混賬小子……居然用空出的另一只手,迅速蒙住了的眼睛?
寧寧一陣心梗。
他當是小孩兒嗎!太傻了吧!稚鬼!超討厭!
的份好歹是師姐,哪能心甘愿在這種事上被上一頭,當即不服氣地皺了眉,用力把他蒙在眼睛上的手掰開,然后將自己的右手往上舉。
兩人皆是坐在柜子里,裴寂的下幾乎抵著腦袋,寧寧看不見他的模樣,為了不驚擾房中兩人,作格外小心翼翼。
右手先是到了一塊的地方,輕輕一,會輕輕凹陷又慢慢彈起來。
是他的臉頰。
這會兒裴寂臉上出奇地熱,四肢則徹底一不,任由寧寧的手掌依次拂過側臉、鼻梁與眉骨,最后如同惡作劇一般,毫不猶豫蒙在他雙眼之上。
他什麼也看不見,卻知道懷里的小姑娘一定出了心滿意足的神,低下頭一言不發地往外瞧。
——裴寂的右手還捂在上,能到寧寧輕輕揚起的角。
他一向厭惡與其他人的肢接,卻并不反此時此刻的作,只是在的時候……讓他有些難。
耳邊是男低微的笑聲與低喃,將曖昧的氛圍發揮到極致。桃花醉人的芳香繚繞其間,四周一片昏暗,由于被蒙住了眼睛,裴寂什麼也看不清。
寧寧坐在他跟前很近的地方,哪怕做出任何一個小作,帶來的戰栗都會擴大千倍萬倍,自腹部一直往上蔓延,仿佛要把莫名其妙的火燒往全。
渾上下皆是燥熱。
裴寂屏住呼吸,由于無法調靈力,只能憑借意識忍住砰砰直跳的心臟。
但似乎難以忍。
那些滾燙的、細的匯聚在一起時,如同烈火猛地發,讓他不由得深吸一口氣,緩緩低了頭,在耳邊竭力低聲道:“別。”
這道聲音被得又沉又啞,化作一道氣音落在耳邊,帶了幾分忍克制卻格外人的味道。
猝不及防的熱氣在耳畔轟地散開,好似有道電流貫穿整條脊椎,寧寧被這兩個字聽得紅了耳,一時間當真乖乖停下作。
突然之間用了這種語氣和聲音……太過分了吧。
他就不能稍微稍微地,讓有個心理準備嗎?
“天哪裴小寂,就你現在這樣,以后要真和寧寧在一起,怎麼得了啊。”
承影的語氣里帶了矯造作的哭腔:“不會吧不會吧,不會真有劍修……要孩子主吧!”
裴寂惱怒,強忍住心底的燥熱之氣,只想立馬拔劍殺了它。
裴寂:“閉、。”
萬幸城主與鸞娘并未做出多麼兒不宜的事,對拼命想要遮住寧寧眼睛的裴寂小朋友造心靈傷害,在不久之后便熄燈睡覺,余留熏香陣陣。
寧寧被裴寂抱在懷里,舒服得像是躺在又又溫和的玩熊旁邊。不知過了多久,正是睡意漸濃之時,忽然聽見木床上傳來吱呀一道聲響。
的倦意倏然消散,過那道小小的隙,見一道纖細人影。
房熏香陣陣,城主安穩眠。白煙與破窗而的月繚繞勾纏,好似輕煙水,恍然如夢。
在一片惹人心驚的寂靜里,鸞娘起下了床。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5 章

我的新郎逃婚了
B市整個豪門圈子都知道,阮芷音有多麼喜歡秦玦。她亦步亦趨跟在秦玦身后多年,看著他從青澀到成熟,然后,終于等到了兩人盛大的婚禮。秦阮兩家聯姻,婚禮當天,新郎秦玦卻不知所蹤。阮芷音知道,秦玦已為了自殺未遂的前女友趕去C市。賓朋滿座,期盼多年的婚禮上,她對秦玦徹底死心。不愿讓阮家淪為笑柄的她,咬牙撥通死對頭的電話: 【程越霖,現在來娶我,一年后離婚,北城項目給你】 那邊程越霖對著滿地的煙頭,握著手機挑眉: 【阮大小姐新郎跑了?成啊,等著,爺來娶你】 第二天,秦少爺和好友回到B市,接機的助理面色躊躇。 好友:“難不成阮芷音要解除婚約?” 助理:“那倒沒有,不過……” 秦玦:“不過什麼?” 助理:“阮小姐現在換了個新老公。” 秦玦:“?” ——抱得美人歸的程越霖:證已領,勿cue,謝謝。 婚后。 阮芷音發覺:這是怎麼離都離不了的婚。 程越霖暗喜:這是萬萬沒想到的天降餡餅。 秦玦悔恨:這是怎麼火葬場都追不回的妻。 【你敢逃婚禮,我敢換新郎。】 【一步到位火葬場,再也追不回的妻。】 【男二火葬場還追不到/男主暗戀成真先婚后愛】 閱讀提示:因古早虐戀逃婚火葬場的憋屈而寫,劇情略狗血,接受無能別為難自己,標明了還吐槽就ky了
23.8萬字5 49734 -
完結200 章

總裁輕些寵
養父母為了十萬塊錢的彩禮,要將她嫁給一個傻子。他從天而降救她出火坑。她捏著衣角感激涕零,“謝謝先生,我會努力打工還你錢的。”他嗤的低笑出聲,“打工?不,我要你嫁給我!”顧寒時對蘇雲暖一見鍾情時,蘇雲暖是周聿宸的未婚妻。後來,蘇雲暖遭遇車禍失蹤,周聿宸另娶她人為妻。顧寒時愛了蘇雲暖七年,找了蘇雲暖五年,他卑鄙的算計她,讓她成為他戶口本上的妻……
35.1萬字8 43498 -
完結304 章

夫君他天下第一甜
明王府獨苗苗世子謝蘅生來體弱多病,明王將其看的跟命根子似的,寵出了一副刁鑽的壞脾氣,那張嘴堪比世間頂尖毒藥,京城上下見之無不退避三舍。 初春,柳大將軍凱旋歸朝,天子在露華臺設宴爲其接風洗塵。 席間群臣恭賀,天子嘉獎,柳家風頭無兩。 和樂融融間,天子近侍突然跑到天子跟前,道:“有姑娘醉酒調戲明王府世子,侍衛拉不開。” 柳大將軍驚愕萬分,久不回京,這京中貴女竟如此奔放了? 他抱着好奇新鮮的心情望過去,然後心頭驀地一涼,卻見那賴在世子懷裏的女子不是隨他回京的女兒又是誰。 雖剛回京,他卻也知道這世子是明王的心頭肉,餘光瞥見明王雙眼已冒火,當即起身爆喝:“不孝女,快放開那金疙瘩!” 一陣詭異的安靜中,柳襄伸手戳了戳謝蘅的臉:“金疙瘩,這也不是金的啊,是軟的。” “父親,我給自己搶了個夫君,您瞧瞧,好看不?” 謝蘅目眥欲裂盯着連他的近身侍衛都沒能從他懷裏拆走的柳襄,咬牙切齒:“你死定了!” 柳襄湊近吧唧親了他一口:“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 謝蘅:順風順水頤指氣使了十八年遇見個女瘋子,她一定是我的報應! 柳襄:在邊關吃了十八年風沙得到一個絕色夫君,他是我應得的! 女將軍vs傲嬌世子
49.1萬字8.18 13561 -
完結1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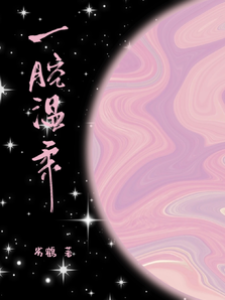
一腔溫柔
【西裝暴徒·戀愛腦大佬x淚失禁體質小奶兔,SC,男主在別人面前孤狼,在女主面前傻狗,老房子著火沒有救~】【男寵女❤先婚后愛+7歲年齡差+體型差+她永遠是例外跟偏愛~】 寧惹君子不惹小人,寧惹小人不惹閻釗! 京城誰不知道閻釗的惡名?四九城里把人剝皮抽筋的活閻王! 可是擁有讀心異能的葉早,每次閻釗兇巴巴,她都能讀取他的內心話—— [這小不點兒,腿長腰細,不知道手感好不好。] [這小姑娘的嘴巴,紅彤彤的,怎麼很好親的樣子。] [這小呆子,被人騙了都得幫人數錢。] [早早!我的可愛老婆!她怎麼還不來哄我?再不哄我我要鬧了!] [啊啊啊啊我已經開始鬧了!] [不親我一下,今兒這事絕對過不去!絕對!] * 壞消息:這個男主強取豪奪,偏執+占有欲爆表,日常不長嘴,玩強制! 好消息:這個女主會讀心~ 虐心虐身劇本也能分分鐘轉甜,小白兔義無反顧治愈孤狼。 【嗜血瘋批,唯獨予她一腔溫柔~】₍ᐢ..ᐢ₎⊹
29.5萬字8 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