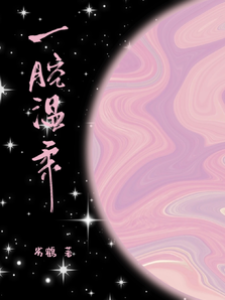《反派同窗他命帶錦鯉》 第90章
聞硯桐聽言一愣, 但見傅子獻沒往下說, 也不好刨問底, 只好道,“你放心, 用不了幾日,咱們就能出去了。”
傅子獻點頭, 而后主與搭起話來,“不知道牧楊的字會是什麼。”
這個聞硯桐知道,但是這種況, 也只能裝作不知,說道, “若是牧將軍取的, 定然是那種含義單純的名字。”
傅子獻抿一個笑, 說道,“先前來的時候,聽父親說起此事,說是牧將軍在上奏折子時寫錯了字,被皇上好一頓批評嘲諷,最后將給牧楊冠字的事由禮部來辦。”
“啊?”聞硯桐訝異道,“由禮部, 那不就是給傅丞相嗎?”
六部的頂頭上司都是丞相,皇帝將這事指給禮部,擺明了是要指給傅盛。這皇帝不僅自己給別人取名字,還喜歡剝奪別人給兒子取名字的權力, 雖然這牧將軍確實是個半文盲。
傅子獻道,“為此事牧將軍氣得兩天吃不下飯,還曾上門尋過我父親,兩人商議過后,確定一人持一字。”
聞硯桐已經能想象到他話中的“商議”有多激烈了,俗話說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像牧淵這樣子急躁的人,卻被傅盛一個文人按在地上捶,顯然有些時候腦子還是比拳頭更厲害的。
不過幸好皇帝多管閑事橫一腳,否則牧楊的字取什麼樣還真難說。據說當年牧楊出生的時候,牧淵秉承著賤名好養活的古老傳承,非要給他取名牧二蛋,此事還驚了皇上。
牧淵本人振振有詞,“賤名怎麼了?我以前就是這麼過來的,鐵牛了二十多年,每次都是逢兇化吉,劫后逢生。”
皇帝指著他道,“你能活那麼大不應該謝你那賤名,而是謝謝你脖子上頂的那顆腦袋——傻子多福。”
Advertisement
不過牧淵倔得很,最后還是牧夫人以命相才把名字改了后來的牧楊。
若是讓他取字,約莫就是些祥子、黑驢之類的了。
聞硯桐想起那些事,忍不住笑了笑,“看來你們傅家與牧家的恩怨又深了一層。”
傅子獻也笑,沒再說話。
聞硯桐又與他聊了兩句,然后才出門離去。傅子獻現在被關起來,什麼事都不知道,只守著上的那方玉牌,聽說這幾日能出去,才稍稍安心。
而知道些什麼的姜嶙則是坐立難安,只覺得誰也不能信任了,邊的人都有可能是應。
哪怕是什麼都知道的聞硯桐還有些不安,生怕有什麼事變。
不過事還是進行的很順利的。
臨近傍晚的時候,秋冬兩人沒有歸來,兩人帶出去的人回來了一個,上中了數刀,回來稟報說人已經被抓了,還是牧將軍親手抓的。
牧淵半生戎馬,沒進朝堂之前是這一代有名的土匪,進了朝堂之后是紹京矚目的大將軍,在戰場上活了半生的人與這些年輕殺手是不一樣的。
所以很多人都很懼怕牧淵。
聽說牧淵親自來之后,不人都慌了神,大部分都贊同先撤退,在這山谷里若是被府的人圍起來,就等同于甕中捉鱉,不可能跑的了。
除非在山谷被圍起來之前他們就尋一條出路逃出去。
于是聞硯桐先前的話立馬起作用了,到底是走往東的那一條路,還是分散走往南的路,或者是分兩撥一南一東。
讓面人很是頭疼。
最后他們先分了三撥人,分別從三條路下山,作為試探。
按照聞硯桐先前的叮囑,南邊的兩條路的人都被抓住了,當場死,而東邊的路放行。
隨后眾人都選擇從東邊的路撤退,青面由于并不相信聞硯桐,將蒙了眼睛,捆住手腳扔在了馬車里,他親自在周圍看管。
Advertisement
聞硯桐的眼睛蒙上之后,只覺得耳朵越發靈敏,周邊什麼聲音都有,青面道,“我們都是姜家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若是東邊這條路不能安全撤退,那我們便一并赴黃泉去見姜大人。”
大概意思就是,如果東邊的路有詐,我就一刀捅死你。
聞硯桐有些慌張,但想到池京禧也在這群人之中,他應該會想辦法救的,現在要做的就是穩定緒,與青面對弈。
鎮定笑道,“你這話說的不錯,不過若是我們什麼都沒做就下去見了姜大人,只怕姜大人會失吧。”
青面冷哼一聲,“倒不至于,反正傅盛的兒子還在我們手里,拉著他一起去見姜大人,也算是讓姜大人心里舒坦些。”
呸,人都死了,還舒坦個屁。
聞硯桐佯裝可惜道,“只是一個庶子。”
“聊勝于無。”青面又道。
聞硯桐懶得說話了,坐得端端正正,仔細聽著外面的靜。
府的大部分人馬都埋伏在了東路,只要他們走到地方,就會被全部抓住。問題是誰能夠在事發生的時候來救,還有傅子獻。
想到傅子獻臉蒼白的模樣,雖說他手很厲害,但看他那狀態也實在令人擔心。
什麼都看不見之后,時間就過得很慢,聞硯桐只覺得一分一秒都無比煎熬。
其實還有些擔心姜嶙,若是這些人被抓住,姜嶙自然也要落網,屆時所有人都會發現他是姜氏的余留,什麼將功補過的都是屁話,皇家不可能留下逆臣之子。
不過先前程昕留下了他,似乎并沒有要將他報給上面的意思,是不是代表著程昕想讓他活下來?還是說當時留下他只是程昕察覺到了什麼,所以才暫時扣下的。
Advertisement
正當聞硯桐胡思想的時候,外面忽而傳來一聲嘶聲馬啼,繼而躁猛地在人群中擴散,原本顯得安靜的山谷頓時響起了數人的吼聲,像滾落下來的巨石,令人心驚膽戰。
青面一見這況,便知道自己這是中招了,當下踹了聞硯桐肩膀一腳,將踹翻了,“大膽狗賊!竟然敢騙我!”
聞硯桐慌張的喊道,“我哪里騙你了!我說了走南路,是你自己不相信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會有埋伏,怎的你自己選錯了路還要怪我!?”
青面道,“你就是在跟我耍心機。”
聞硯桐立即怒道,“若非是你不信任我,也不必落得此下場,現在好了,你自己死也就罷了,還要拉上我一起!我如何對得起姜大人?!”
反正到最后也還是要堅持演戲。
青面目眥盡裂,刷地一聲了腰間的長刀,怒道,“既然我率領姜家兵落敗于此,你也同我一起去向姜大人請罪吧!”
聞硯桐什麼都看不見,只聽見利刃劃破空氣的聲音,讓猛地起脖子,本能的往后閃躲,“救命啊——!”
隨后一聲震耳的聲響,好似有什麼東西刺破了車廂,碎屑在空中飛舞,青面的刀到底是沒落下。
之后就是短兵相接的錚然聲,有人闖了進來,與青面上了手。聞硯桐靠著車廂盡力的往后挪,生怕自己擋著別人的路了。
隨后再響裂的聲音,有人怒吼一聲也加了戰斗,而后狂風卷了進來,好似車廂被人捅破了個大窟窿,所有的風,聲音,腥一同涌來,包裹住聞硯桐。
用力掙扎著被捆在背后的繩子,急促的呼吸在風聲里環繞,覺自己的頭發被吹得舞,袍也進了寒風,卻因為眼睛看不見而恐懼無比。
Advertisement
掙不開繩子的聞硯桐只能盡力的小自己的,聽著耳邊持續不斷的打斗聲,努力保持鎮定。
打斗持續了很久,時不時有慘聲傳來。后來聞硯桐發現耳邊的風聲慢慢小了,似乎是奔跑的馬慢慢停了。
顛簸也逐漸小了,耳邊的聲音也消失了,只有其他地方傳來的打架聲,聞硯桐的周圍卻突然安靜了。
戰斗結束了。聞硯桐很忐忑,非常害怕聽青面說話的聲音,也不敢主開口問。
聞硯桐的腳邊都是,染紅了的一雙錦靴。池京禧神淡漠的將尸從車廂上踢了下去,順手把劍釘在一邊的木板上,甩了甩雙手的。
傅子獻遞來一方干凈的錦帕。池京禧看他一眼,手接下,低著頭認真的著手上的,從腕到指尖,每一手指。作慢條斯理,得直到手上的都干了之后,才將沾滿的錦帕隨手扔了。
隨后他走到一團的聞硯桐邊,眼眸里的寒冰才開始融化,方才殺人的戾氣也逐漸消失,最后變得澄澈,映出一旁火把上的芒。
他抬手,用干燥的手指輕輕了聞硯桐的肩膀。
猛地往后一。隨后池京禧將眼睛上的黑布慢慢拉下來,輕聲道,“別害怕,已經沒事了。”
聞硯桐的眼睛被蒙了很長時間,一開始視還有些模糊,轉了轉眼睛,就看見面前蹲著池京禧,他的眼睛里都是溫和之。
再一看,他后站著持劍的傅子獻,半都是,還順著劍刃滴滴答答。池京禧的手上也都是,但是這雙手卻是干燥的。
良久之后,聞硯桐因驚嚇而蒼白的臉上出一抹笑容,“我知道。”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1 章

軍婚:跟首長閃婚後全豪門來團寵
【現言軍婚】【超級爽文】傳聞高嶺之花的軍區首長傅宴庭在戰區撿回來了一隻小野貓。野性難馴,盛世美顏,身懷絕技,吃貨一枚。傅宴庭就好這一口,直接閃婚,綁定夫妻關係,禁錮在身邊圈養,應付七大姑八大婆。京都吃瓜群眾評價:“毛病太多,沒有背景,早晚被傅家針對,掃地出門,淒慘收場。”哪裏想到這隻小野貓不簡單,不服就幹,絕不憋屈。剛領證就把首長壓在身下,占據主動權。進門第一天當著公公婆婆的麵掀桌。進門第二天就把挑事的綠茶打的滿地找牙。進門第三天就跟桀驁不馴的小姑子處成了閨蜜。進門第四天將名媛舅媽潑了一身糞水……被打臉的京都吃瓜群眾評價:“得罪公婆小姑子傅家親戚,看你怎麽死!”結果被寵上了天。公公傅盛銘:“家人們,誰懂啊?第一次看到我那個不可一世的兒子蹲下身給婆娘洗jiojio,笑瘋了。”婆婆林清月:“笑瘋了姐妹們,我兒媳婦的大師叔竟然是當年求而不得的白月光,現在還得低頭叫我一聲林姐姐呢。”被揍得鼻青臉腫的渣渣們集體到傅宴霆麵前哭訴:“首長,您女人都要把天給掀翻了!求您發發神威管管吧!”傅宴庭:“哦,我寵的。”
21萬字8 8962 -
完結7 章

再重逢,總裁前夫盯著我流產單失控了
和宋楚城在一起那幾年。我們做盡夫妻該做的事,但他從沒提過一句“愛”字。 后來我才知道。 他有個貫穿了整個青春的白月光。 而她,回來了。 我懷孕三個月,他陪了白月光三個月。 于是我提離婚,放他自由,自己一個人去了醫院流產。 “沒有家屬簽字?” “我自己簽。” 手術很疼,可我卻聽到他在手術室外痛哭:“老婆,別不要我們的孩子..."
1.3萬字8 698 -
完結1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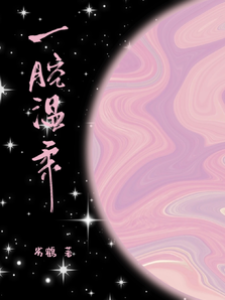
一腔溫柔
【西裝暴徒·戀愛腦大佬x淚失禁體質小奶兔,SC,男主在別人面前孤狼,在女主面前傻狗,老房子著火沒有救~】【男寵女❤先婚后愛+7歲年齡差+體型差+她永遠是例外跟偏愛~】 寧惹君子不惹小人,寧惹小人不惹閻釗! 京城誰不知道閻釗的惡名?四九城里把人剝皮抽筋的活閻王! 可是擁有讀心異能的葉早,每次閻釗兇巴巴,她都能讀取他的內心話—— [這小不點兒,腿長腰細,不知道手感好不好。] [這小姑娘的嘴巴,紅彤彤的,怎麼很好親的樣子。] [這小呆子,被人騙了都得幫人數錢。] [早早!我的可愛老婆!她怎麼還不來哄我?再不哄我我要鬧了!] [啊啊啊啊我已經開始鬧了!] [不親我一下,今兒這事絕對過不去!絕對!] * 壞消息:這個男主強取豪奪,偏執+占有欲爆表,日常不長嘴,玩強制! 好消息:這個女主會讀心~ 虐心虐身劇本也能分分鐘轉甜,小白兔義無反顧治愈孤狼。 【嗜血瘋批,唯獨予她一腔溫柔~】₍ᐢ..ᐢ₎⊹
29.5萬字8 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