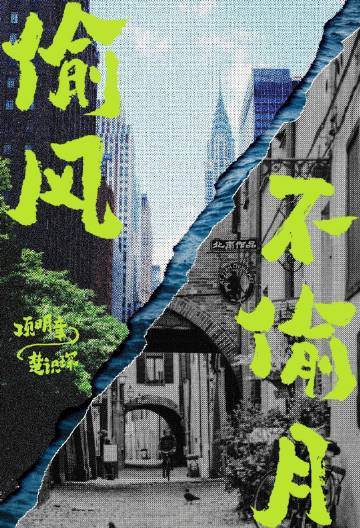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王牌女助》 第747章 別不要我
陳博軒不懂,或者說大多數的男人都不太懂,人的承能力,往往比男人強大的多,尤其是在重大變故面前。
蔡馨媛當然不是不在乎,只是循著他的異樣,猜到一些什麼,如今聽他親口承認,也倒坐實了心中的想法。
至於什麼哀莫大於心死,這種不會出現的這麼快。
只是靜坐了一會兒,周圍死一般的安靜,陳博軒也不好貿然開口說些什麼,最後,還是蔡馨媛主問:“只是睡在一張牀上,還是真的睡了?”
陳博軒想到商紹城的話,他一口咬定沒睡;可他腦海中又不由自主的出現白牀單上的斑駁紅點……掙扎之下,他還是選擇遵從自己的心,反正代也代了,就別再半真半假的往外禿嚕了。
他說:“我真的喝斷片了,中途有一點印象,還以爲是你,是到了,其他的做沒做,我真的不記得,馨媛,我發誓我絕對沒有故意想什麼歪門邪道,不然我也不會跟你說,出了這樣的事,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對,但我希你能原諒我,我保證以後不會再發生。”
蔡馨媛面上依舊不見任何緒波,如果非要用一種表來形容,可能就是面無表吧。
陳博軒解釋過後,只‘嗯’了一聲,說了句:“我知道了。”
陳博軒不知道這算是什麼意思,只見蔡馨媛拿起包,從沙發上起。
他下意識的跟著起來,蔡馨媛轉頭,邊走邊道:“不用送我。”
陳博軒看著的背影,心底又急又疼,忍不住上前拉住的胳膊,沉聲道:“馨媛,對不起,你原諒我一次行嗎?”
蔡馨媛微垂著視線,低聲回道:“你讓我回去好好想想,你一晚上沒睡,一會兒睡一覺,我們都想想清楚。”
Advertisement
陳博軒聽著波瀾不驚的話,急著抱住,蹙眉道:“馨媛,我想得很清楚,我只喜歡你一個人,如果我但凡有點意識,我絕對不會一手指頭,你相信我。”
蔡馨媛說:“我信。”
陳博軒抱得地,像是一不小心鬆了勁兒,就會走。
“你鬆開我,讓我一個人冷靜一會兒,我信你這次不是故意的,不然我直接跟你說拜拜了。”
話音落下,陳博軒稍稍放開了手臂,垂目睨著那張繃的面孔說:“是我不好,讓你傷心了,如果是我主犯了錯,不用你說,我也沒臉來求你原諒我,但我不想就這麼不明不白的跟你分開,我覺得我也是害者,你千萬別不要我。”
平日裡玩鬧的時候,他也經常裝弱,可蔡馨媛心裡明白,他骨子裡還是很傲氣的人,等閒不會在認真的時候跟誰裝可憐,如今他一句話,直接讓紅了眼眶,想走,陳博軒卻拽著不讓,拉扯之間,蔡馨媛終是繃不住,淚水模糊了視線。
他想幫眼淚,蔡馨媛暴躁的擡起手打他,有時候是掌,有時候是拳頭,一下一下,胡的拍在他口,手臂,有時候甚至刮到他的下。
陳博軒就站在原地,一不的任由打,蔡馨媛視線被淚水模糊,什麼都看不見,機械的重複著打人的作,打著打著,到底是抓著他前的襯衫,垂下頭,大哭出聲。
陳博軒也紅了眼,擡起手,他扣著的後腦,把拉到自己前。
蔡馨媛哭的很大聲,說是殺人也毫不爲過,破口大罵:“陳博軒,你他媽混蛋!”
陳博軒結上下微,脣瓣開啓,出聲說:“我是混蛋。”
Advertisement
又說:“你故意欺負人……”
他跟著說:“我錯了,以後再也不這樣了。”
蔡馨媛擡起拳頭,狠狠地往他上懟,可不是做做樣子,是真的用力,有時候直接懟在陳博軒胃上,他覺得胃部瞬間一陣痙攣。
可是上的疼,讓他心裡的愧疚了些許,站在他的角度上,他是害者;可是站在蔡馨媛的角度上,他是傷害者。
他沒有理由要求蔡馨媛一定要爲他的不得已而買單,所以他語氣甚至帶著卑微,他在乞求原諒。
活了二十六年,陳博軒第一次開始懷疑自己過往的人生,雖然沒有傷天害理,可是不是過得太放縱了一些?以至於老天爺都看不過去,讓他終有一報。
事兒還是從前的那些事兒,他房裡也不是第一次被人塞了人進來,只不過從前是禮,現今是炸彈,因爲他變了,所以一切都不是從前的那些了。
也正因爲如此,他不能過分的怪郝銘,也不能怪那個人,他只能怪自己,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現在,他終於相信世間有報應這一說了。
蔡馨媛被陳博軒抱在懷裡,哭了好久,能不生氣嘛?能不委屈嘛?出門一趟,回來弄這麼個事兒。
兩人就這樣杵在客廳一,不知過了多久,蔡馨媛眼淚漸收,推開陳博軒的懷抱,徑自走到一旁拿紙眼淚和鼻涕。
陳博軒的視線一直落在上,生怕隨時一個舉,或者一個句話,就能讓他肝腸寸斷。
“我先回去了,你這兩天也不用打給我,我想好了自然會找你,你自己也想想,都先休息幾天吧。”
蔡馨媛還是要走的,陳博軒說:“我送你吧?”
Advertisement
“不用了。”
蔡馨媛走至玄關,穿上高跟鞋,頭也不回的推門離開。
待到房子中只剩下陳博軒自己的時候,他一個人站在原地,久久沒,前的襯衫上溼了一片,其中一還蹭上了口紅,同樣都是紅,可卻天差地別。
口上的口紅,是他的心頭;昨夜牀單上的落紅,是他的眼中釘。
頭疼裂,他只能靠閉眼來緩和,心中五味雜陳,他唯有告訴自己,這都是命,誰讓他從前風流不羈,這都是他應該承的,教會他什麼因果循環。
蔡馨媛從陳博軒那裡離開之後,除了回家別無可去,中途岑青禾打給,想說有個客戶來公司找,讓回來一趟,結果電話打通,蔡馨媛聲音發悶,岑青禾一細問,蔡馨媛直接在電話裡面哭了,嚇得岑青禾趕放下手頭工作,跑回家裡。
兩人一聊,得知陳博軒‘被睡’的消息,岑青禾也很是驚訝,再看蔡馨媛哭得兩隻眼睛腫核桃,岑青禾心裡不忍,趕忙安道:“你先別哭,你看我給你分析一下啊,首先這事兒是軒哥主坦白代的,那最起碼能說明,軒哥沒撒謊,出了事兒他想著跟你坦白從寬,沒想過渾水魚;還有他既然敢坦白,那就說明他心裡沒愧,誰自己做虧心事兒還主代的?他傻嗎?你也說了,這事兒是他朋友自作主張安排的,軒哥喝多了,其實他也是害者啊,誰心疼心疼軒哥了?我沒看見他,都能到他睜眼時的懵和恐懼。”
如果陳博軒在這裡,他一定要激涕零,上前給予岑青禾一個大大的擁抱,平日裡沒白對好,關鍵時刻真有用。
蔡馨媛抹著眼淚道:“我問他睡沒睡,他說他斷片了,一點兒印象都沒有,那是睡還是沒睡?”
Advertisement
岑青禾道:“其實怎麼說呢,你最介意的是軒哥跟其他人發生了什麼關係,還是出現這種結果的起因,是不是他自願的?”
蔡馨媛立馬道:“他要是自願的,我還跟他費什麼話?哪兒涼快哪兒待著去吧。”
岑青禾道:“所以說嘛,你就當是一次事故,軒哥現在也是害人之一,他說他可能斷了,你何必計較他到底是真斷還是假斷,就算是真斷,你能因爲這種意外就不要他了嗎?”
蔡馨媛搭著回道:“那心裡也不怎麼舒服,癩蛤蟆不咬人還膈應人呢。”
岑青禾道:“欸,你可別這麼說,軒哥聽見多傷心啊?”
蔡馨媛盤著,遲疑著問:“那你覺得我該原諒他了?”
岑青禾說:“目前看,軒哥除了酒量差點兒之外,貌似沒有其他bug了,而且喝多之後也不是他主酒後,他這屬於吃悶虧吧?咱就算不能給他報仇雪恨,也不能再讓他無的冷暴力了,你說是吧?”
蔡馨媛是個理智的人,岑青禾說的這些,都已經想過了,如今只需要一個人堅定不移的肯定的想法,讓不再懷疑自己的判斷。
眼淚乾了,腫著一對眼睛問岑青禾,“欸,如果是你家城城,你會怎麼辦?”
岑青禾瞬間就了,連著‘呸’了三聲:“烏,你可別咒我。”
蔡馨媛馬上道:“你看你,勸我這麼理智,推己及人,能不能換位思考一下?”
岑青禾搖頭,“我不敢想,你覺得我和城城之間的雷點還不夠多嗎?我倆連談個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弄出點兒幺蛾子出來,你就別祈禱我的生活更加絢爛多彩了。”
蔡馨媛雙手往腦後一墊,著天花板,忽然慨的說:“其實我不是單純因爲這件事兒不高興,我只是在想,出個差都能演一出酒後送禮的戲碼,他以前的生活是有多?這一次是誤會,會不會還有下一次?下一次他是主還是被?還會不會跟我說?”
岑青禾聞言,聯想到商紹城跟陳博軒的生活環境是一樣的,頓時也陷了沉思。
評論過一萬,加更一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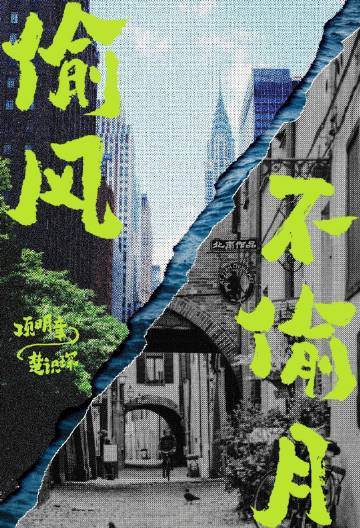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1407 章

嫁給傻王爺后被寵上天
令人聞風喪膽的女軍醫穿越到了段家廢柴二小姐的身上,爹不疼,沒娘愛,被迫嫁給奄奄一息的傻王爺。誰料到傻王爺扮豬吃老虎,到底是誰騙了誰?...
243.7萬字8 16239 -
完結7 章

霸道專寵,葉總裁他又兇又甜
陰差陽錯,她成了總裁的合同替身情人。她給他虛情,他也不介意假意。她以為是義務,卻在偏心專寵下不斷沉淪。她把自己的心捧出來,卻遇上白月光歸國。她經歷了腥風血雨,也明白了如何才能讓愛永恒……合同期滿,葉總裁單膝跪地,對著她送出了求婚戒指,她卻把落魄時受他的恩賜全數歸還。這一次,我想要平等的愛戀!
1.5萬字8 99 -
完結143 章

被我強取豪奪的太子爺回來報仇了
【久別重逢+破鏡重圓+雙初戀+HE+男主一見鐘情】五年前得意洋洋的晃著手中欠條威脅顧修宴和她談戀愛的黎宛星,怎麼也沒想到。 五年后的重逢,兩人的身份會完全顛倒。 家里的公司瀕臨破產,而那個曾因為二十萬欠款被她強取豪奪戀愛一年的窮小子卻搖身一變成了百年豪門顧家的太子爺。他將包養協議甩到了黎宛星面前。 “黎主播,當我的情人,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 身份顛倒,從債主變成情人的黎宛星內心難過又委屈。 會客室里,外頭是一直黏著顧修宴的女人和傳聞中的聯姻對象。 這人卻將她如小孩一樣抱了起來,躲到了厚厚的窗簾后,按在了墻上。 黎宛星:“你要干嘛!” 顧修宴勾起嘴角,“偷情。” - 顧修宴在金都二代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性子冷淡,潔身自好,一心只有工作。可突然有一天像被下了降頭一樣,為了黎宛星公開和顧家兩老作對。 身邊的人好奇的問:“怎麼回事啊?這是舊情復燃了~” 顧修宴淺抿了一口酒,“哪里來的舊情。” - 這麼多年來,一直以為是自己先動心的黎宛星在無意間聽到顧修宴和朋友說。 “我喜歡黎宛星,從她還沒認識我的時候就喜歡她了,是一見鐘情。” 黎宛星一頭霧水。 什麼一見鐘情,當年難道不是她單方面的強取豪奪嗎?
27.3萬字8 1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